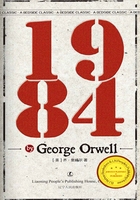“刚才我在想冒名顶替。找一个可以让他顶替的人。借尸还魂。一个活人的鬼魂。但这也有漏洞。假如那个正主儿还活着,那么‘基地’组织早就把他安排在上层了。假如他已经死了,他们也会知道。所以,行不通。”
“这文件真厚,”马雷克·古米尼说,“我能把它带回去看吗?”
“当然,这是一份复印件。但只能看,不能外传。”
“你放心好了,老朋友。只是我自己看。除此要么放进我的保险柜,要么焚毁。”
中情局副局长飞回了兰利,一周后他又打来了电话。史蒂夫·希尔在秘情局办公室里接听了。
“我想我还得飞过来一次。”中情局副局长开门见山地说。
两个人都知道英国首相已经答应他的白宫朋友,在清查“黄貂鱼项目”的工作中,英国方面将给予全面合作。
“没问题,马雷克。你们取得突破了吗?”私下里,史蒂夫·希尔也产生了兴趣。应用现代技术,任何信息都能绝对安全地从美国中情局传送到英国秘情局,而且只需几秒钟就可完成传送。何必要飞过来呢?
“冒名顶替的对象,”古米尼说,“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年纪是轻了十岁,但他看上去很老成。身高和体型都相仿。同样黝黑的脸庞。那个人是‘基地’组织的一名老兵。”
“听起来很不错。但他为什么没和那帮混蛋在一起?”
“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被关在关塔那摩,已经在那里待了五年了。”
“他是一个阿拉伯人吗?”希尔吃了一惊。如果“基地”组织有哪个阿拉伯高层人士在关塔那摩关了五年,他是应该知道的。
“不,他是一个阿富汗人。名字叫伊兹玛特·汗。我这就出发。”
距离上次车里的对话已经过去一周了,但特里·马丁还在失眠,就为了那次愚蠢的多嘴。为什么他不能闭上他的那张臭嘴?为什么非要拿哥哥吹牛?或许本·乔利已经说了些什么,毕竟华盛顿是一个大地方,流言飞语很多。在他信口开河的第七天,他打了一通电话给哥哥。
麦克·马丁正在屋顶上掀起最后一批完整无损的瓦片。现在他终于可以在瓦片下面铺设格条木和房顶油毛毡了。一个星期后,他就可以弄好防水的屋顶了。他听到手机发出叮叮咚咚的乐声。手机放在他挂在附近钉子上的外套口袋里。他小心翼翼地踩着脆弱的椽子去取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他在华盛顿的弟弟的号码。
“嗨,特里。”
“麦克,是我。”特里总是搞不明白人们是如何知道是他打的电话。“我干了件蠢事,想请求你的原谅。大概是一星期前,我说漏了嘴。”
“没关系,你说了什么?”麦克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但是你要注意,如果有任何穿西装的人登门拜访——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人——你就告诉他们这事没门儿,让他们走开。我说清楚了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任何人造访……”
从他的“鹰巢”里,麦克·马丁能够看到一辆炭灰色的“捷豹”汽车缓慢地由一条巷子开上了通往谷仓的土路。
“好的,兄弟,”他温和地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来了。”
两位间谍头子坐在折叠椅上,麦克·马丁则坐在一段将要被电锯锯成小片当柴火的树干上。马丁倾听着美国人的“策反”,同时朝史蒂夫·希尔扬起了眉毛。
“最后由你定,麦克。我们政府已经向白宫作了保证,不管他们需要什么,都提供全面的合作。但这么说并不是迫使任何人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属于这种吗?”
“我们倒不这么认为,”马雷克·古米尼回答,“哪怕我们只是获得了‘基地’组织内一个知道这个项目情况的指挥官的名字或是蛰居地点,我们就会让你撤出来,然后由我们去做其余的工作。只要窃听他们的闲聊我们也许就能成功——”
“但乔装打扮……我认为我不能再去装扮成一个阿拉伯人了。十五年前在巴格达,我打扮成一个卑微的花匠,居住在一间棚屋里。那次对付伊拉克秘密警察的盘问还不成问题。这一次,要面临的是深度审问。一个落在美国人手里五年的人,为什么没有变节呢?”
“是的,我们猜想他们是会审问你的。但如果运气不赖的话,来审讯你的也许会是一名高官。这样的话,你只要设法逃出来,把这个人指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就埋伏在附近,近在咫尺。”
马丁拍了拍关在关塔那摩监狱里那个人的档案,说:“这是一个阿富汗人,前塔利班军官。那意味着是普什图族人。可我根本讲不了流利的普什图语。恐怕我一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就会被人家识破。”
“我们会安排几个月的培训学习,麦克。”史蒂夫·希尔说,“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是不会让你去的。到时候如果你自己认为不行,我们也会取消行动。而且你将会待在远离阿富汗的地方。幸运的是,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很少会走出自己的地盘。”
“你觉得你能在有限的学习后说一口磕磕巴巴的、带普什图口音的阿拉伯语吗?”
麦克·马丁点点头说:“可以。但万一那些戴头巾的人带来一个人,他认识我冒名顶替的那个家伙,那会发生什么呢?”
另两个人沉默了。如果发生这种事,那么现在围坐在篝火边的三个人都明白,游戏将会结束。
两位间谍头子凝视着脚下,不愿解释一位特工在“基地”组织手里如果被剥去了伪装将会是什么下场。马丁翻开了他膝头上的那份档案。眼前的资料让他愣住了。
这张照片是五年前拍摄的,照片上的那张脸因生活的磨难而布满皱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岁。但这人还是那个来自山区、在卡拉伊贾吉差点死去的男孩。
“我认识这个人,”马丁轻声说,“他叫伊兹玛特·汗。”
美国人凝视着他,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自从五年前被抓获,他一直被囚禁在关塔那摩。”
“这我知道,但多年前,在托拉博拉地区,我们曾一起抵抗入侵的苏联人。”
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人回想起在马丁档案里的记载。是的,他是有一年在阿富汗帮助穆斯林游击队抗击苏军的占领。事隔多年可能有些淡忘,但那两个人曾经相遇也并非绝无可能。他们就伊兹玛特·汗的情况问了马丁足足十分钟,看看他还能补充些什么。马丁把档案递了回去。
“这个伊兹玛特·汗,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在D营,在你们的手里待了五年之后他有什么变化?”
来自兰利的美国人耸了耸肩:“他很顽固,麦克。顽固不化。来时头部受了重伤,还有脑震荡,是在拒捕时受的伤。起先,我们的医务人员还以为他的情况也许……嗯……比较简单,但正相反,他神智完全糊涂了。也许是因为脑震荡和旅途的颠簸吧。那是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初,‘九一一’之后不久。我们给他的待遇……嗯,怎么说呢……不是很温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好像恢复了,可以接受审问了。”
“他对你们说了些什么?”马丁问道。
“不是很多。只是他的简历。他拒绝回答所有提问,也不想要所有的待遇。只是盯着我们,士兵们从那双黑眼睛里看不到一丝热情。所以他被囚禁在地牢里。但从其他渠道我们了解到,他的阿拉伯语还过得去,是在阿富汗国内学会的,此前还背诵过多年的《古兰经》。另外,据另两个英国出生的‘基地’组织的志愿者说,他能讲一些结结巴巴的英语,是他们教他的。这两个人曾跟他关在一起,现在已被释放了。”
马丁瞟了一眼史蒂夫·希尔:“应该把他们抓起来进行‘隔离消毒’。”
希尔点点头说:“当然了。我们会去安排的。”
马丁又继续翻看了一会儿档案,马雷克·古米尼站了起来,在谷仓周围踱步。麦克·马丁凝视着篝火,在火苗的深处,他似乎看到了一道遥远、荒凉贫瘠的山坡。两个人,一丛岩石,还有一架苏军“雌鹿”武装直升机转过来正要发起进攻。戴着头巾的那个男孩问道:“我们会死吗,英国人?”古米尼走回来,蹲到地上,用铁棒去拨弄篝火。刚才想象的画面化成了一片火星。
“你这里的工程量不小啊,麦克。我还以为是一个专业装修队伍在做呢。都是你自己动手做的?”
“尽量自己做。二十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呢,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可是钱不太够吧?”
马丁耸了耸肩:“如果我想找一份工作,有许多保安公司。光是伊拉克,专业保镖就已经供不应求了,还一直在招募。他们在逊尼派地区为你们的同胞打工,周薪要比当兵的半年的薪水还多呢。”
“但那意味着要回到沙漠和危险的地方,还会搭上性命。你不是已经从那种生涯中退出来了吗?”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与‘基地’组织的人在佛罗里达群岛度个假?”
马雷克·古米尼微微一笑:“美国人在许多事情上都遭到过指责,麦克,但对待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却很少有人说我们小气。我正在考虑支付咨询费,嗯,二十万美元一年,连续支付五年怎么样?汇到国外的账户上,税务局不会来找你麻烦。你也用不着再去找工作了,用不着再去经历枪林弹雨了。”
麦克·马丁的思绪飞到了他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的一个镜头。托马士·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提出付钱给阿乌德·阿布塔伊,让他与他一起进攻亚喀巴。马丁回想起那个精彩的回答:“阿乌德不会为英国人的金子骑马去亚喀巴,他去是因为这使他开心。”他站了起来。
“史蒂夫,我希望把我家用篷布整个儿盖起来,从屋顶到墙脚。等我回来时,我希望看到它与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点点头。“没问题。”他说。
“我会带上自己的东西。不会太多,后备箱就足够了,不会再多了。”
就这样,西方反击“黄貂鱼项目”的计划在汉普郡一座果园的苹果树下敲定了。两天以后,通过随机选择,电脑把这个反击计划起名为“撬棍行动”。
后来在历次情报汇报中,关于这个曾是自己朋友的阿富汗人的事,马丁留下了一个细节没说。如果受到质疑,麦克·马丁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
他想,也许“无须知道原则”是双向的,既有上级不需要下级知道的事,也有下级不想让上级知道的事。也许,他认为这个细节太不重要了。它与一场用阿拉伯语进行的交谈有关,那次交谈发生在一个叫贾基的地方,一座阿拉伯人开办的山洞医院的阴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