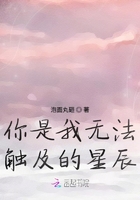这么小的个子,一桌的食物去了大半。过了一会儿,午夜终于开口,“别吃了,过来。”
红歌不解,放下勺子,嘴里还在捣鼓着,起身越过椅子站到午夜面前。
午夜坐立不动,隔着衣服摸了摸红歌的腹部,软软的,很平,没有什么异常。
“怎么?”红歌看着午夜说,“难道你儿子是傻子?撑着了还吃?”
午夜心中又是一阵冲击。“你儿子”,这是代表的什么意义?是认可。叫不叫爸爸有什么区别。那一刻,午夜觉得红歌已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感情重于一切,亲生和非亲生又有什么不同呢?
“告诉你,才到这里。”红歌没有发现午夜的激动,用手指了指胸口,“还差一小截呢。”
一有空闲,午夜就会陪红歌玩,打游戏,练习乐器。已能弹奏简单的曲子。晚饭后,二人时常会来一场合奏,一人一把吉他。笑声不断。
红歌已习惯了午夜赋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起熬夜,晚睡早起。不赖床,不闲坐。手里时刻要捣鼓点什么。
时日长久,被渲染得和午夜一样,话多,爱笑,崇尚新鲜事物。
“告诉你个秘密,今天我受到了表扬。老师说我是班里唯一没有迟到记录的好学生。”红歌一脸得意地对午夜说。“是整个学期哦,天天早到。当然这应该是你的功劳。”
午夜点了点红歌的鼻头,笑说,“那当然,有我呢。所有的迟到都是借口。如果天不亮就出门,就算有再多的意外,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解决好。是不是?”
“对嘛。”红歌伸出小手,示意午夜和自己来个击掌。
薇儿怎样努力也换不来红歌的好感,她又是难过又是愤怒。又很无奈,于是也不再费神。反正妈就是妈,不亲也是妈,改变不了。还如从前一般生活,对一切置之不理。
红歌每天晚上要自己洗袜子,自己选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和携带的物品。午夜在旁边看着,很少帮忙。
小衣柜被翻得有些乱,红歌试图将它们整理好,却反而把旁边已经叠好的一摞衣服给拽乱了。因此有些不高兴,不过手上的动作一直没有停下。
“我这么小的时候也什么都自己做,因为你是男孩子。”午夜看出红歌此刻有了小情绪,主动开口。
“为什么我要做的事比妈妈还多?为什么她整天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她是女人吗?”红歌说出自己一直的疑惑。
午夜却不知怎么回答,“妈妈和妈妈不同。难道你喜欢妈妈什么样,她就要什么样吗?”
红歌接着说,“还有,为什么她不像老师那样温柔亲切?我们都喜欢围着老师转的。”
午夜想了想回答,“一直就是这样。这个我也无法回答。这样吧,等我物色一个符合你心意的,然后把她换掉怎么样?”
红歌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认真琢磨起午夜的话来。托腮想了半天回答:“还是不要吧,陌生人也许还不及她对我好呢。”
新搬来的邻居,也有个一般大的女孩。有时周末妈妈会带孩子来做客。红歌很快就和小女孩玩在一起。
“你房间里的玩意真多,不过挺漂亮的。”小女孩叫妃妃,也很活泼。“我的床上全是洋娃娃。”
“那下次给我看看。这些都是我自己摆放的。很特别吧。”红歌一直对自己的这个杰作感到骄傲。
“嗯。你妈妈很漂亮,我妈妈就从来不穿那个颜色的裙子。”小女孩对漂亮的评价,是从裙子来判断的。
“你对她有什么感觉?”红歌问小女孩。
“比我所有的洋娃娃都漂亮,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的妈妈,因为她很温柔。你妈妈好像不太笑的,笑起来的感觉也不大一样。”
“她不是妈妈,是阿姨。”红歌感觉这个词才能形容自己和薇儿的关系。
“哦。我知道,阿姨就是爸爸的新女人。你爸很帅的,因为他好瘦,我不喜欢我爸爸的大肚子。”
“哦,那让你爸也瘦成我爸那样不就行了?”在他人面前,红歌对午夜的称呼,已是“我爸”。不过在午夜面前还是叫他名字,两人也一直不觉得别扭。
“那好吧,回家我就跟我爸爸说,要他把大肚子变走。”小女孩大大的眼睛,笑起来可爱极了。
这样看来,一家人也勉强算是其乐融融了。
见午夜和红歌挤在一起,吃着饭还又说又笑的,似乎在说暑假要带他去国外玩,帕特雷等等,说了一些去处,描述得绘声绘色。听得红歌一脸憧憬。
薇儿在旁边听着不悦,孩子这么小,折腾什么?把瘾勾搭上来,不去不行。去了水土不服怎么办?八成是午夜自己想出去玩了,拿孩子当幌子。
“不许去。等他大点再说。想去在附近转转不就完了。”薇儿挟了一片笋给红歌,自己却没怎么动筷子。
“要说现在去是有点早,那就再等等吧。”不是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午夜一般不会与薇儿产生分歧。
“那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呀?”红歌却抬起头来看着薇儿。
薇儿有些意外,他竟主动和自己说话了。也不想太扫兴,“六岁就可以了。”
“哦。”答应一声,红歌低头扒拉了两口饭。
见红歌神色失望,午夜赶紧说,国内也有很好的去处。南京的甘泉湖,有尼斯海怪,天斩飞渡。广州的长隆欢乐世界,好玩的有沙比国王和冰河世纪。然后对游乐场景做了简单描述。
听得红歌又开心起来。
“这个我能去吗?”红歌又转过头去问薇儿,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我没有称呼吗?跟你爹学得一点礼貌都没有。”薇儿见红歌整日叫午夜名字,觉得不像话。不过午夜都不介意,自己也没有必要管。知道自己反感“美女”这个词,红歌现在也很少叫了。但是也许他找不到合适的称呼,叫“阿姨”更是不像话。所以连个“哎,”,“喂”,这样的词都省略了。
“叫声妈,就让去。”薇儿以此来诱惑红歌。
红歌撇撇嘴,低了头吃饭。不再说话。
那便是拒绝了,为了不叫人,连梦想之旅都放弃了。
薇儿气不打一处来,觉得自己很下不来台。又拿红歌没辙。再没了吃饭的心思。
又觉得午夜多事,无端讲什么旅行,不好好吃饭,还那么多话。再看南宫烈,对刚才的事充耳不闻,碗旁边还摆个笔记本。吃一口,摁两下。屏幕里还不时传出惨叫声。
忽然觉得眼前这一切都很让人厌烦,想到红歌对自己的态度,更是恼怒。
“吃个饭也不叫人安生!”薇儿忽然将碗一推,一只手按在桌子上。面色因恼怒微微潮红。
三人同时抬头。
“难道又要开战了?”南宫烈似在自言自语。抱起笔记本,冲薇儿说,“没我的事,我早就服你了。他不服,你找他。”南宫烈眼神瞟了瞟午夜,然后自行离开了。
午夜见怪不怪。薇儿极度易怒,越吵越坏,没人理等会儿自己就能好。随即站起身来,将杯子端起送到红歌嘴边。红歌将杯里的果汁几口喝了个干净。放下杯子,午夜忽然一把将红歌抱起,离开了餐桌。
红歌告诉午夜,自己这几天在幼儿园一直肚子痛,一阵一阵的,也不是很强烈。午夜有些紧张,问他白天都吃过什么东西,红歌说中午吃了冷饮。午夜觉得应该是凉到了。从卫生间出来,果然没再闹疼。观察了一晚上没有异常,转天清晨午夜打消了去医院体检的想法。
直到某天接到老师电话,说孩子突然晕倒,已送到医院。
午夜,薇儿,南宫烈,三人从不同的地方同时赶到。
噩耗。医生的话让三人吃了一惊。
贾第虫病。红歌的体内竟有肠道寄生虫,虫卵吸食血液和养分,体积已经很大。肝脏被损坏,肠道有破损和出血状况。红歌属于无症状病原体携带者。这种情况最糟,漫长潜伏期,患者不会有不适情况发生,很少引起注意。而在后期症状急剧爆发,此刻胆,肝等重要器官已被严重损坏。病人生还几率很小。
医生说红歌饮食了带有虫卵的蔬果或水。据推测,卵虫进入身体已有一年半之久。
此刻红歌危在旦夕,医生说,虫体与肠道搅缠在一起,清理风险很大。
薇儿跌坐在椅子上,怎么会这样?一年多了?那便是在养父母家里的时候吧。必是妻子死后,那老头精力下降。只顾着挣钱,红歌无人照料,自己疯玩,乱吃了东西吧。
都是自己的错,自己为什么不把他留在身边?小小年纪吃了那么多苦,恐怕还要失去性命。自己这个做母亲的,该被雷劈死才对。
南宫烈更是自责,怪自己说了谎,是自己拖延了病情,害红歌丢失生命。自己当时忙的是什么?只想着玩乐。觉得自己愧对午夜,愧对孩子的那一声“烈叔。”要是红歌有什么意外,自己这后半生无法安宁。
午夜亦是悔极,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自己当初真的忙得连一天的时间都挤不出吗?知道南宫烈不靠谱,自己还不认真点。吃得多,体重减轻,脸色不佳,不都是征兆么?自己怎么就那么糊涂呢?当初将他接回家的时候,就应该做个体检。没病了解一下身体状态也好呀。那时若发现病情,也许还有得救。都是自己的错。
医生说,红歌还是身体素质好的,换了体质差的孩子,早就病变了。
午夜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急救室的灯亮起。
那是一个漫长的刑罚。薇儿泪水直流,真想打自己耳光。
南宫烈倚着墙壁,一脸的担忧与懊悔。
午夜似乎略微镇定了些,站立不动,眼睛紧盯着门口。
肠虫已清,但是内脏重要器官严重破损,修补无益。情势暂时被控制住,但医生说,没几天活头了。
看红歌躺在那里,一副蔫黄瓜的模样,再想想当初凌人的小霸王样子,三人心酸不已。
插了一身的管子,就脑袋还露着。红歌紧闭着眼睛,脸色发白。
三人无话,各自悲痛。默默守了一夜。一直警惕,都没有合眼。
如医生所言,第二天红歌醒了过来。这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午夜做出选择,医生拔去了红歌身上的管子。这会加快死亡的速度,但可以和家人交谈,身体能维持片刻的正常运作。要不就是在昏厥中睡死过去,虽多活几日,却也没有意义。
午夜选的是前者。
“你难受吧?”午夜强忍心酸,巴不得自己替红歌受罪。
“还好,有一点儿。”红歌抬起了小手,午夜赶紧握住那只手。觉得难过,又轻轻将红歌拉起,抱在自己怀中。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隔着衣服,午夜明显感受到那小小的身体,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和热度。
“嗯。我知道我生病了,没事的,我根本不害怕。你说男孩子要坚强的嘛。等我好了,我们再一起去跑步。还有,你说暑假要带我出去玩的。”红歌哪里知道自己就将抛下他的亲人,独自离开。
“好。”午夜都不敢多说,怕自己会情绪失控。
“又有点难受了,让我休息一下。午夜。”红歌耸拉着脑袋,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
“你怎么又叫我名字呢?”平时午夜真的不在乎,此刻却希望红歌改一改口,圆了自己心愿。可也不敢多言,怕自己越来越抖动的话音会吓到红歌。
再度抱紧,将红歌的下巴放在自己肩头。
“这样好一点了。”红歌抬头看到满脸泪痕的薇儿,看到她那痛苦的眼神,忽然也感到有一丝难过。知道她还是爱自己的,只不过不是自己喜爱的方式。此刻自己生病,她竟伤心到这个地步。红歌感觉自己心中一下子柔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