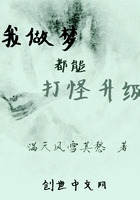贺木额日斯听着赫连哈尔巴拉和挛鞮希都日古低声交谈,又犯糊涂了。
东胡明明在备战,他们为何要歪曲事实?
这可是关系到匈奴生死存亡的大事呀,他们竟然如此草率?
贺木额日斯暗自决定,自己只要能够脱身,必须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死亡之地了。
最好还骑那匹宝马,那马的脚力快,他们发现我离去,即使想追我也是望尘莫及。
凭我的身手,到了东胡,一定能受到重用。
到时候我带兵来攻龙城,赫连安其尔还能不是我的人吗?
贺木额日斯暗自胡思乱想,赫连哈尔巴拉与挛鞮希都日古在低声商量着什么,他一句都没听明白,也无心去听,似乎他们的话题也与自己无关。
贺木额日斯窝窝囊囊在挛鞮希都日古的房子里度过了漫长的冬夜。
挛鞮希都日古一大早便出去了,贺木额日斯又熬过了大半个白天,才看到挛鞮希都日古迈着意满志得的方步回到自己的屋子。
挛鞮希都日古对贺木额日斯说:“我已禀明单于,并经过独孤敖嘎同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龙城的副总管,也就是我的助手了,从此再不受独孤敖嘎的约束。”
贺木额日斯的心态还没有从恐惧中回过味来,听挛鞮希都日古说要让他当助手,心中顿时一喜。难道自己是在做梦?
只听挛鞮希都日古又说道:“阏氏已经说了,只要你忠心服从阏氏的指令,等呼德在正月聚会上当上单于以后,就让你做匈奴的大将军兼龙城卫队总指挥。”
贺木额日斯欣喜若狂,诚惶诚恐,激动得身体再次颤抖起来,说:“只要您和胭脂吩咐,额日斯愿意赴汤蹈火。”
挛鞮希都日古淡淡一笑,说:“那就好。现在,独孤敖嘎和万俟腾和已经离开龙城,他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了。”
贺木额日斯正要满心欢喜地离开,挛鞮希都日古又喊住了他,说:“你今天准备一下,明天一大早率人去拉盐吧。我已向单于明说你去拉盐了,拉不回盐不好交代。再说,你现在呆在龙城也会惹出事端来,还是避一下风头的好。”
走出挛鞮希都日古的屋子,贺木额日斯望了一眼正在西下的日头,心里好生得意。
回想一日来的经历,贺木额日斯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
昨天晚上还命悬一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龙城的副总管,下一步还要接替独孤敖嘎当上匈奴的大将军,真是天上人间了。
贺木额日斯抬头望了一眼龙城后面高高的祭坛,心想,一定是上天爱我之才,不忍让我久居人下,让我飞黄腾达了。
想到此,贺木额日斯的脚下便有些飘飘然了,趾高气扬地迈着方步向自己的居室走去。
路过龙城大门边上,贺木额日斯突然想起,这两个兵士昨天曾经嘲笑于他,便走到门边,呵斥道:“你们是怎么立岗的?站没个站相。”
回到自己的房间,贺木额日斯突然觉得这房子实在是太小了,将来怎么也得让赫连安其尔住上宽敞的房子。
一边想着,困意突然袭来。
从昨天至现在,贺木额日斯一直在生死线上翻跟头,根本没心思睡觉。
现在不但闯过了难关,还青云直上了。
贺木额日斯舒心地笑了,点旺了火盆,拉开皮被,很快便进入了甜美的梦中。
突然,皮被被人粗暴地揭去,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猛地将贺木额日斯拎了起来。
贺木额日斯睁眼一看,独孤敖嘎正愤怒地盯视着他,站在独孤敖嘎身旁的是万俟腾和。
贺木额日斯大惊失色,不知是做着噩梦还是在现实中,心都快要冲上喉管从嘴里飞出来了。
“你说,你到东胡究竟探得了啥消息?”独孤敖嘎仍然拎着贺木额日斯的前胸,喝问。
贺木额日斯被独孤敖嘎拎着,早已经惊魂天外,哪里还敢说谎话,结结巴巴将真相告诉了独孤敖嘎。
独孤敖嘎义愤填膺,骂道:“你个下贱的东西,为着一个女人,竟然连匈奴的命运都不顾了。我真是瞎了眼,怎么会看上你这样猪狗不如的东西。走,立即随我将真实消息禀告单于。”
贺木额日斯被独孤敖嘎和万俟腾和夹在中间,哆哆嗦嗦向头曼单于的宫室走去。
独孤敖嘎仍然难平心中之气,不住口地骂着,不时用脚踹向贺木额日斯。
贺木额日斯像一条被人牵着的癞皮狗,可怜巴巴地向前挪着。
头曼单于正与赫连哈尔巴拉、呼德、赫连安其尔和挛鞮希都日古一起用餐。
挛鞮希都日古的一则笑话还没有讲完,便看到满面怒容的独孤敖嘎推搡着贺木额日斯走了进来。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出乎屋里人的预料,欢乐的气氛顿时被打乱,人们的目光都同时盯向涌进来的三个人。
挛鞮希都日古大惊,感觉要坏事,身子不由得向后退了退。
赫连哈尔巴拉反映迅速,款款站起身来,“哎哟”一声,说道:“是贺木额日斯呀,真是精干利落,这么快就完成任务回来了?敖嘎将军,你不是已经同意贺木额日斯做龙城的副总管了嘛,又后悔了?怎么那样毫无礼貌地对待龙城的副总管呀。”
独孤敖嘎怒气冲天,也不去听赫连哈尔巴拉说了些啥话,又将贺木额日斯向前推了一把,喝道:“还不赶快将你在东胡看到的真相告诉单于。”
赫连哈尔巴拉同样柳眉倒竖,对着贺木额日斯喝道:“贺木额日斯,你现在是龙城的副总管,将你的腰板挺直了,干嘛要受人要挟。”
贺木额日斯猛然警醒,知道这是赫连哈尔巴拉在给他暗示,如果他坚持不说真话,就会有人替他说话。
反之,将是死路一条,头曼单于、独孤敖嘎、赫连哈尔巴拉三方谁都饶不了他。
想到此,贺木额日斯朝赫连哈尔巴拉望了一眼,立即从赫连哈尔巴拉的目光里看出了内容,更加心领神会,身子向挛鞮希都日古身边靠了靠,侧身问独孤敖嘎:“你让我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