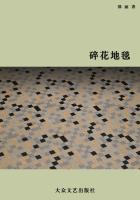雷远也笑:“那是。这丫以前不说话,特别是打球的时候,要说只说四句,篮板是我的,篮板都是我的,你们谁也别和我抢,抢也抢不过。”
陆程禹一本正经道:“就算这会儿出去打,篮板也是我的,”话音未落,三人都笑起来。
雷远摇头:“老了老了。”
陆程禹对雷远说:“你还行,不算老,这会儿又换人了,还是90后,和你没代沟。”
“嗨,”雷远压低嗓门,“玩玩呗,谁还当个真,现在的小姑娘个个勇猛,玩得起。”
许可问他:“怎么着,你和关颖彻底断了?”
雷远说:“别提这事,她已经被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了,在外面呆了这么久也不回,我和她是很有默契的,各玩各的,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许可听了这话,似乎想到什么,有些儿走神。
“不像你,”雷远看他一眼,“人生苦短啊哥们儿。”
许可低头一笑,没搭话,却问陆程禹:“怎么不带家属过来,上次我去北京办事,也没能参加婚礼。”
雷远听见这话,不由意味深长道:“你当时真该来。”
许可不解其意。
雷远看了眼陆程禹,思来想去,最后仍是忍不住说出口:“咱们这儿也没外人,有什么我就直说了,陆程禹你丫也挺狠的,你和李初夏都快复合了,怎么又和别人搞出个孩子来,马上奉子成婚,还让人来参加婚礼。”
陆程禹随意呷了口酒:“我没让她来。”
许可对雷远道:“婚都结了,没啥事别提想当年。”
雷远对许可摇头:“你不知道,”他看着陆程禹,“你老婆当初为什么和你结婚,你又不是不清楚,她说的那些话可是铁板钉钉的。要不是咱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也不会多这个嘴,反正现在孩子也没了,李初夏那边还等着你,你俩是大四开始的谈的吧,认识多长时间了,谁对你真心谁对你假意,你难道看不明白?”说话的当口,他已经在旁边踱了好几圈。
陆程禹抬眼瞧他,问:“你见过她了?”
雷远说:“是。”
陆程禹说:“以后别见了,见了也别谈以前的事,这事儿你管不了,没人管得了。”
雷远点头:“我不该插这个手,但是我心里不痛快。我和李初夏也算是朋友,因为你才认识。那会儿几个常在一起的,要么出国了,要么退学了,我是一路看着你们走过来,她心情不好有时候会找我发牢骚,好几次因为你小子在我跟前哭得稀里哗啦,还不让我跟你说,在你面前又装得没事人一样。别的不说,人也是挺懂事挺体贴一姑娘,这几年等你等成了老姑娘,你把她和那谁放一起比比。是,涂苒也不错,长得那什么确实不错,但是李初夏要长相有长相,要学历有学历,家庭条件也不用说你是知道的,平常兔子都不敢抓,人为了你跑去学临床,这次又跟着你一起出国,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陆程禹不置可否:“她现在已经转内科了,儿科内科,”他拿起酒杯晃了一晃,仰头吞下小半口酒,漫不经心道,“涂苒也没那么差,还是有优点的。”
雷远接口又说了一遍:“也就是长得不错。”
陆程禹没搭理他,想了想才说:“省事,不闹腾,基本不教人操心。”
四人吃了饭,上牌桌切磋。
雷远小赢几把,有次还拦了小对象的清一色。
小姑娘不干了,说:“牌品见人品,三个人里就大叔你最没意思了,”她指了指许可道,“学学这位,要整就整大的,小的人不屑玩,一看就知道是做大事的。这位……”她又指着陆程禹,“出牌干净利落,一点也不脱离带水,记忆力又好,铁定是个喜欢算牌的主……”
雷远无所谓:“小和也是和,积少成多嘛。”
许可却说:“别看人年纪小,还有些见地的。”
雷远骂了他一句:“表扬你就是有见地了?”
那姑娘见陆程禹不说话,只管看牌,就托着腮帮子一个劲瞧他:“这位哥哥呀,是不是外科医生都像你这样气质又冷长得又帅呀?”
陆程禹放了一张牌出去:“比我冷的很多比我帅的没有。”
雷远又骂一句:“长得越帅越是庸医。”话音才落,就听家里的电话一个劲儿的响,雷远跑过去一看来电显示,表情有些得瑟,远远地冲着陆许二人比划了个口型,约莫是“关颖”两个字,接着就在那儿小声接了。
陆程禹这会儿才想起要给涂苒去个电话,先前只说不过去吃饭,却没说上哪儿睡觉,单身久了,也没跟人交代行踪的习惯。他起身从外衣口袋里掏出手机,上面有两个未接来电,手机静音,一直也没发现。
他看了下时间,仍是拨回去,那边很快接起,涂苒一嗓子困顿疲沓,也没问他在哪儿,“喂”一声后便不说话。
陆程禹直接道:“今天有些晚了,我就不过去了,明天一早还要上班。”
涂苒说:“那边的房子收拾好了,你早点休息,别折腾得太晚,”她顿一顿,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
陆程禹想了想:“你以后搬过来,上班还挺远。”涂苒没做声,他又说:“你要是想搬,我周末过去帮你,这几天事儿多。”
“嗯。”
两人都沉默一小会儿,又同时开口:“晚了,早点休息。”
陆程禹挂了电话,再看时间确实晚了,勉强摸完两圈麻将告辞,众人皆散。
他回到新住所,开了灯,一眼又瞧见桌上的相框。上次过来收拾,那儿还搁着一只碗和三根点过的纸烟,现在被人换成了小香炉,炉子里上了三炷香,香已燃尽。
陆程禹看了几页专业书练了会儿哑铃后,才去冲澡睡觉。
浴室栏杆上搭着簇新浴巾,衣橱里的衣物已分门别类安放妥当,床头的台灯有人给重新换了灯泡,床上被褥干净齐整。他适才喝了酒,现在躺床上有些儿上头,酒意腾起来,在身体里点起一股子燥热,似睡非睡里想:管她愿不愿,就应该直接招来做了再说。
如果有人问他对于婚姻和另一半的期盼,陆程禹大抵一时半会是答不上来的,待到经过一定思索之后说出的答案,十之八九纯属书面化的扯淡。
不是没认真想过诸如此类的人生大计,偶尔感性起来,也会翻翻旧账,然而想得越多越觉索然无味,感情再深厚也会为俗事反目,虽儿女成双,终究一个另起新灶,一个郁郁而终,人性和生命一样脆弱。久了,对于婚姻这种关系,他谈不上有所期盼,也不是毫无念想,只觉得刚刚就好,杯里的茶水不用注入太满,路旁的高树也勿需太过刚强。柔韧不足,刚强易折。
连日来,陆程禹如意料之中忙碌,这种忙碌使生活有了滋味,有人把激情赋予爱情之后的婚姻或者婚姻以外的爱情,有人带着激情投入工作就像赌徒沉迷于赌场。
大医院,男外科医生的岁月总是在多姿多彩之间流逝,既有上手术时的刺激和挑战,也有救回人命的成就感,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医患纠纷,年轻漂亮的小护士、踏实干练的女医生、说话娇嗲女药代。涂苒也是她们中的一员,只是那会儿,她可一点不拿乔,有事说事,直来直去,性子也还爽利。
最近陆程禹觉得,自打他回国,她就有些吊着自己,虽然持证上岗,夫妻生活反倒可遇不可求。
当然这些事儿他也没工夫计较,每天脚不沾地席不暇暖,等到下班的时候,外面的路灯早亮了。
以前读书,他便认定收获和耕耘成正比,如今工作,更加肯定这条硬道理,付出努力以后,得心应手的感觉尤为畅快。
特别是外科这种地方,如果没机会上手术,对年轻医生来讲是件糟糕的事情,即使风险大,过程漫长而劳累,手术来了,人人都抢着做。
矛盾的工作性质产生别具一格的吸引力,促使他的内心始终流淌着激昂的情绪,陆程禹看见李初夏的时候,仍然沉浸在这种情绪里无法自拔,这是回国以来,两人第一次邂逅。
住院部的电梯里有些空旷,陆程禹一进来,李初夏就觉得心里某个角落被塞满了,即使他安静的站在那里,神色寻常言语简短。
两人同窗多年,却只相互点头打了声招呼,然后谁也没说话。
接下来的几分钟看似短暂又很漫长。
周遭的墙面像镜子,李初夏注意到他穿了浅蓝色衬衣,领带搭配得很好,男性的沉稳干练之中,多了从容不迫的书卷气质。
她以前就觉得,身材高大的人,穿板型正式的衬衣一定好看。但是那会儿还是学生没那个闲心,后来他回复单身,想必也缺少每日熨烫衣物的耐心。因而在她的印象里,他一向不怎么穿衬衣,可是人总会改变,不知不觉就变了。
陆程禹心情不错,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思维会更加活跃。他抬头看看前方跳动的数字,视线划过镜子里的李初夏的脸,她总是习惯性的微笑,嘴角轻轻上扬,若有似无。以前喜欢上她,也许缘于惊鸿一瞥,那么多人的操场上只看见了她,那个女孩儿,笑起来眉眼弯弯,明亮端庄,很是难忘。
但是,爱笑的人也多半爱哭,大抵逃不脱较为丰富的情绪波动。
涂苒也爱笑,只是也不见她哭过……是了,陆程禹忽然想起来,她以前做不出题会哭,考试分数不高也哭,眼泪早哭完了,这人一旦变起来,当刮目相看。
电梯“叮”地一声响,陆程禹稍微迟疑,便迈开步伐走了出去。
李初夏习惯性地落在后面,以前是跟在后面,稍稍落下一点。
那时的他习惯拖着她的手往前走,她是典型的慢性子做什么都慢吞吞,他外表沉稳内里却急躁脾气,急性子的人往往主意大,一旦下定决心就无回旋余地,很多时候她没法明白他的想法,却能轻易被他左右。
李初夏望着那背影渐远,不觉有些儿感叹,人总是难以摆脱习惯,现在,她已经习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他。
李初夏跟散步一样走回家,从医院侧门出去拐个弯,没多久到了,近得很。
几幢独立小洋房是租界时期的建筑,被簇拥在新盖的青年楼和教师楼之间,隔着精心修剪过的绿化带,备受瞩目,李初夏的家就在一幢欧式小楼里。
开门进去,她和往常一样把钥匙串儿随手搁在走道的鞋柜上,正转身上楼,又和往常一样被人唤住。
院长夫人一边把钥匙串挂进墙上的钥匙匣,一边问:“又在食堂吃过了?”
“吃了。”
“食堂能有什么好东西,又被你爸说中了,天天给你留饭,天天倒掉,浪费。”
“一时觉着饿。”
院长夫人看着女儿摇了摇头,又轻轻推了她一把:“去,陪你爸说说话,工作就这样累,连陪我们聊会子天的力气都没有了?”
李初夏懒洋洋向后靠着的,被她妈往客厅推一步走一步,院长夫人笑:“我家博士闺女哟,奔三张的人了,还跟个小孩儿一样。”
李院长正靠在沙发上看报,这会儿抬起头来笑眯眯的问:“怎么样啊,小李医生?”
李初夏一下子歪在沙发上,说:“不怎么样,成天鸡飞狗跳的。”
李院长放下报纸:“怎么,又被孩子们吵昏了头?”
夫人忙说:“吵昏了头也比在外科好,咱们还是安稳点好,女孩子整天和那些什么血啊,内脏打交道有什么好的,就是钱多点,又脏又辛苦,咱们也不缺那几个钱。”
老李笑笑,悠悠叹了口气:“你们这些人,哪知道做这一行的乐趣,我是老了。”
夫人摆手:“我是不想知道的,您啊留着自己慢慢乐,”转脸又对女儿说,“你张阿姨给介绍的那个搞税务的,看照片小伙子还不错,你抽时间去见见吧。”
李初夏说:“不见,”隔了会儿又补充道,“才回来上岗,哪有那个时间。”
夫人说:“去见见,工作也不错,家里和咱们也算门当户对的,都是公务员,年龄也大不了你多少……”
李初夏打断道:“最烦公务员,脑满肥肠。”
夫人又说:“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银行的……”
“最烦整天和钱打交道的人,一身铜臭味儿。”
夫人气的瞪她一眼:“你说你不烦什么吧?这种事哪能由着性子来。先见见再说。”
人如果在一处兜着情绪,在另一处就忍不住寻找发泄口,李初夏从沙发上站起来:“不见,没时间,要去你自己去。”说完噔噔噔地上了楼,随后砰的甩上房门。
夫人很伤神,埋怨:“都是你给惯的。”
老李也说:“你给惯的,”拿起报纸来继续看,“哎呀,这小李医生,脾气可不小。算了,随她去。”
停了片刻,夫人低声道:“还想着以前那个呢,指不定这会儿心里正怨我呢。”
老李说:“肯定的。”
夫人说:“死心眼儿,像你。”
老李说:“可不是,这辈子就认准你了。”
夫人又气又笑,拿起茶几上的杂志随手翻了几页:“你说,那会儿我要是不反对,这事儿其实也还过得去。”
老李瞟了她一眼:“看人家出息了,你现在后悔了?”
夫人撇嘴:“能有多大出息,你们医院里,这样的小医生成把抓。”
老李搁下报纸:“要我说,还真没几个这样的,我以前带过他,上手术的手有意放手试了试,年纪轻轻的,不得了,基础扎实,胆子也大,敢下刀,是个聪明孩子,难怪何老看重,现在是人才,过几年就是个人物。就你那眼光,不行,没你女儿的好。”
夫人说:“那是,要不怎么找着你了。再好的,这不已经结婚了嘛,”她顿了顿又道,“听说找了个卖药的,还是奉子成婚,这样的人能好到哪儿去?一个女的做那一行能好的哪儿去?物以类聚。所以眼光要长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些事你们男人不懂,女人找老公未必要找个能干的,能力上过得去,最重要是贴心,有啥事都能把自己老婆孩子放前头,那就是好男人。现在的男的比不得以前,比女孩家还怕吃亏,都精明着,男人太聪明能干了,未必罩得住,我是不想你姑娘以后活得累。”
老李不想争辩,只说:“外科的小年青们,工作压力大了,个人生活放纵的也是不少,比不得咱们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