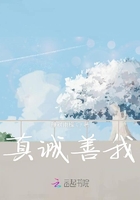对自然的审美必然刺激着美的创造,导致自然美艺术的产生和兴盛。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集中概括,自然美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有力地标志着自然审美的自觉。我们翻阅六朝的诗文集,便可发现,其中表现自然美的诗、赋、文章数量之多,前代无可比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此时出现了独立描绘自然美的田园诗、山水诗和山水画。陶渊明的田园歌咏,虽然以农村生活风貌和他个人的躬耕体验为基本内容,但其中确也有不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对山水、草木、花鸟的描写。如果说陶潜的田园诗由于政治和文风等原因还难以在当时广为流行的话,那么以二谢诗歌为代表的山水诗,却酿成了风靡一时的艺术风气。二谢特别是大谢的山水诗,虽然不时流露出追求感官享乐的颓废情调,但由于他们受当权士族排斥,具有“贵不屈所志”(《游岭门山诗》)的抱负和“得性良为善”(《游山》)的情趣,因而此情寄于自然风物,仍然能在诗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审美。就今存的文字资料判断,六朝的山水画不仅存在,而且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否则,就不会有顾恺之“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的分类,也不会有宗炳《画山水序》的专门概括。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水”的事实,更有力地证明了山水画的普及。仅据不完全的统计,六朝山水画家就有顾恺之、宗炳、王微,夏侯瞻、戴逵、陆探微、谢庄等十余人。当然,自然美艺术决不仅限于诗画。梁简文帝《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千音写凤,百戏承云”的诗句,说明自然美已进入音乐、舞蹈领域。其次还有园林艺术。园林中的树木花草虽为自然物,但被人工移植于园囿之中,与建筑相映成趣,就兼具了艺术创造的性质。《洛阳伽蓝记》向我们展示了魏晋以来显贵们“争修园宅,互相夸竞”的盛况;“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室芳树,家家而筑,花树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松冬青。”及到六朝后期,就更是“园林多趣赏了”。
“自觉”一词,本指人对自己有所觉察,后引申为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以进入自由领域。因此,某一事物“自觉”最重要的标志,是形成关于这一事物的理论,并以之指导此事物的实践。同样,自然审美意识自觉的最高标志,也是自然审美理论的形成。这种理论,在六朝应运而生了。六朝自然审美理论的特点,是表述自然审美实质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陆机、葛洪、刘勰等人的文论,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姚最等人的画论,锺嵘的诗论,对自然美及其艺术表现均有角度不同的论析。此外,成公绥、谢灵运等人赋写自然的文章,六朝许多歌咏自然的诗章,以及《世说新语》的有关片断,也时有论及自然美的观赏、艺术创作和鉴赏的精思妙语。而且大多数论析,都能抓住物性与人情、形美与神似、实感与韵味等关键问题展开。其中,尤以宗炳山水画论和刘勰的自然美文论最为完备。
宗炳的《画山水序》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山水画论。文中“山水以形媚道”的命题,一语点明了自然美以形式美取胜的特征;“应目会心”、“神超理得”的表述,又准确勾画了自然审美的心理过程;而“万趣融其神思”、“畅神而已”的结论,更是抓准了自然审美适趣、动情的本质。刘勰《文心雕龙》的某些篇章,以朴素的唯物思想作指导,围绕“物”、“情”、“辞”三者的关系,对自然美的艺术创作做出了更富美学色彩的理论概括。如《物色》篇就提出了“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自然审美论纲。在这一纲领的统摄下,他认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描写自然是“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他既不废“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的形似,又认为“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因此,他主张“入兴贵闲”、“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其他,如要求“宛转附物,怊怅切情”(《明诗》),“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诠赋》)等论断,也都合理中肯。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六朝毕竟是自然审美初步觉醒时期,理论概括不可能很全面、系统和深入。这正象一个刚刚站立起来的孩子,还难以对自我进行深刻的心理反省。
自然审美意识为何恰在六朝觉醒?回答这个问题应是一篇专论的任务。这里只能据笔者管窥蠡测作个极为简略的回答。我以为,自然审美意识觉醒最深的根源,当然还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既深且广地认识了自然的众多属性及其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复杂对应。当然,由此到自然审美的觉醒,又不能不经由许多复杂的中间环节。其中之一,是六朝士族由城镇坞堡到山林庄园生活环境的转换。山林庄园的自然风物为自然审美提供了理想的对象。恩格斯曾写道:“站在宾根附近的德亨拉菲尔斯或罗甫斯培克的顶峰上观看的景物——这便是具有形体的基督教。北德意志的荒郊,表现了犹太人的世界观。”此论从哲理的高度,揭示了外在自然与人类心灵的某种程度的对应。此论与我国古代所谓“江山之助”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确实,明丽而富于变化的江南风光,也叠印在古人的心扉,引发起人们爱恋与冥想的陶醉。此外,魏晋以来,“士”阶层的扩大,失意士人的增加,避市远祸、复归自然意识的增强,也促成了自然审美意识的觉醒。许多文人每将山林与市朝对立起来,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疲策倦人世,敛性就幽蓬”,就流露了这种情绪。当时的人又多信奉玄学,继承老庄匿迹山林的思想,“望岩怀逸许,临流想奇庄”,将怡悦山林与游心泰玄结合起来。时贤每言山水诗是对玄言诗的否定,但确切些说,“山水”是对“玄言”的辩证扬弃。“玄言”之不乏风景,“山水”之“时遇理趣”,就证明着二者的藕断丝连。除以上条件,佛教的流行,佛徒“山栖木食”生活所酿成的“集岩水之娱”的意识;为适应农业开发、商业贸易而大量进行的对山川草木的地理学和植物学考察,也都有力刺激着自然审美意识的觉醒。探讨六朝自然审美自觉的原由,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审美意识的特征。
二、六朝自然审美的基本特征
由上可知,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通过复杂的中介环节,酿成了六朝自然审美的觉醒。这一审美意识的核心,是丰富多采的形式美与人的情趣、个性、人格的交应契合。下面试从四个方面,探究它的重要特征。
(一)外物与自我的齐一
“物我齐一”本来是庄子的思想。他认为,只要达到“万物与我为一”,就“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但庄子的“齐一”是消极的顺从,而不带主观意志,所谓“外物不可必”。六朝的“齐一”意识,虽然借用了庄子的思想资料,却经过了改造。这主要表现为人的能动性增强了,人在对自然美的观赏中力求达到以我为主的“物我泯然同体”。
物我齐一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对自然的“环境”意识增强。自人类出现之后,自然就是人类环境的自然。但由于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难以驾驭自然,人们便容易把自然看成超自然的异己力量。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人们对自然的“环境”意识也与日俱增。在我国,这种“环境意识”似乎更为强烈。在六朝,士人清谈就往往将“土地人物之美”相提并论。孙子荆就这样介绍其家乡风貌:“其山巍巍以嵯峨,其水甲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当时画人物,也多注意配置适当的自然背景。顾恺之画谢幼舆,周围巧布岩石,只因谢有“一丘一壑”的山林之趣,因此“此子宜置丘壑中”。有人画嵇中散啸歌,也辅之以“林木雍容调畅”的背景。歌德说:“在他们那里(指中国——引者),……自然外境总是和人物形象相联系。”也许是旁观者清吧,他以特有的敏感发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这一特色。确实,我国的自然美艺术,不管怎样洗炼,如何清空,总是较富于人生情味,而极少象西画那样,物象近乎生物学的机械描摹,也不象有些现代派绘画那样狂放地突出自我,而是始终保持物我交应的合谐。
物我齐一的另一特点,在于以情为灵魂的触景生情和怀情感物。《文赋》所谓“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就是对此的生动概括。前者是触景生情,后者为怀情感物。这一特点见之于诗歌创作,常常表现为运用拟人、象征等手法将物人格化,或运用夸张等手法使抒情主人公挥斥外物。前者如“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后者如“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而有时甚至表现为主人公与自然物的倾心交谈。陶潜《拟古》之三就这样询问新燕:“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主人公此时已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燕了。而在一些神话和传说中,又常常借幻境、幻化等形式表现物我的感应。《韩凭夫妇》的故事,结尾就令韩凭夫妇的精魂化为一对鸳鸯,“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当时,有人对物我齐一的这类艺术表现难以理解,刘孝仪《咏石莲》诗就发出了“不解无情物,那得似人心”的疑问。同时代的人回答极妙:“但使心齐物,何愁物不齐?”对自然美的观赏和艺术表现,决不是镜子似的复映,而是倾注着创作主体的心血,因而才能使物色带情,达到“素志与白云同悠,高情与青松共爽”。自然审美的这种感情贯注,古今中外艺匠哲人均有发现。老托尔斯泰看到克拉兰的湖光山色,便“立刻觉得想要爱”;阿米尔则惊叹:“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相似的宏论,反映着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结构。不过在同中仍有不同的民族表现形式。
物我齐一的纽带是主体的感情,感情的性质和状态制约着物我的齐一。从六朝自然审美史实可以看出,那些情趣健康、人格高尚的人,往往对自然美特别敏感。陶潜洁身自好、知足寡欲,其高情逸趣便能与自然美景交感融汇。他在“树木交荫,时鸟变音”的美景前“欢然有喜”,“依杖久听”田水声,叹其“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和郭主簿》、《归园田居》等诗对山水、田园的描绘,倾注着他多少深情啊!在这里,那些高山、白云、青松、芳菊、凉风、清荫似乎已成为他亲密的伴侣,招引着读者的无限思慕。魏晋以降,能“师心”、“使气”、坚守高风亮节的人愈来愈少,但也不能说举世皆浊。以山水驰名的大谢、小谢,就清风尚存。他们都是有志有才而难逞其能的人,因而那模山范水的清词丽句,每每隐含着他们的情趣和怀抱。白居易评大谢诗“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不能不说是破的之论。灵魂空虚、精神贫乏的人,殊难产生自然审美。梁陈期间,士人大多情昧操低,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的“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每每沦为声色狗马之乐。“自我”的贬值乃至丧失,意味着外物对主体的拘役和压迫,结果必然导致物我的分离,审美的破坏。
(二)形似与气韵结合
对自然美的观赏和艺术创造,不可能脱离具体物象、外在形式。中国古典艺术重在表现,但这表现又从来不脱离再现。所谓“形立则章成”,没有“形”,也就没有“文”和“美”。审美中重视形似,表明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更加深细,是人类认识的一大进步。当然,停留于形式也难以构成审美。只有当自然物的外形式美与某种神韵相结合,充溢着一股蓬蓬勃勃的生机和气势,进而体现一种人生情趣时,审美的桥梁才得以搭起。南朝人一般把这种生机和气势称之为“气韵”、“神气”。钱锺书先生据他对《古画品录》的新断句,认定“气韵”就是“生动”,即画中“栩栩如活之状”,甚为确当精辟。当然,“气韵”与情趣也有密切联系。
总起来看,六朝自然审美,力求形似与气韵的统一。王微《叙画》所谓“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谢赫《古画品录》归纳的“六法”,王僧虔《笔意赞》所说神采、形质“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刘勰、锺嵘、颜之推诸人的有关文论,都表述了这一意识。窥其大势,可知整个六朝偏爱形似已成时代风尚。绘画追求“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目想毫发,皆无遗失”;诗文也“功在密附”、“曲写毫芥”;民歌则重“妖而浮”的吴声。但有学识的文人学士却不为时风所拘,力倡形似、气韵的统一。上列数家就是如此。《古画品录》就极重二者的结合,认为“纤细过渡,翻更失真”,对“似”与“不似”的辩证关系已多所领悟。此间的优秀诗人也都在努力实践着这种结合。只不过是“时俗如此,安能独违”罢了。但这种形似、气韵结合的美学思想,毕竟成为我国古典美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以风景画而论,我国既难见到仅仅显其光影变化的、单求形似的作品,也决无某些现代派画家那样肆意变形的画作。
六朝期间,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自然界“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因而对于自然形式美的感受、观赏益加细致、深入。《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司马太傅与谢景重一起赏月,就曾发生月明无尘和微云点缀何者为美的争论。这种情况反映到山水艺术创作中,便出现“巧构形似之言”、“尚巧似”的倾向。大家所熟知的南朝民歌《采莲曲》,对鱼儿在亭亭荷下东南西北窜游的生动描绘,不就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物特写吗?而《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勾画,则完全可以看作从远近高低不同视点描绘的水墨风景,是声、色、味俱全的田园交响乐。拿这些作品与《诗经》对比,可知对自然物描绘的具体、形象、细腻确是大大发展了。当时山水画的失传,使我们难以考察其形似水平。然而卫夫人的《笔阵图》,在“通灵感物”基础上,用坠石、犀象、枯藤、雷奔“形容”点、撇、竖、捺,却使我们看到了自然审美的形似已渗透到书法领域。
已如前述,“气韵”就是“生动”,也即突现一种生机勃勃的美。那么,六朝的“气韵”是一种什么格调呢?诚如李泽厚所言,魏晋历史画卷展示着“人的主题”。六朝(特别是前期)期间,人格的觉醒,个性的勃发,给自然审美贯注了一股盎然生气。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叹天地之辽阔,逞人类之主宰,其“高情属云天”的乐观格调,不正透示出人类“自我”初步觉醒,力图向自然索取更大自由的强烈意愿吗?顾恺之形容会稽山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水经注》描状夷水风光“夹峰高山,犹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指直,千百成峰”,不都体现着一种活泼灵动、生气蓬勃的气韵吗?统观六朝自然审美,可知这恰是一种时代的气韵。这一气韵竟也在最抽象的书法艺术里鸣响:“鸟企龙跃,珠解泉分,轻如远雾,重似崩云,绝峰剑摧,惊势箭飞。”陶潜等人的田园山水诗,民歌中的风景描绘,也无不充溢着这种气韵。甚至玄言诗中的某些写景句,在平板中也跃动着一丝汩汩的生命潜流,而决不是心如死灰。在对自然形式美的观赏中,充溢着蓬勃的生气和顽强的求生意志,这又是我国自然审美的一大特色,而与西方现代风景某些一味麻醉自我、诅咒社会人生的消极情绪迥然不同。
(三)应目与会心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