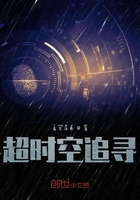可恨小周氏眼拙嘴贱,这会儿才发觉她不是窅娘,倘若昨日上了凤辇被召去嘉瑞殿的人是窅娘,今晨窅娘恐是都没命活着回来这宴春阁。想是小周氏倒乐得为窅娘收尸。
永宁摘下了纱笠,掷向小周氏脸上。
小周氏惊跳:“你,你是……”
“不识吾了?”永宁又逼向前一步。
“不……怎地会是你!?”小周氏惊遽的连连倒退了几步,撞在李煜身上。
李煜的心神正落在永宁身上,一时扶小周氏不及,小周氏珠履一绊,踩在她曳地的裙裾上,向后绊跌在地上。
“你这般惊怯作甚?适才不还厉声叫骂,要与吾问个究竟!”永宁步步逼近小周氏,“吾便在这儿,你有甚底好问的,今日便当着阿兄之面,索性问个明白!”
“不,你不是……窅娘呢?窅娘……”小周氏惊颤不能自制,惶然扯住李煜的衣摆,“是你欺了我!你说她已命丧黄泉!”
当日金陵城破,城内百官士民皆流传江南公主葬身在了鼓楼火海之中,尸骨无存。为此,这一年多,宋.庭无人追查此事。
“是十殿阎王不收我……”气血上涌,永宁喉间又是一甜,硬是咽了下去,“你可知,吾在阎罗殿遇见了何人?”
她俯下身,逼视着小周氏:“昭惠国后托吾捎个话予你,她道自家人只你一个姊妹,甚是挂心于你,她带着瑞保在阎罗殿会等着你!”
“瑞保?”小周氏死死拽紧李煜的衣襟。
“可不是瑞保怎地?”永宁扯起笑味,凤眸沉痛,“你可还记着瑞保?瑞保三岁,诵孝经不遗一字,宫中燕侍合礼,如在朝廷,昭惠国后尤爱之……他四岁那年,一日戏佛像前,有大琉璃灯堕地,哗然作声,因惊得疾,竟卒,其时昭惠国后已疾甚,闻瑞保夭,悲哀更遽,数日而绝!”
“不是我,非是我害了他!不干吾之事!”小周氏矢口狡赖,惊疑的面无人色。
“是么?大琉璃灯岂会无故堕地?”永宁句句紧逼。
“是、是为狸猫所触……”
“宫闱森严,何故有狸猫?佛堂净地,狸猫乱窜,岂非蹊跷?”
“吾……吾怎知?”
“你不知?”
小周氏支吾其辞,永宁越发笃定当年她所猜疑之事:“阿兄笃信佛法,虔诚礼佛一百拜,日供千僧,于宫中筑永慕宫,又于苑中筑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崇修佛寺,昭惠国后亦非不敬佛之人,佛前大琉璃灯却堕地,祸及黄胄,岂不悲哉?”
周娥皇生前,为李煜诞下两子,长子仲寓,次子仲宣,仲寓年长仲宣三岁,仲宣小字瑞保,永宁和他相差一岁,因她不足月就诞降,身子骨羸弱,李璟崩不过半载,钟太后悲恸过甚,无暇照拂她,于是将她交由周娥皇看顾。
永慕宫发生祸事那年,永宁刚长及三岁,正是蹒跚学步之年,那日仲宣趁着周娥皇午憩,正要去永慕宫为周娥皇荐福,不巧被永宁发现他要偷溜出瑶光殿,她拉着他的衣角也闹着非去不可,仲宣生怕她哭闹再吵扰了周娥皇养病,便与她约法三章,才应下带她同去。谁也不曾想,进殿后二人合上殿门,她学着他一步一跪也从门内跪向佛像前,殿顶的大琉璃灯突然间竟堕下,仲宣护着她躲向一旁,把她挡在了身下,他却被砸伤昏迷了三日,受了惊吓。
小周氏犹在惊恍中,永宁质诘道:“瑞保自小仁孝,昭惠国后抱病在榻,他见日去永慕宫,在佛前求祈,莫说你不知!当日你做了见不得人之事,便不怕冤死之人向你索命!”
“不!”小周氏霍地坐起,浑身颤栗,怒指永宁,“是你!你莫忘却,曾有华山老道为你称骨算命,你命中带煞,刑克父母,天煞损六亲……”
她反口暴跳,永宁微怔,却听李煜截口制止道:“这话未确,切莫过言!江湖术士之言,姑妄听之,又岂可尽信?”
小周氏摇摇晃晃站定身,扬起下巴,冷笑一声:“既是不经之谈,国主何必讳莫如深?不允宫人谈说此事?”
永宁咄咄逼人,李煜视之不见,她反斥永宁,他立下就护短,小周氏的恨意被激起,她一指永宁,恨愤道:“若她不是个命硬的,何以先帝才迁都南都,泛舟孺子亭,便因她母女二人暴死?江南多风调雨顺,五谷丰熟,而她一诞降,金陵便大旱了两年!其母亦因她……”
“莫再说了!”
李煜怒声喝断了小周氏,扬起了手。
看着他的大掌扬起在她头顶,小周氏眸中恨意更重:“国主这是又要打我么?”
永宁从未见过李煜发这般大的火,她看了小周氏一眼,拉下李煜的袍袖:“阿兄,且由她说下去。”
交泰元年(959年),李璟升洪州为南昌府,并于961年将都城从江宁迁往南昌,号“南都”,同年,立李煜为太子,令其留在金陵监国。六月里,李璟崩,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仲宣即生于此年,而她是次年春正月诞降,永宁一直以为李璟是病故在南都,可今日小周氏一席话,言下之意,李璟之死听似竟是另有隐情,那华山老道的相骨之语,这十几年来永宁更是闻所未闻。
“奇谈怪论,闳大不经!无稽之言,言它作甚?”李煜拂袖背过身去,好半晌才转过身看向永宁,怒气微敛,“且不说旁的,此是怎地一回事?窅娘、黄氏现在何处?”
他问及黄氏、窅娘,永宁这才想及她还欠李煜一个交代,她与小周氏争一时之气,差点误了大事。但小周氏刚才所言之事,她亦想弄明真相。
“阿兄……”
“你连为兄的话,也疑虑了?”
她闷着声一开口,李煜就看出她心生疑惑。他看着她年愈长大,怎会不了解她的性子。
永宁垂下眼眸,话到嘴边却变得难以启齿。有些事,她被蒙在鼓里,可见是李煜刻意隐瞒了她。
其实,她何尝不也瞒了李煜一些事,永慕宫那件事,时到今日都没人知晓那盏大琉璃灯实非是狸猫所触堕地,当时大殿乱作一团,她也吓得嚎啕大哭,在被宫人抱出殿时,她却瞥见了一个青碧色的身影从佛像后趁乱一溜风奔离……小周氏贯喜身服青碧色的衣装,若非她所服的衣装均为青碧,李煜也不至于为**她而满宫竞染天水碧。
周娥皇母子相继离世,本就令李煜痛不欲生,那时她年岁尚小,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仲宣,待过了几年开了人事,她又不忍再让李煜负疚成疾,故才瞒下,即便是春桃,亦不知她藏在心底的这个隐秘。今日倘不是小周氏激怒了她,永宁也断不会提及这桩事,旧事重提,她虽是在质疑小周氏,却也是在剜李煜的心痂,没成想竟逼得小周氏泄露了她并不知情之事。
春桃搀扶着窅娘急赶到宴春阁时,转进庭院就见窅娘寝房的门扇大开着,二人往黄氏的房里看去,便看到李煜、小周氏竟都在黄氏房中。
“公主!”
一见永宁亦在,春桃悬了一路的心才算落下。路上就听见有嘴碎的宫婢聚在一块叽咕昨夜嘉瑞殿燕乐了一宿之事,这宫中没有不透风的墙。
抬头看见她二人走进来,房里的人多少都有些诧愣。
窅娘颊上还敷着那张面皮,永宁自是识得出她,李煜和小周氏却不识眼前人就是窅娘,但却认出了春桃。
“奴见过国主。”春桃对着李煜礼道,亦朝小周氏礼了礼。尽管她对小周氏也有颇多不满,但小周氏怎说亦是李煜曾册立过的南唐国后。
“你二人怎地过来了?”永宁心头涌上不祥的预感。
“公主……”顾不及见礼,窅娘急急步了过去,紧握住永宁的手。她这一出声,李煜眼中划过丝喜色,显是听出了窅娘的声音。
“可是出了何事?”永宁的手也不暖,只是窅娘的手心浸着凉意,一手心的汗津。
春桃上前,接过了话:“奴二人是打延福宫而来,今儿辰正时辰,众官妇便要谢恩出宫,候不见公主,窅娘执意回来一看。”
“公主,快些出宫吧!迟了,怕是有变!”窅娘说着就要撩落**.帐,与永宁换回衣装。临来时,她就打定主意,若能寻见永宁,定与永宁换回装束。
一.夜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危急关头,却可让人想通很多事。
永宁却站着未动:“黄氏可有回来?”
窅娘与春桃摇了摇头:“昨日一别,便未再见着她。”
永宁若有所思的望向李煜:“昨夜宴散后,阿兄回了宴春阁,可有见着黄氏?”
昨夜李煜在黄氏房里坐了大半宿,卯时才去的窅娘房中,却是不曾见过黄氏。
她略一沉吟,又问道:“阿兄可知,北辽大汗一行人等,此时辰有未回还上京?”照此情状看来,想必黄氏已跟着耶律隆绪出了宫,昨夜耶律隆绪在约定之地没等见她,却没把黄氏扔下,或许事态还有转机。
“昨日曲宴上,听齐王说,今日会于都门帐饮,百官代天子出行,为其长亭饯行……”李煜有些不明就里的说到这,皱眉看向了永宁,恍然有些会意了永宁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