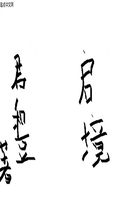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马车上,永宁握着袖下的胭脂盒,不觉百端交集。
与那吕蒙正,此一别,再见无期,许是再无相见之日,有这一面之缘,纯是意外之事。
可以看得出,吕蒙正是个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之人,它日若出相入将,亦会为一代贤良之臣。患难见知交,今日之情,待到那时,各为其主,但愿不会步人后尘。
“女人,你姓李名青?”耶律隆绪睨视着她,语带质诘。
永宁垂下眼眸,不予作答。
她与吕蒙正的那一番交谈,想是耶律隆绪尽收于耳。适才在街上,她还真有些怕他当着满大街的人大声唤她“女人”。
她对吕蒙正隐瞒实名,非是存心欺他,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实也是为吕蒙正着想,不想牵累于他。倘若她是亡国公主的事走漏风声,凡与她结识的人多半难逃牢狱之灾,自然,这当中亦有所顾忌耶律隆绪主仆四人。
她不吭声,耶律隆绪挑起了盒面脂,把玩了几下,扔回小榻下的虎皮毡上。
“小王交代你挑两盒胭脂……”他拧着眉毛拍了拍手,一脸的嫌恶,极不喜盒上的胭脂味儿沾在身上,话却只说了一半。
永宁瞟了他一眼,看他眉梢微吊,就像她挥霍了他忒多的银钱,心疼的他不得了,她唇一抿,扑哧竟笑了。
车内的气氛一缓。
耶律隆绪却愁眉锁眼弯下了身,对着那一堆脂粉盒子发起呆来。
永宁忍了笑,垂下眼眸,忍不住又瞥向他,心知他并非就是心疼那俩钱,但瞧着他,愣就觉得解气。
谁让他以小欺大,她便狠花他一笔,送人人情,解解恨。就这她还没直说,她之所以买了这一大堆脂粉,是怕他带回上京不够他那群莺莺燕燕分的。永宁心下憋懑又禁不住漫过笑,耶律隆绪忽地偏着头,看向了她:
“女人,江南国主是你何人?”
他的声音闷闷的,闷声闷气,极易让人错觉说这话的人是在吃味,被人抢了在乎的够深的心爱之物而闷闷不乐。
永宁神色一凛。
只坐了他二人的小榻,气息逼人窒息。
永宁眼中慢慢染上警惕,吃不准耶律隆绪是何意,不敢臆断他是不是猜忌出什么。
“是你的良人?”
他看着她,又甩出一问。
没成想耶律隆绪竟有此一猜,永宁有些哭笑不得。那是她的皇兄,怎就跟她的良人扯上关戈了?
耶律隆绪呐呐着,歪着头斜睨着她:“女人,汉人改嫁,可要休书一封?”
车舆上的卷帘,摆动了几下,车外的冷风灌入,驭夫和那两名甲士就坐在车驾前。
这车内的说话声,坐在车前都能听见。前刻在车上,她跟耶律隆绪争拌了两句嘴,驭夫和那两名甲士就听见了,耶律隆绪唤她下车挑胭脂时,驭夫三人看她的眼神就有些怪怪的。
“女人,小王为你讨一纸休书?”睇眄她,耶律隆绪坐直了身。
他说这话时,狭目浓黑,如墨一般,不像是在顽笑。
永宁屏息凝神,这厮儿的话,有时候确实叫她跟不上节拍……
“那便这般说下了,小王便在今夜的曲宴上,讨了你!”
他像是在诱哄她,直听得永宁越发发愣,讷讷地眨了眨眸子,也没能答上话来。
他说讨了她,他已不只一次的对她说要讨了她了……
昨夜在晋王府偏院的那间寝房,他就说过一次,刚刚他又说了同样的话。
换了哪个女人,亲耳听着一个男人对她亲口说这个,亦真亦假,会不心乱如麻。
永宁握着胭脂盒的十指不觉收拢,莫不是北辽肯助她相救她的皇兄?可是在晋王府,耶律贤并不曾表态。
还是说,他又在戏弄她……
凝睇耶律隆绪,永宁试探着说道:“人若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大汗可是圣心回宥?”
她言外之音,已甚明,是在重提宋、辽逐鹿之争一事。
“父汗?”耶律隆绪懒懒地倚着身,似想了下,才不咸不淡回道,“小王不知。”
他一句话就把她打回了原形,永宁霎时心凉了半截。
“你当问父汗。”
看着她脸色一白,耶律隆绪双臂环胸,轻嗤了声。这女人在他父汗面前都敢强聒不舍,一转身就跟他面前可怜兮兮,当他人小好欺。他的父汗可甚少听人絮絮不休,她却在他父汗面前巧言令色,侃侃而谈了半天。
理该让她尝点苦头。
他的汉人夫子说,女人是拿来宠的,但在他看来,女人可以宠,却万万不可宠过了度。不然,以这女人的不驯服劲儿,她还不把他推出去,拿他用来挡箭!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女人,此话何解?”耶律隆绪又闭目养起了神儿。
永宁眉心蹙起。她在急处,他偏在慢处,他是成心在刁难她。
她钳口不言,耶律隆绪也不催她,往腰带上的算囊里一摸,摸出了那张面皮,而后抽出胡刀。
他持着刀鞘,铮亮的刀尖对准了摆放在刀下的那张面皮。
这把胡刀,刃如秋霜……永宁看得心惊肉跳,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颤着声讲道:“有个穷秀才进京赶考,净顾赶路,错过了宿头。天色已晚,路遇一屠夫,便借宿人家。二人相谈甚欢,颇为投机,屠夫问他,‘万物有其雌.雄,江海之水,哪是雌哪是雄?太山之木,哪是公哪是母?’……”
这厮儿刁狡,未必不知这话何解,可她却不能眼睁睁的任他毁了那张面皮。永宁平复着心绪,劝慰自己只当是给这厮儿讲古了,待马车驶入宫门,她与他也就不会再有任何交扯,她宁可不求他相助。
“秀才一下子被问呆了,只好向其请教。屠夫告之,‘江海之水,有波有浪,波为雌浪为雄,雄弱于雌’,秀才听了连连点头,又问,‘那太山之木,何以有公.母之分?’屠夫答曰,‘樵夫伐木,自是以‘松’为公,以‘梅’为母’,秀才闻言,恍然大悟。”听她讲到这儿,耶律隆绪放下胡刀,压在那张面皮上。
永宁干吞了口吐沫,方又往下讲道:“待到赴考之日,卷上所考之题,正是屠夫所言的雌水雄水公树母树之说,众考子面对考题,两眼发呆,唯有那秀才,一挥而就,一举夺榜,钦点为状元。他荣归故里,便奉上厚礼,书匾赠予屠夫,其上所题之字即‘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直到她讲完,耶律隆绪也没赞一词,反而听得快打盹。永宁咬着红唇,慢吞吞的指了指那张面皮:“少、少主,可否还吾……”
她期期艾艾,他却没应声,连句痛快话都不给她。永宁恨不能扑上去动手就抢,可她却不能这般造次行事。且不说耶律隆绪有股蛮力,这车前可还坐有他的三个随侍,她如何以一敌三。
逃,逃不掉。
打,打不过。
跑,跑不了。
那就只能忍气吞声。
就算趁他一时不备,她逃脱了身,稍迟也得乖乖地跑回来,死乞白赖的爬上他的马车以便混进宫去。
“吕蒙正可会及第?”
她怨艾的垂着头,过了会儿,耶律隆绪倒开口问了句。
永宁抬眼,琢磨了下,才弄懂他话外之意,苦笑道:“吾怎知?”
她又不是那屠夫,吕蒙正也不是那秀才。在街上时,她那些话只是意在激励吕蒙正。
她不答反问,又似怒极反笑,耶律隆绪面露鄙薄,拿起那把胡刀塞入算囊。
那张面皮却留在了那。
他只收回了胡刀。
永宁心下一喜,又不无疑顿的看了他一眼,方鼓足了底气,慌忙伸出手去抓。
可她却乐极生悲了……她向前刚一倾身,搁在她腿上的胭脂盒就滑落了下去。
随着车舆前驶,胭脂盒滚了两滚,不偏不倚滚到了耶律隆绪的衣靴下。
永宁微怔,在一把抓过那张面皮后就连忙折腰去拾胭脂盒。耶律隆绪却已长臂一捞,先于她出手把胭脂盒捞在了手里。
他出手极快,她呆愣愣抬起头看向他时,耶律隆绪已将胭脂盒正过来翻过去看了个遍。永宁欲哭无泪,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刚讨回了一件,竟又落入他手上一件,她可有够触楣头的。
他似是没能看出手上的胭脂盒与堆在虎皮毡上的那四十几盒胭脂水粉有何不同之处,他睇了睨她,她的皓腕还搭在小榻边上,僵着身姿伸长玉颈在望着他。
确切地说,她是在望着他拿在手上的胭脂盒,虔诚至极的半跪在下。
耶律隆绪嗤鼻,索然无味的甩手将胭脂盒丢还给了永宁。永宁狂喜,忙不迭收好胭脂盒。这胭脂盒,其实她也没瞧出什么名堂来,吕蒙正赠她此物,或许并无它意。
瞧着她如获至宝般收起胭脂盒及那张面皮,耶律隆绪扬起下巴:“女人,小王听人说,汴京的目连戏十为有趣!你与小王去看一场,何如?”
永宁刚要松口气,又因他这两句话愣住:“去、去看戏?……宫中今夜不是设了曲宴?”
睇目她,耶律隆绪满不在乎的说道:“父汗赴宴,小王大可不去凑热闹!”
好半晌僵视,永宁气红了脸,气得脸色铁青。
兔子急了还咬人……他这副恣态,说变就变,她可是急于进宫去!都陪着他逛了半条街了,他竟半路上变了心意,不去赴宴改看戏了,这不是把她往绝路上逼……还说要讨了她,都是欺她!
“停车!”
怒从心头起,永宁怒声喊罢,二话没说爬起身就撩起了卷帘。她要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