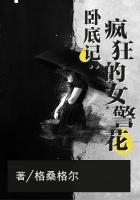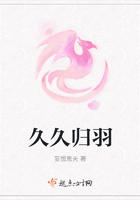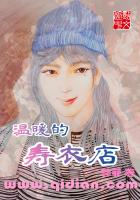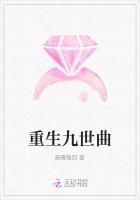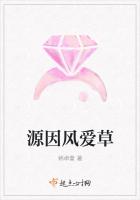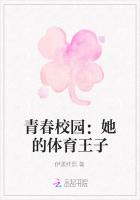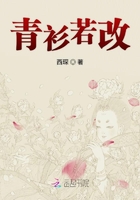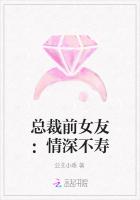三乡下生活
波霸的厌倦,另觅了依靠;母亲的坚持,不愿放的手。父亲回归了家庭,但他还是因为和波霸的那一段不清不楚,受到处分,他被发配到离海边很近、很贫困的村小学任教,将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城市。
母亲终于无法忍受这些,在吴意和昊的面前爆发了与父亲的战争,地上的碎瓷片是母亲气极摔坏的日本磁壶盖,可是这无法平息她的恨。温顺的她爆发了,如同发威的豹子,她动手打了父亲,坚持要离婚,并要求带走昊。此时的这个男人是隐忍的,也许是因为亏欠。
外婆来了,她看着昊和吴意恐惧的眼神、不住地颤抖的像豆芽般的身体,她满眼痛楚地第一次扇了女儿耳光。看着外婆那痛得让人窒息的样子,看着两个无辜的孩子,母亲觉得生不如死:“我不想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离婚!”。
外婆说:“混账!离什么离?什么带昊走?亏你还是个妈,怎么可以在孩子面前说出这些?我没有这样教育过你!不许离!想离,等我死!你们生死都要是一家在一起!”外婆用最传统、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她的决绝:“磊子去乡下,你带着孩子和他一起去,你生是磊子家的人,死亦是他家的鬼!”
那个被称作父亲的人流着泪对着外婆跪了下来:“妈,对不起!谢谢!”父母终究还是没有离成婚。
吴意一家四口在一个飘着鹅毛春雪、冷冷的天,带着一箱箱书、为数不多的家具、日用品来到了陌生的、满是盐碱地的贫瘠的、水咸咸的小乡村。那年吴意6岁,昊9岁,吴意的家里有了双亲,看上去很完整。
村是贫穷的村,房子几乎都是泥坯围成的墙,屋顶上盖着草,正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景象。吴意一家就在这里安了家。这里淳朴、忠厚的人们看着从城里来的吴意一家没有粮食、没有菜,纷纷从并不富裕家里给吴意家送来了需要的食物、用品。那一幕,让幼小的吴意感到从没有过的暖意,直到今天,每每想起在乡下的那些单纯、厚道的人们,依然让吴意感念。
村里的生活很艰苦。村里给吴意家的自留地因为父母不会料理,家里的蔬菜没有办法自给,常常吃了这顿没下顿。这些并没有影响吴意兄妹长大,太阳晨出暮落,日复一日过着。
村里的左邻右舍给予来自城里的这一家人最大关怀,包揽了家里的力气活,吴意和昊学着村里人担负起自留地的种植、养猪、养羊、养鸡、养鸭的任务,慢慢地可以让家里的生活可以自给,两个孩子成了村里人羡慕和夸奖的典范:聪明、懂事、能干、肯吃苦。这年吴意8岁,已经是乡小三年级的学生。
乡下的学校,房子很是破旧、教室光线差、老师多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代课教师。
吴意,城里来的小姑娘,瓜子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忧郁的丹凤眼、高挺的鼻、虽然海风时时吹着,怎么也晒不黑,依然白皙的肤、显得有些苍白的不薄不厚的唇、细细的麻花辫带着一些微黄,瘦弱、清秀。小姑娘因为一口还算标准的普通话、回答问题的准确率高、考试时好看的分数、比同级同学小两岁的年龄,当然长得也漂亮,得到了任课老师们的喜爱。课上偷偷地看《在人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吝啬鬼》等闲书。入神时还会神游,想着高尔基的外祖母对他的慈爱,想着他的外祖父为什么吝啬到泡茶时都要数茶叶?想着保尔的坚强,渴望成为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想着......
老师本着偏爱的心宽容着,权当视而不见。课间,他们常常会悄悄地向吴意借一些如:《家》、《春》、《秋》、《十日谈》阅读。
同学们眼里的吴意,虽然常常穿着哥哥的旧衣服改的,但是洗得很干净,总还是觉得与他们有些不一样,而且寡言、忧郁、不爱笑。
陆乐说:“总觉得吴意身上有股仙气。”
其实吴意不太合群,性格有点孤僻。喜欢在空余的时间看闲书,和同学主动交流不多,甚至显得关系有些疏离,但人蓄无害。同学有不懂找上她的,她也会不嫌厌烦的教,大家喜欢围着她,一起相处得算是相当和谐。
这不,一下课,大个子小芳、陆乐、李静秋围了过来。
小芳说:“吴意,这道数学题我们不会,教教我们吧。”
吴意放下手里的书,拿过本子,仔细看了起来,然后讲解给他们听。
陆乐说:“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做的。”
吴意点点头。
三年的初小,因为学校搬迁,原来班上的同学和老师也一起随迁,早晨吴意和昊都是要步行四十分钟才能到新校,一起随行的有陆乐、李静秋。昊看着在家门口等的他们总有些不耐,“你们怎么又来了?”
李静秋红着脸不说话。
陆乐嘻嘻一笑:“顺路,一起喽。”
这样的风景一周基本是五天,他们都是吴意的伴,这样的友谊也一直延续着。
欧阳清明、江南猪、张楠等等就成了吴意的新同学,这一下不好奇,为什么吴意和欧阳清明他们小学只一起同学了三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