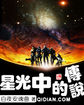春日暖阳,柳树抽芽。十里春风,咋暖还寒。
蒋卓恩紧了紧肩上的竹编箩筐带子,抬头看了看天,头顶苍天大树枝叶繁茂,阳光透过其间细碎的布满了蒋卓恩的视野,蒋卓恩微眯了眯眼,只觉得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心里估算了一下时辰便撒开了腿奔向了山下的凉州大营。
泰成二年那场大尹****入侵凉州带来的突然却短促的战乱,结束于大尹****兵败西平城后销声匿迹。时光荏苒,匆匆已过去三年,时泰成五年。
这场透着无数疑点的战乱随着同样行事诡异的大尹****的销声匿迹而终止,也使凉州重新获得了平静。
搜山找回的那三千余原金城城民跟着分派到金城守备的两万人马回了金城。汇合金城驻守的七千余壁虎军编入新建的凉州大营,三日后八百里加急快马圣旨到,擢壁虎军都尉黎晰鸿校尉职,统领凉州大营,协西平,酒泉知县驻守凉州。
黎晰鸿一战成名。
即使西平之战已过去三年,有幸亲睹黎晰鸿英姿的兵士,每每回味起来都仍觉震撼人心。
却说黎校尉当时就如从血海里爬出的红色魔鬼一般,身上盔甲同身下战马都被血液浸透成了红色,满脸糊了不知道几层鲜血,唯一可辨的双目也早就杀得刺红,就如戴了副血玉面具,势如破竹般无法抵挡的一路冲杀进敌阵,渐近敌阵中心时,周围混战的兵士仿似被这血人般的杀将所震慑,竟是自动避让出了一条路,只见那血色杀将直直冲向破败方阵中心的指挥阵而去,高高举起那同样沾满了鲜血的银枪长啸而入。
黎老将军身边的副将权相职找到黎晰鸿的时候,他已经杀疯了,身下战马不知何时已被砍倒在地,眼前身边都是层层叠叠的大尹国军士死尸,黎晰鸿却还在不知停歇的挥舞着刺头已破损的血色银枪。
这惨烈场景让从前便跟着黎老将军身经百战的权相职,及随他而来的将领们不忍直视。
黎晰鸿最后是被权相职带了人合力打晕了才带回了大军后方,交到黎符手上。待好不容易洗去黎晰鸿那一身血污,才发现他身上竟是除了几处箭伤外没有其他伤口,足可见当时杀红了眼的黎晰鸿有多难近身。
自此,黎晰鸿便得了个浴血杀将的名号,迅速在大臻朝传扬了开来。
这黎府百年将门世家果然不是盖的,连这么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将士都如此了得。
蒋卓恩在医帐外听得白术下了这么句不伦不类的结语,只得无语苦笑。这小子又没亲眼看见,不过是事后从刘杨那里听来的,却每每营里进了新兵都要被他召集了起来大肆宣讲一遍,就好似他白术才是当时紧紧守在黎校尉身后的亲卫队长权羽清似的。
蒋卓恩抬眼看了看天色,也懒得进去医帐了,将装满了新采草药的箩筐取下,放在了医帐门口便往伙夫营跑去。
正在分饭的老张头转眼看到远远跑过来的蒋卓恩,便招呼了身边手下接了勺,往围裙上蹭了蹭手,冲愈跑愈近的蒋卓恩摆了摆手算是打招呼。
蒋卓恩见老张头招完手,就转身往搭建起来的炊事堋走去,也不在放饭点停留直接跟了进去。
老张头提了装了白子泉饭食的食盒递给蒋卓恩,又笑着招手让蒋卓恩近前来,蒋卓恩心知这是老张头又要给自己加好料了,便咧嘴露了个甜甜的笑凑上前去,老张头掀开大灶旁还未熄火的小火炉上的罐子盖,一阵混合着酒香的野山鸡肉香便隐隐飘入了蒋卓恩的鼻间,老张头见蒋卓恩猛吸口水,满意的复又盖上了盖子,冲蒋卓恩挤着眼睛低声道:“这是今早二虎打来的野山鸡,给白大夫送完饭,你去喊了白术二虎他们过来吃,我给你们用小火慢慢炖着,入夜了再来。”
蒋卓恩用力点了点头,又冲老张头感激的笑了笑,便提了食盒往白子泉的寝帐跑去。
白子泉当年带了临时编入他手下听命的二十个兵士,跟着黎晰鸿往西平方向赶,本来是打算照着交代白术的阴招如法炮制,看能不能摸进大尹****那九万大军里去阴人家一把--这人身为医者的医德全不用在坏人身上还真是识时务,结果还没等的及摸进人家后方,就直接在打了起来,白子泉无法只得由那二十兵士护送到了伐北军后方,战事了了后也留在西平医治受伤军士,直待了三四个月才回了金城。
在蒋卓恩心里,现在的生活可真是平静安稳,即使她心知这战还没打完,但是能偷得几年闲散光阴,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金城之役,蒋卓恩私下嘱咐了白术,将功劳都归了白术一人,姑且不论后来的军士,壁虎军却是无人不知白术名号的,待得黎晰鸿入了金城,处理军务时要提拔白术进亲卫队跟着林虎做事,却被白术婉拒了,只道不敢居功,要继续跟着白子泉学本事。黎晰鸿也不勉强他,自放了他回白子泉身边。
蒋卓恩当时也是有幸面见了声名鹊起的浴血杀将黎晰鸿的,她站在白术身边,黎晰鸿处理完白术的事,看到白术身边的年幼孩童,心知这是当初他亲自从马坡城死人堆里捞出来的那个重伤孩童,却什么也没多问多说,只怜惜似的摸了摸蒋卓恩的头顶,轻声说道:“好好跟着白术。”
说完停了许久也没再说话,却也没移开他放在她头顶上的手。
蒋卓恩仰起头看他,黎晰鸿的手就顺着她仰头的动作,轻轻往她脸上滑下,盖住了蒋卓恩的眼。
那只布满了硬茧和细碎伤痕的大手弄得她双眼不住的眨。
她听到他在头顶上如叹息般说道:“你安心,我已经替马坡城民报了仇。”
随即她就感到了白术牵她的手加重了力道。她似乎能透过那只大手,看到少年脸上似曾相识的肃穆沉静的表情。
蒋卓恩缓缓半敛了眼皮,低低应了声:“是,黎校尉。”
那之后蒋卓恩便仍跟着白术在白子泉身边打下手,因着她识字,白子泉归了凉州大营后,就开始教她二人医术,且严苛无比,隔几日便要考校一番。
蒋卓恩觉得白子泉是因为战事暂了闲出屁了,又不想回京城,就用这个法子来折腾她和白术。
这三年来,蒋卓恩不仅每日早间要拉着白术蹭在新兵后头跟着操练,求个强身健体,将来有个万一要逃命的时候不至于成软脚虾,又要利用午休和晚间的时间,研读白子泉的医书,每日真是累死累活。白子泉那里蒙混不过关就装痴卖傻耍孩童脾气,白子泉大概心里多少也觉得金城之役对蒋卓恩的安置不厚道,且他又从白术那里得知了详细经过,对蒋卓恩是又愧疚又疼惜,因此对她也多有放水。
这二缺。
蒋卓恩想到旧事,只觉得白子泉这人实在是个怪人。
待看到白子泉的寝帐近在眼前,才三步并作两步撂帘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