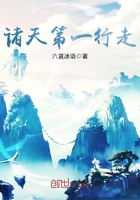第三章
应是末时,寂肃在浮屠塔处行走,闲暇时,常在这里看着些许先辈高僧,似乎能从中悟出不少的禅学宗理。
这时两位五十多岁衣冠华丽的男人在一尊佛塔面前叩首,微有祭拜之意。
自然是清楚这尊佛塔,寂肃向前去,单手行礼;“阿弥陀佛,两位施主可是姓郑”?
那二人听其言语,其中一人回礼道;“正是,敢问大师可是寂肃大师”。
愕然,不想竟之其法号,寂肃又名白,便直接言语道;“正是小僧,二位施主此行可是要见其湛经师叔”?
那二人也是明白;“请大师前去打扰说,郑世贤,郑青贤拜见”。
寂肃听到是贤字辈的人物有些心虚,道;“小僧这就前去,只是二位施主与其师同辈莫再称小僧大师了”。
“得罪师傅了”那二人倒是很客气。
说罢,就带去其师叔的房间。
湛经大师平日里就在房内打坐参禅,不过问世事,寺内大小事宜一般都是寂空,寂末打理。
寂肃带领郑家二人到了湛经大师的房间,刚到门口门就自己开了,寂肃自然退下,郑世贤,郑青贤进入,门又自己关好。
既知我法号是寂字辈的僧侣,却又要称为为大师,郑家的人客气过了,寂肃一边思考一边又回到浮屠塔,看到去尘老僧在扫地。
平日里每隔几天此僧便会到此扫地,偶尔寂肃也会前去帮忙,只是那老僧似乎又聋又哑又盲,听不清言语,说不出话来,看不见其人。
瘦骨嶙峋,脊背弯曲,若有痴呆,穿着极旧发灰的百衲衣,颤颤巍巍的拿着破木扫把,不小心身子碰到一尊小佛塔,似有察觉,缓慢的转过身子,眼睛动一下,想睁又没有睁开的样子,一手还拿着扫把,一手行了个礼,嘴巴轻张,似乎想说话又没说出来,微微的点了两下头以表歉意,又缓慢的转过身子继续扫地。
有山的地方就会有水,山水配合默契的地方就会有瀑布,这树林中的小山就有一条小瀑布。
自上而下水转折路过地面的地方有人建了座茅草屋,正在水上。水在屋子底下穿过,别有一番意境。
茅屋外墙的大门上挂着的对联更有意思;屋下流水屋上有水,下联;山外世人山内居人,横批;屋山人水。看着倒也简单。
傍晚茅屋的主人回来了,这里看门的阿三急忙迎了过来。
“阿三,二弟回来了没有”那人边走边问。
阿三走在身后到;“回来有半个时辰了还带了不少菜肴,现在二爷在缓水处钓鱼”。
已经走到屋门口的朱瑾听到停了一下,又向缓水处走去,还是边走边说;“阿三你在家准备饭菜,把藏得酒拿出来两坛”。
“是”啊三也不能跟着,不便打扰,二爷是喜欢钓鱼,大爷是喜欢二爷钓鱼,这对兄弟似乎也类似。
朱瑾走到看了一下道;“二弟,都半个时辰了,还是第一次见竹篓里什么都没有”。
朱亮坐在那里手握鱼竿,目光不转,微微一笑道;“兄长再看一眼吧!这次我是将它放在水中,现在竹篓里有半篓水”。
朱瑾不明觉得可笑,又问道;“那鱼呐”?
“都是小鱼,它们吃完后上钩,又跑掉,我提上来换上新饵继续钓,是时候该提上来一条大鱼了”。
朱亮这样言语朱瑾知道有深意,却也不懂。
这两兄弟都是非常忠诚之人,坛主都是非常赏识的,朱亮却多一样,便是聪明,聪明的可怕,却又放心。
“好了,二弟有些日子没有一起喝酒了,今日且先回去吧”!朱瑾此话似有催促之意。
“哦”朱亮一惊又一喜,微笑起来抬头看一眼朱瑾说;“我猜测应是明日,不想兄长竟然着急了”?
朱瑾无奈道;“你的哑谜我不懂”便要弯腰,拿起水中的鱼篓欲走。
“且慢”,朱亮猛地站起身来用力回拉“大鱼果然到了”用力将鱼竿向岸边甩,却不偏不移的落到朱瑾手中的竹篓里。
“哈哈,兄长大鱼到你手里了”说罢收起钓竿笑着向回走,似乎是有方才朱瑾的着急。
朱瑾无语,拿着竹篓带着鱼与其弟,一起回屋了。
天渐渐的黑了,白杨树林里依稀看得到有萤火虫飘来飘去,有一颗大树下有位女子,带着粉色面纱,手中比平时多了一把竹制短箫,头上装饰多了一根鸾凤紫金簪,是在观望,也是在等待。
女子站的地方飘飘然的有了一些酒气,前面一丈处的树下多出个男子来,手中拿着紫酒葫芦的酒壶,仰面而上的狂饮了一气。
那女子终于等待不了了,健步如飞的奔向前去,一头扑进这个男人的怀抱紧紧的不松开,这时谷良落泪了,用手抚摸着苏显的头发,心中好多话却说不出,只是缓缓的一句;“显儿,我好想你”。
苏显自然是哭了哭的有些高兴也有些委屈。手臂松了一些抬头看着谷良眼神中有怨气,有娇气,有委屈,有深意,有思念,有期待,还有些许的激动,这样的眼神十年未见胜过千言万语,谷良一手前去搂着苏显的纤腰,一手从发迹转到耳边,轻摘下面纱,吻了过去。
夜初降,十年故人今朝见;白杨下,戏水鸳鸯连理枝。林静风动满天月,结伴萤飞向彩云。
再说另一对常年相伴的夫妇,黑鲤白莲。
今天入庙拜佛不去店里卖茶,也睡得早一些,白莲看出黑鲤有些烦躁,比昨夜的还厉害。
想;出了寺门就不怎么说话,下午在家一眼不发,虽说是谷良来了却也不应该呀!
奈侧过身子,手放在黑鲤的身上就问;“师兄,今天去庙里,恩公下达了什么命令,怎么也不和我说一下”。
黑鲤不动眼睛看着屋顶;“恩公并没有下达什么,我把朱亮兄弟转交的木盒给了恩公,他就叫我回去了”。
白莲很好奇又问道;“周坛主可以直接交给恩公,为何还要转手这么多次”?
黑鲤还是眼睛不动的回道;“不清楚,我也在想”。
白莲无奈,黑鲤都想不明白的,她自然也是不懂的;“那谷良的事情,恩公说什么了”?
黑鲤听到谷良二字,心情似乎是有一些不同了,侧过身体,面对妻子道;“恩公说,谷良和苏显坛主十五年前是夫妻,还有一子”。
“噗嗤”白莲听后笑了出来,半笑着说道;“苏显妹子芳龄几何?十五年前成婚怎么可能?再说了谷门的规矩在那里放着”白莲看黑鲤很正经的样子看着自己收了一下笑声疑问道;“恩公真是这么讲的”?
黑鲤无奈道;“是啊!所以我更想不明白了”。
这两天接二连三的事情确实为难黑鲤的脑袋了。
白莲有些纳闷又有些怜惜;“想不到苏姑娘命这样哭,嫁了个这样的男人,一个人拉扯孩子,对了,十五年前,那苏姑娘的孩子今年不都有十四岁了,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黑鲤一听白莲分析孩子的事情,急忙打断,伸手将其搂在怀中,在额头上轻吻一口;“我都够头痛的了,你就别多想了,睡觉吧”!白莲很听话也去抱着黑鲤,二人甜蜜的相拥而睡去。
夜彻底的落了下来朱家的两兄弟也都喝了个半醉。
朱瑾端起竹筒做的酒杯道;“二弟差不多了,再喝就要醉到明天下午去了,满饮此杯,都且睡去吧“!
朱亮倒是有些清醒之意,不过也差不多了;“也好,日后你我兄弟二人可天天饮酒,又岂在今晚”说完又喝了一杯。
朱瑾虽醉,大脑却还算可以,笑道;“你在子鼠,我在鹿马,日后天天饮酒,二弟你醉了”。
朱亮听后大笑;“哈哈哈哈,兄长,周坛主为何要将那木盒转交多次给郑坛主,你可知道”?
一般坛主的吩咐朱瑾都是照做不去过问,忠诚又老实的人到了这种地步也难怪坛主会喜欢。
“哈哈哈”朱瑾也笑了起来,似乎是笑朱亮的多心,又问道;“那你说,为何”?
“兄长啊”!朱亮早已习惯兄长的这个样子,看着朱瑾道;“你我,黑白夫妇,周坛主的意思是此物牵扯的事情关乎兄弟,夫妻”。
朱瑾即使听懂了朱亮的话也自是不明白,却也没有好奇心。
朱亮看到大哥这样;“好了兄长,不早了你我都且睡去吧”!说完站起身来,晃晃悠悠的走回房间。
朱瑾与二弟一起在家的时候,朱亮时常分析其周边,这次关系到自己,想多想一些却又想不明白“哼”自己笑自己了一下慢慢的站起身来也是半晃得回屋睡觉了。
天还未亮,谷酿从客栈出来,一个下午的路程已到了金羽寺附近,当然,这样的行程,谷酿另有自己的用意。
寺内床上的郑坛主在睡梦中被叫醒“这是,空谷回音,又有几分阴柔之气,谷酿”。
一边思索一边下床穿好衣物整理了一下。
出门来,转身回去又把门关好,闭了下眼睛感受一下方向,抬头看了一下,不紧不慢的轻轻一跃,便到了屋顶看了一下四周,又轻轻一动身体,前去找谷酿了。
金羽寺南边二里地处,有一条自东向西流的清水河,两岸栽了杨柳,在河边站了一位姑娘,头上古木簪斜插浅入乌云,粉面低垂,淡淡双唇晕微红,似春笋手卧宝剑,纤细腰婀娜,布长裙护体,脸似三月新开桃花,眉似春风新裁柳叶,素体轻盈淡妆丽,微微一面可倾城。
“谷酿妹妹,别来无恙”言语中郑坛主从杨柳树后走了出来。
谷酿并无动弹,静静的看着流动的河水;“有二十年没见面了,难得杨大哥还记得小妹”。
郑杨柳侧过身子去看河水感慨道;“你不是也还记得我,还清楚的知道我住的地方,哼,像这流水一样,二十年过去了,现在请叫我郑大哥”。
听到郑时,谷酿惊了一下;“小妹二十年不曾下山,敢问郑大哥在做何事”?
郑坛主见谷酿试探着问索性就都告诉他;“我在十二坛的子鼠坛做事,已有十年了”。
谷酿这下明白了,路上听谷源说附近有个隐秘的组织叫十二坛,看来眼前的杨大哥就是十二坛的郑坛主。
突然似乎好像想到了什么;“杨,不,郑大哥子鼠为生肖之首,十二坛都听命与子鼠坛吗”?
郑坛主对谷酿的担忧心知肚明,轻笑了一下,想既然这么问了,就让你再紧张一些好了;“十二坛是坛宗杨远管理的”。
“杨远”谷酿吃惊的叫了出来,方才自己勉为其难的沉静,一下子被这个名字彻底打破;“可是那,翠柳山庄的杨远”?
郑坛主完全理解谷酿,不紧不慢道;“六十年前,翠柳山庄的庄主杨宏让位与其弟,自己暗建十二坛,一庄一坛,一明一暗,二者相辅做事,坛宗自然也是杨家的人”。
郑坛主不紧不慢,谷酿却不然;“那杨远坛宗打算如何对付谷良”。
“坛宗闭关未出,还不知此事”郑坛主这样言语谷酿是松了一口气,却又思索了一下道;“那郑坛主打算如何对付自己的杀父仇人,昔日的兄弟”。
谷酿这样问,郑坛主自是不愿意回答的,看着河水道一句;“我很好奇,你为何一直不问自己最想问的,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谷酿有些心酸道;“没有我的打扰,他们两个会活的更好”。
“哼哼”郑坛主一笑“看来你知道他们还活着”。
谷酿心里明白道;“杨大哥的为人小妹心里清楚,郑坛主会做的事情我也明白”。
“天要亮了,且回去吧!说话太久对你我都不好”。
郑坛主这样言语谷酿心知肚明一拱手告辞状走了,原本想询问谷良,却对其行踪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