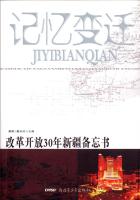“不好玩你还去那么久?”陶木晴摇了摇头,仍是心有余悸,“战场比不得别的。你竟连一个口信也不带回来,若是从此一去不回头,你叫我怎么办?”
宿兮没奈何,“我若是当真告诉你了,你不得从中原一路追到西夏来么?
“能活着回来就好。况且……我当时是盟主,身先士卒,理所当然……顾不得其他。”
“这个我当然知道。”陶木晴抬起头来,忽而笑道,“不过你把武林里头的事都推给不笑大师,这当真好吗?”
“又如何?”宿兮慢吞吞地撑起身子来,“当初是他把这个苦差事扔给我的,如今叫他也尝尝,一报还一报。”
“……”
苍山高远,烟霭茫茫,一地的枯草衰败,烛火随着气流冒出一段黑烟,滚滚而起。
总管在一旁边,瞧着那地上跪了半日的黑衣人,终是忍不住偏过头,拭了拭眼睛的泪花,然后劝道:
“将军,回府吧,您老这么跪着对身子不好啊……”
两座坟头一高一矮,孤零零的在山中静静立着。
总有一日,墓碑上的字会磨损不清,总有一日,坟边会杂草丛生,荒芜萧条。
能葬在这个能看清汴梁城全貌,能看见自己一心死守的城池的地方,想来,便是死也该瞑目了。
步云霄缓缓站起身,一言不发地举步往山下而行。
宋夏三战之中,大宋屡屡残败,死伤无数,虽已言和交好,但毕竟损失最大的还是宋军。
江陵城百姓便自发在河边放灯祈福,悼念亡灵。
那方流动的河水上满满的皆是宁静闪烁的花灯,灯光明黄,随着水流浮动,就像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人世的长河里起起伏伏,飘飘沉沉。
渡头的一个小哥手拿着河灯朝陶木晴这边招手,笑道:“夫人,放个河灯吧?”
陶木晴垂眸看过去,那花灯是用白色丝绸所制,一侧画了一只正在梳理羽毛的白鹤,白墨交织的颜色瞬间让她想起许久之前的一些事情来。
“娘啊娘,我们放一个吧?”见着她半晌不说话,宿谦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扯了扯她的衣摆。
陶木晴方回神过来,低头笑道:“你要放就放吧。”
宿谦兴冲冲的奔了过去,接过那小哥手里的灯正要往水里扔,那小哥忙制止他。
“诶——小公子,你还没写东西呢。”
“写东西?”宿谦不解,“写什么?”
那小哥取来纸笔凑到他跟前笑道:“既是祈福和悼念的,自然要写一些东西,否则,天上的神仙如何知道?”
“啊……”宿谦为了难,转头去看宿楚,“我们写什么好呢?”
“随便写吧。”后者不以为意。
“这东西哪能随便写呢!”他歪着头,咬着笔杆想了许久,这才在那纸上写好,交给那小哥。
“好了,小公子。”那小哥帖好了纸条,将花灯交给在他手里,“您拿去放吧。”
宿谦兴高采烈地捧着花灯,一手拉着陶木晴:“娘,我们一起放吧。”
实在是拗不过他,回头见宿兮正对她笑着点头,陶木晴这才颇为没奈何地跟着宿谦往河边走,白色的河灯散发出温暖的气息,她就着宿谦的手,蹲下身子,两个人慢慢地把河灯放进水中,轻轻又拍了拍水,将它赶到河中心去。
河灯随水越飘越远,越飘越远,终究混在那一堆河灯里,分别不出来了。
“娘,那边有汤圆。我们吃汤圆去吧,好不好?”
“好。”她能说不好吗?
到底孩子还小,放河灯也不过是顾着有趣,等到他们都长到能懂的年岁。这世间又不知是怎样的境况。
宿谦拉着陶木晴的手,迫不及待地往路边的摊子上跑过去,后面的宿楚吐了吐舌头,自推着宿兮跟上去。
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仍旧是那般繁华景象。
姑苏城外,夜半钟声。
河岸边柳树下,寂寂安静。
风起波澜,柳枝摇动,黑色的衣袂飞卷而起,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手边摁着一个大酒坛,浓郁的酒香在四周弥漫开来,醉人心扉。
柳絮在他俊逸脸上划过,从前的飞扬神色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心安的沉稳和坚毅。又一口酒灌入喉中,依稀,记得在这个河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清晰如昨日。
恍惚间,他想起初见时,有人曾对他说过的那一句话。
——“人有时候小心过度了,可是会错过许多东西的。”
视线里,石桥之下突然悠悠荡荡出现一个光点。
步云霄微微凝神看过去,水面上波光粼粼一个小圈,好像是一盏河灯,随水悠悠荡了过来,片刻之后,被河水打在岸边,眼看就将熄灭。他缓步走了过去,随意俯身将那盏花灯拿在手中看。
灯身已被河水浸湿,隐约却见得那灯中贴着一张什么字条,他定睛而看,纸上只写了几个字,字迹稚嫩,是孩童的杰作。
“愿随春风步云霄”
他唇边浮起一丝笑意,再度将那河灯放回水中,搓身仰头饮酒。
一轮明月高悬,清冷,皎洁,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