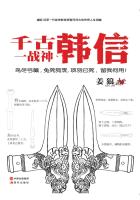第二年,肖依九岁时,她大概能读一些小诗了,也基本能认字。墨子期于是常常带她上街遛弯,让她指出每个商户的名字和招牌上的字,这件事一直让她乐此不疲,加上常识的积累,她开始给各种可以取名字的地方取名字。于是她家里的亭子都多了些新名字,有些时候,她对学习没太大的兴趣,但她却有时会很喜欢诗歌,墨子期有时会在夜晚讲一些故事,无论是狐鬼,还是典故,墨子期都很喜欢讲,而肖依很喜欢听,于是有时的晚上,两人就不会回房太早,而是聚在一起讲一会,听一会。
有一天的故事,是讲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肖依听了满脸疑惑,说:“周幽王为什么要戏耍他们?”“因为他荒淫,为了美人儿忘乎所以。”墨子期按照以前老师教的说。“那他为什么荒淫,什么是荒淫,这比天下百姓更重要吗?”肖依又问。墨子期有点问懵了,便一时不知怎么解释,怎么和一个九岁的小孩解释“荒淫”呢?他只好清清嗓子,转了个说法:“因为他爱褒姒,迷恋过了头,便是胡涂。”肖依又似懂非懂的看着墨子期,说:“爱是什么?会让人昏了头?”
墨子期说:“就像是令慈令尊对你,我对你,都有爱呀。”“那不是周幽王对褒姒的感情吧?”墨子期又失了话,不知说什么,自己活了二十年,没有喜欢过的人,也没有结过婚,当然说不上什么别的了。于是就只好讲了些《诗》里的有关爱情的诗。最后说:“男女之情爱不同于其他的感情,它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人都可以有的感情,人人都向往的感情。”
肖依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墨子期至今难忘,那就是:“那我什么时候会有一份呢?”这是一个小女孩,她也许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爱情,却已经被自己老师的话勾的向往起来,这件事,听上去也很暖人,至少墨子期是这样想的:“你会拥有一份的。但现在于你,还是早了些。”
肖依摇摇头,一把抓住一旁睡得正舒服的汤汤,说:“您看它怎么样?”汤汤是只公狗呀,不会肖依是???????“老师,您说汤汤怎么不找夫人呢?”墨子期的脸抽搐一下:自己脑子刚刚在想什么呢?“汤汤还是只幼犬,也,也,也不会找夫人。”墨子期尴尬地说。
有时候,肖依偷懒,就会赖在案上,一趴,说:“老师,我累了,让我休息一天吧,不要读书了。”墨子期似笑非笑的一摇头,拿著书准备递给她,肖依看没效果,一把抱住墨子期的手臂,说:“老师,我真的不想写。”同时还投出了一股深切的目光,墨子期一笑,说:“少来这套。”肖依有从案上站了起来,这时候,她矮小的身形正好和墨子期一边高,两人离的很近,几乎要贴上了。肖依说:“老师,不要呀,”说完还晃晃墨子期的手臂,墨子期一歪头,拿笔末端一敲肖依的额头,说:“还是少来这套。下来。”肖依在桌上一跺脚,撒娇道:“别呀别呀。”墨子期宠溺的笑了笑,一把将她抱了下来,然后说:“现在开始上课,跟我接:‘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肖依一脸郁闷的开始背。墨子期看看她,默默的说:“要不以后不背这么绕口的了,背背《千字文》或是《急救篇》怎么样?”肖依眼睛一亮,一抬头,说:“怎么样呀,好背吗?”“听听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但又有时,墨子期则会宽容一些。“老师,您想不想知道城门口的小孩子们在玩什么游戏?”肖依倾身枕在一迭硬黄纸上,刚刚睡醒,揉揉眼睛说。墨子期看着她静静的坐了很久了,这个家伙不仅作业写的寥寥草草,而且还打瞌睡睡觉,竟然还敢大言不惭的枕在自己的作业上,安然入睡。墨子期抬眼一瞧,墨迹未干的地方将墨渍粘在了肖依睡觉的半边脸上。他嘴角拂过一丝无奈的笑意。“先生默许了,那老师再见了。”说完就跑了。墨子期一愣,自己怎么答应的她?后来一想,气的一拍大腿,说:“默认什么的,谁说是的?”刚想帮她把墨渍擦了,现在可好,叫她出去自己玩吧。哏,回来了,莫怪我罚她背书了。墨子期想。
可等肖依回来,听她说了好半天的趣闻,墨子期却也没了脾气,看看她转了一大圈竟然还没发现脸上的墨渍,轻叹一声,坐在椅子上示意她过来。肖依却一惊,看这墨子期的“诡异”笑容,一皱眉,后退一步,说:“老师,您可别要罚我。”墨子期继续保持笑容,招呼她过来。同时往下坐一坐,想的不那么吓人的样子。小女孩一看抵不过,就小碎步走了过去,到了离墨子期三尺之外的距离站住了。墨子期一把将她拉了过来,这时,正好和他坐着一样高。他打量了一下,肖依今年有四尺高了。他伸出手,向肖依的脸过去了,肖依吓坏了,以为墨子期要打她,又反身要跑,墨子期拽着了她,一把将她拉回自己跟前,然后一边伸手,看着肖依紧紧一闭眼,一咬牙,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墨子期笑了,说:“我又不打你。”说完用手轻轻附上肖依的脸,用手将墨渍蹭下来,因为墨渍干了,他蹭着越来越用力,就心中念叨:啊~~~~~~老师这次又要以柔克刚了,哎呀呀??????
墨子期最后放弃了,说:“算了,你还是,自己去洗吧,为师尽力了。”然后松手,看看她被自己蹭红的脸,和她落荒而逃嘴里喊“老师饶命”的样子,心里说:“真是的,我又不吃了你。“
偶尔也有一些有趣的事,肖依拿着一卷《孔子背问书》说:“老师,今天开始是要学这个吗?”墨子期拿著书翻翻,“嗯”了一声。肖依皱皱眉,说:“老师这看着很难的样子呀,我们为什么每天都只学一些课本上的东西呀,为什么不学学别的?比如什么琴韵呀什么的。”墨子期转念一想,的确她倒没学什么别的了,作为贵府之女倒也没学什么别的雅韵。于是,墨子期就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教出来了。
“老师,这是什么?怎么吹呀?”肖依看着墨子期手里拿着的小陶器,问道。“这是埙,我小的时候,我娘教我的,你不是说每次都看一些书面的吗,这次教教立体的。”
这话不假,我的父亲是教书匠,母亲是隋朝宫廷御用乐师的女儿,阿娘继承了外祖父的音乐细胞,对音乐掌握的很好,但是自己却没有学琵琶什么的弹拨类乐器,唯独爱着埙。后来有了我,我就会经常在学业之余听阿娘吹,久了,阿娘也就教我吹,阿娘死后的前几年里,我却不敢吹了,因为我还是会想起娘,想起来就会很伤心。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听肖依想要练音韵,我却翻箱倒柜的找到了阿娘当时叫我用的小埙,带给了肖依,教她吹。也是在这种教学中,我能过用它来代替我对娘的伤感怀念的死循环。
“看好了,”我拿起我的六孔埙,吹出了一个音。肖依学的认真,只用了两天她就能自如的吹所有的音了。墨子期很喜欢,也很满意这个学生。肖依学会了以后,便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到处推销这件事。
墨子期总是乐此不疲的看着她东奔西跑的展示,等她的朋友和家人都知道了肖依会吹时,她才终于能安静下来好好的学下去。墨子期觉得这件是很好的,安安静静的尽心教。
直到一天,肖依回来时,憋红了脸,急匆匆的抓住墨子期的手臂,晃着说:“老师老师,快教我一首难的曲子。”墨子期正在看她的作业,没理这茬,指了一个错字给她,说:“这个字写错了,应该是????????”“老师!”肖依皱眉起来,晃着老师的胳膊说,“作业我回来改,老师,求求您叫我首曲子吧!”“怎么了?”墨子期放下作业,看着她问道,“为什么要急着学,你现在还没法学这些难的曲子呢。”肖依一噘嘴,说:“我今天遇到一个人,他在吹笛子。他会吹好多东西,听见我吹,说我吹得不好,而且那么简单的乐器,根本没有技术水准。”墨子期气的站了起来,一挥手,说道:“他人那里呢?我倒是要问问他,为什么笛子比埙有技术水准。”
墨子期拿了自己的埙,奔着肖依的地方就去了,肖依在后面追着。“老师老师,您别急呀,我还没说完呢,他还说埙?????????”
等我到了那里,我却只见到一个小男孩,坐在一个胡凳上晒太阳,身旁放着一根笛子,旁边立着两个仆从。我这尴尬了,原来是个小孩,我可怎么理论。我拿着埙一屁股坐在小男孩身边,说:
“你就是侮辱埙的那个小孩子。”那个小男孩一下子跳了下去。作揖一拜,说:“岑家幺子岑康见过墨先生。小生自然不敢侮辱埙,不知您从何讲起。”墨子期看看刚追过来气喘吁吁的肖依。肖依一插腰,说:“哏,叫你说我吹得不好,我把我老师召唤出来。”岑康嗤之以鼻,“真是不讲究,自己吹得不好,叫师傅来撑腰。”
肖依红了脸,说:“你你你,你真是的,现在好了,让你听听什么是埙的艺术。”岑康一挑眉,毕恭毕敬的转过来,朝着墨子期一鞠躬,侧耳道:“小生洗耳恭听。”墨子期拿起埙,吹了起来。
那是我娘叫我的最后一首曲子,也是我所听过学过的埙曲中最难的,它的指法很多,连音也多,初学时不会换气,总憋得脸发青。好在它真的很好听,娘说你那是她的看家本领了。
吹了一半,墨子期想起什么。说:“你是不是岑俶的弟弟?”岑康点点头。
墨子期缓缓地说:“我识得你,你和肖家订了亲。”岑康说:“先生这些都知道,真是神人了。”“我并不聪明,因为我知道这件事罢了。”墨子期说。肖依好奇的凑了过来,说:“什么人要嫁他?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姐姐吗?”墨子期摸摸肖依的头,不说话了。只是笑着,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她哥哥毁了婚约,她要继承她哥哥的婚约,嫁给她的弟弟,现在两个未来的小夫妻在这里遇上了。
这是后来就没人提了。岑康体弱,自小爱生病,所以经常在病余出来晒太阳。过一会就又回去了。因为他没有评价我的埙,所以肖依就求我教,她每学会一点,都会跑回去演示给岑康看。岑康这时就用一首笛子的曲子回应她,两人一吹一喝,蛮有意思的,我倒也很高兴。岑康只知有婚约,不知要娶的就是眼前的这位肖小姐,而肖依更是什么都不知。我从未拆穿,因为这样二人之间所诞生的纯洁友谊才是自愿的,这是充斥着童真的,好呀好呀,妙哉妙哉,我倒是很鼓励这件事,我若让他们以音会友,成为朋友,那我也算是个好人了。善哉善哉。
但是我也发现,岑康完全在往带坏肖依的路上走。一天中午,我正安安静静的坐在案边看书,看得累了些,打算睡一下,刚趴下,突然我感到嘴角一抽,痛的我身心交瘁。
“哎呀!”墨子期的嘴角痛的抽动起来。他一摸,左嘴角上刚刚滋生出来的几根胡须被活生生的拽了下来。墨子期双手紧握痛的用手迅速的捶了一下头,然后将哀怨的眼神投向四周。“谁干的~~~~~~~~~”
肖依一下子跳了出来,说:“老师老师,我帮您修理一下,您看,别人都没有在嘴角边长头发啊,帮您拔一下,是不是很贴心的样子呢?”“你没看到令尊,令兄都长了吗?”墨子期继续哀怨的说。“嗯????????我知道胡子是什么样,是一缕一缕的,您的就几根,是头发。”肖伊说。
墨子期痛苦的揉揉那里,然后随手一指门外,说:“谁告诉你的?简直胡说。”肖依一挑眉,“岑康呀。”岑康!会杀此市井儿!!!!
秋初下雨了,汤汤一去不知何时归来,肖依急得很,急着找,可是外面下起了雨,墨子期也帮忙找了找,可也是没有,等他回来,肖依却不见了,全府也没有,这让墨子期心里着急得很,就打了把伞出去找,街上巷陌都没有,墨子期越来越着急越,眼看着雨越来越大,心中十分担忧。红色的伞在雨中显得格外的刺眼。突然,他在街中央看到了一个人影,是肖依的,怀里还紧紧抱着汤汤,坐在地上。墨子期快步走了过去,将伞打住了。“老师???????汤汤受惊了,跑出来淋了雨,好可怜呀???????”肖依幽幽的说墨子期将伞完全遮住了肖依,说:“好了,跟我回去吧。”肖依抱抱汤汤,墨子期的伞小,自己的前襟都湿了,才遮住肖依,为了让肖依不淋雨,墨子期不得不将她背起,汤汤就这样被抛下来,在后面追,肖依趴在墨子期的背后也一点也不老实,一直是在说笑?????这孩子,刚刚还为了自己的爱犬不管不顾吗,现在却又忘之脑后了。后来回到了肖府,才发现自己走的时候没有换木屐,履已经湿透了。
至于那把伞,我记得自己好像后来送给黄廉清还是谁了,因为那天下了雨,所以就借给了他,之后又忘了找他还,最后干脆给了他。
由于肖依每天看完书就去找人玩,我就去找别人玩。之前救过我的秦武修,我和他聊的也满投机的,秦武安作为我的学生,对我倒是恭敬一些,少了些朋友的感觉。有一日,他们聊到秦武修定亲,说要娶胡休的长女胡静淑,倒是要请我来观喜礼。“不过说到这里,子期兄,你怎么没娶亲呢?“
“我?大人早逝,没有定。此时便不了了之。”墨子期说。“那,您为什么不在自己找一个呢?您今年二十了吧。”秦武修好奇的追问。墨子期一抖手,奶酪差点掉了,随口漫不经心地说:“没打算没打算。”秦武修的好奇心上来了,凑了过来,说:“要不我帮你寻寻,静淑应该还有些好姐妹未嫁呢,说不定有戏????”“算了吧,我独身独惯了,况且现在还要教肖依读书,也不方便不是。”他接着就不再听秦武修的话了,只是喝茶,亦或是必要出“嗯”一下,“啊”一下的。
但谁知道,这里面有一声“嗯”,竟然代表着答应让秦武修找姑娘。一周后的一日,他来找秦武安下棋,碰上了秦武修,秦武修正找他呢,抓着他,说:“我找到一个符合你胃口的好姑娘了,你不来听听,比你小七岁,虽然小了点,但是出身不低,可是个好姑娘。”墨子期无奈的望了他一眼。
“她家里祖上三辈,有读书的,有做官的,有跟着圣人抗前朝的,身份一点也不低,而且别怕你配不上人家,他家里现在并不是可别有钱,就是很普通一家,人很好的,门当户对。”秦武修跟着说。
“我祖上有教书的,还有当官的呢,尤其是三代往上。还有给汉武帝当文官的呢,我家还是汉朝的贵族呢,”墨子期说,“这些以前的事就不要提出来说了,说说别的吧,况且,我也并不打算婚配。”
秦武修一皱眉,说:“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你不打算看看?”“以后再说,最少,也要等她及笄了。”墨子期这一句,足以让这件事再耽误下两年了.
又忽然有一天,肖依回来的很早,她一回来就扎到了墨子期跟前哭。“老师,不好了,岑康生病了,他家人不让我看他了,听说他还昏着,怎么办呀,万一他有什么不测怎么办呀?”墨子期也不知怎么安慰,只好说:“他身子本就不好,这件事也许他能熬过来呢,不要担心。”可是肖依总是在哭,与墨子期,那声音就如刀绞一般,他心中不安,看着她却也不知说些什么。
我只好拍拍她的背,安抚她一下,她却哭的更厉害了,我不知说些什么。只是垂下眼,看着她,虽然她看不见我的目光,但也似乎有安慰功能吧?我轻轻的拍拍她的背,说:“你还是不要担心了,以后岑康又不是不出来了,还是个小孩子,老天不会不那样对于他的,放心吧。”肖依一听,转移了哭的位置,直接抓住我的衣襟哭虽说我们两个跪坐在案旁边,她这样的动作她舒服得很,但本人实在是承受不了,她其实还是很重的,我用手从后面支撑我,然后用另一只手拍拍她的背。这个动作吧,虽然她是小孩子,但也让我尴尬不已。我是一个很重礼节的人呀,男女授受不亲呀!!这样,简直是非礼也。但我有什么繁杂的礼节的道理来推开小姑娘,还她哭得更厉害呢?没有,所以我不去想,只是安安静静的安抚她的情绪。什么礼节,在她面前,现在见鬼去吧。我伸手轻轻的抱住她,轻轻地用我的话安慰她。就这样,慢慢的让她平静下来了。
这个小姑娘很有趣——这是他这两年对她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