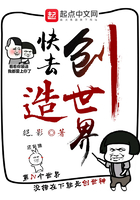次日五更天刚过,天未亮起,只听得楼下一个雄厚声音的大声骂喊:“楼上哪个讨死的畜生,杀了客栈掌柜和老板娘,都给爷滚下来!”
“哼!该死的贼人,想必你们和他俩是一伙的,那就一起受死吧!”墨惟踢门而出,提剑翻下楼来。
对面是个紫黑阔脸一身粗肉的大汉,左右站着五个持刀的同伙。大汉打量了墨惟一眼:“就是你砸了爷的生意?来啊,一起把这厮剁了!”
原来这伙人与黑店掌柜合作多年,如果前日有好看的姑娘住店,掌柜就会把消息送去,让他们第二天天亮之前来接人,带去卖给青楼为妓或者卖给大户人家为奴,回来两家分钱。
一楼堂内本是有四张方桌供人吃饭,方桌边上摆着一圈凳子。六人踹开挡道的凳子,围住墨惟,一齐举刀杀来,墨惟想擒贼先擒王,一个箭步直取带头的大汉。那大汉拿刀一挡,再一振,一股极大的力道推向墨惟。墨惟脚底一溜退了几步,另外无人的刀锋也劈头盖脸地过来。墨惟见大汉不好对付,打定主意先杀了五个喽啰。只见他冲天而起,凌空倒翻一个跟斗,落在六人合围之外,时而左劈右刺,时而绕桌而走,始终与大汉隔出一段距离,却将其他五人一个个杀了。
楚瑶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握剑出现在身旁,一声喊,杏目圆瞪扑向大汉。大汉没了喽啰,被两人缠住,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拼死相搏。一刀敌三剑,架格遮拦甚是吃力,斗了十几回合便落入下风。大汉发一声吼,朝楚瑶虚砍一刀,楚瑶急忙闪过,让出一个空挡。大汉格住墨惟的剑,转身就走,两人哪里肯舍,执剑快步追来。那大汉常年在山林中行走,脚力了得,两人追不上,只好随他去了。
回到客栈,其他半夜未走的客官也收拾完行李慌忙走了。
“我们也走吧。”墨惟说。
“墨公子要去哪里?”楚瑶问。
“我去羽山之南,找刘君安叔父。”
“就是那个制蛊的山南刘家吗?”
“正是。”
“那我也同去吧,师父去京都参加三月三大会,应该也要过些时日才回山,不如和你山南刘家走走,刘家的符咒天下闻名,正好去长长见识。”
墨惟也不好推脱,答应下来。两人四下搜了下,翻出些银两带在身上,一同出门。行了半天,到一集市,找个贩马的选了两匹,往羽山南赶去。
毕竟太平时候买蛊的人不多,武家除制蛊之外还有种植草药的营生,山南刘家一样,平时也以画符治病或招鬼问事为生计。与武家将家安在羽山山麓不同,刘家常有寻常百姓来往,便住在山南的官道边,不至于有蝮虫出没的地方。
又过两日,来到一个篱笆围起的院子,凌乱地栽着几株桃树,粉色的花开得正盛,简陋的柴门虚掩,一个四十来岁,身穿皂布袍,容貌轩昂的人正坐在屋前的石桌边画着符文。刘君安未曾娶妻,膝下无子嗣,当没有百姓来访时,院子显得分外清静。
墨惟与楚瑶下了马,有一个书童迎上来将马牵去栓了。
“侄儿墨惟见过刘叔父。”墨惟作揖,楚瑶也跟着施礼。
刘君安听见了,放下手中的桃木笔,站起来笑道:“侄儿可是稀客啊,近两年都未曾见过了。这位是?”刘君安手指了指楚瑶。
“小女南冥楚瑶,路上遇上件麻烦事,幸好有墨公子出手相助,然后同路过来了。”
刘君安打量了下。“哦,难怪不曾见过,还以为是名剑阁新来的小师妹,呵呵。”
“今年我随家父上京参加三月三大会,会前一日家父说义王请你和武淳叔父去京都,便派我来了。”
“请我和武淳?”刘君安抬头想了想。“那必然是和巫蛊有关了,莫非是虞天策觉得他父王是被毒死的?”刘君安虽然偏居一隅,但对天下的事还是有些了解的,知道老义王去世新义王继位。
墨惟听了说:“一路来的时候,我也这么想的,但家父也未曾透露什么消息,详细如何就不知道了。”
刘君安刁然一身也没有什么可交代,回屋找了几件换洗衣裳,取了几张符纸,将刚才用过的桃木笔一并打了包袱,带上防身的剑,交代了书童几句,出门来。“我们是否要去与武淳会合?”
“是的,来时,我跟武叔父说一齐上京。”
“从水路到武家只需一日,那我们坐船走吧。”刘君安说着,领着墨惟、楚瑶一起往屋后走。
屋后有一扇小门,出去便是河水,一只小船系在长篙上,长篙笔直插入浅滩。刘君安的武艺高出墨惟许多,自然是没把蝮虫当回事,墨惟、楚瑶壮着胆一起下了船。刘君安取出符纸,画了一个驱邪的符文,贴在船头,拔起长篙撑船而去。
一路无事,偶尔有几条蝮虫遇上,也是绕着船游走了。墨惟、楚瑶对刘君安的符暗暗称奇。
“刘叔父,若有空暇时候,教我画符吧,来的路上遇上一条大蝮虫,斗得好苦。”墨惟说。
“呵呵,你当我只是在纸上画个图么,若要灵验,需要将功力注入符中。侄儿若什么时候可以轻松除掉蝮虫了,我再教你。”
“若是能轻松斩杀蝮虫,我也不需再学了,直接用剑便可,何须再多带这些笔墨符纸。”
刘君安笑着摇摇头。
墨惟转过头来看着楚瑶:“这几日,你师父应该也在回山的路上了,你还与我们一起去京都吗?”
楚瑶想了想,说:“回去估计也是再去令丘山中谷之外看着人家出入,甚是无聊,还不如去京都吧,将来师父问起,随便编个故事瞒过好了。”
“令丘山中谷?莫非前几日,你跟踪的是长生门的人?”
“师父担心长生门欲对南冥不利,便让我和几个师兄弟去盯着。”
“左掌门这么做,是觉着南冥派已不如长生门了?”
“那不至于吧,南冥毕竟是数百年的基业了,长生门还不足三十年。”
说话间,船已靠在羽山脚下,三人跳下船往走不多时,就到武家的竹楼下。竹楼周围游荡着数十只黑犬,见有陌生人来,呲着牙聚拢过来,将三人围住,墨惟见识过黑犬的厉害不免紧张,楚瑶更是紧握剑柄,随时要拔出剑来。
武淳听到外面有异响,与武阳一起下楼。“哈哈,贤侄今日才来,我等你们多时了。”那日遇上墨惟要借他船时,看出墨惟怕这蝮虫不肯走水路,故此取笑他一番。武淳朝黑犬使了个眼色,黑犬四下散了。
墨惟尴尬地笑笑。
“呵呵,武兄家的犬是越发通人性了啊。”刘君安说。
“让刘兄见笑了,如果我有你那画符的本事,就不用这么费劲养犬了。”
武阳回楼里取来行李,武淳拿了。“阳儿在家好好看着刚种下的药草,应该不出一月我就回来。”
武阳应了,撑船送四人过河便回。四人找一处马市又买了马,直赴京都。
三月廿五,一行人来到京都,先去了转星楼,墨攻还在那里,众人见了面,开了房,一起前往义王府。
路上,墨惟对楚瑶说道:“刚才我与家父说了你是南冥弟子,他随口说了左掌门还在京都,或许一会就在王府遇到。”
“哦,那我岂不是不该跟你们去了,让师父知道我偷跑到京都来,会罚我思过。”
“你不是要编个故事瞒他么?”
“还未曾想好呢。”
“不如这样,就说我在路上遇到贼人,得姑娘出手相助。姑娘放心我不下,怕路上再有麻烦,便执意要送我来京。”
“不成,我的功夫师父岂会不知,哪轮得到我出手助别人。”
“或者说你跟踪那长生门的人来京,遇上我们,知道掌门在王府,便一起来了。”
“若师父问那二人去向呢?”
“未曾想到京都人多,走过几个热闹的街坊便不见了。”
“。。。。。。”楚瑶低头想了想。“那先这么说了,若有破绽你可要为我圆场。”
“那是自然的。”
“刘、武两位叔父不会说什么吧?”楚瑶低声问。
“姑娘放宽心,不论是说了什么,包在我身上,保你不会被师父责罚。”
墨惟、楚瑶跟着三位长辈到了王府,墨攻说明来意,有奴婢引着众人直到浣月轩。虞婉兮站在门口,与之前一样将墨惟、楚瑶拦下,领到后花园喝茶赏玩去了。
墨攻、武淳、刘君安进入屋内,虞天策、虞朝宗已等候着。
“久闻羽山刘、武两家盛名,今日得见,幸会幸会。”虞天策说。
“山民刘君安,见过义王。”
“山民武淳,见过义王。”
众人施过礼,各自坐了。
等女婢进来上了茶,退出。虞天策说:“这次请二位来,是为了家父去世的事。家父一直硬朗,无病无痛,突然日益虚弱,御医束手无策,不知症结在哪。去世之日便全身泛黑,其中必有蹊跷。”
“殿下是说有人下蛊?”刘君安问。
“确有此推测。”
“目前可有什么线索?”武淳问。
“上回墨阁主问了中毒前日的情况,那晚设宴招待南蛮使节,大家同桌吃饭并无异样。若是席后回房就寝的时间,凭家父的身手,要想下毒没有动静是万万做不到的。”
对于虞平道的武功,获得江湖中人公认,五年前西戎拜火教教主萨木阿哲欲染指昆仑,虞平道带领乾坤、北冥、南冥三大派众高手远赴西北驰援。昆仑一战诛杀拜火教八位长老,重伤萨木阿哲,弟子伤亡过半,从此西域无事。其中虞平道手刃三长老,力克萨木阿哲,居功至伟。而也正是这一战,让天下人看到了虞天策行事、武艺与其父的差距,若不是还有义王府这招牌支撑着,今日的乾坤派已无力号令江湖各派。
“冒昧地问句,是否有大夫验过尸?”刘君安继续问着。
“一代义王被人毒害,传出去非同小可,外人哪怕家中的奴婢、门客、家丁也都是不知道的。”
“若是中了剧毒,定然当场发作,先王从犯病到去世应该有些时间,可能有二,其一,所施之毒能够潜伏一段时日,但既然是潜伏就毫无征状,不会使先王体弱身虚;其二,有近侍之人持续下毒,剂量轻微,可能在殿下说的宴会那日之前就已经下手了,只是那日之后逐渐起效罢了。”武淳说。
其他人相互望了眼,觉得有理。
“家父贴身使唤的奴婢都是家中老人了,近几月也无异常,更无人在家父去世后离开王府。”
“可否将先王生前用过的碗筷起居之物都让我们看看?”武淳想若有人在这些东西上施毒,若没清洗干净可能残留些痕迹,先查一查。
虞朝宗叫了两个奴婢,将虞平道用过的器物都取来,一一摆在地上。武淳与刘君安起身,一件一件细细查看过去。
这时,虞越、虞起二人将独孤泰、左玄请到,与众人见过,坐在一旁,看着刘、武二人查看器物。
全看了一遍,两人相互摇摇头,没有发现。武淳又请求查看虞平道的衣物。虞朝宗又叫奴婢抱了来。
武淳翻到一件泛旧窄袖中衣,绸缎料子,摸着有细微不同,却说不出什么问题。“殿下可知这件衣服从何而来?”
虞朝宗唤来虞天策生前的贴身侍女,侍女仔细瞧了,说:“这是半年前云山司马家送来的缎子,府上缝衣匠制的衣服。”
“云山。”武淳若有所悟。“我有一种猜测。”
“快说来听听。”虞天策说。
“云山上有桂竹,四、五丈高,叶大节长,竹叶带有巨毒,其毒无色无味,若遇人伤口,可致命。有人将桂竹叶捻制成丝,编入绸缎。先王是武林中人,难免会有些伤口。竹丝中的毒本来就少,加之先王身体强健更难以发觉。而中桂竹之毒的人,大多当场殒命,医术上不会记载其缓慢毒发的情形,因此御医也无法察觉。”
众人都惊住了。往前几次都只知道查吃过的食物,用过的茶壶碗具,从未想过竟然用衣物下毒。
“云山,司马家,司马高望。一个江湖小派与王府素来无仇,为何要害家父?”虞天策呢喃着。
“司马家势力与江湖各大派相去甚远,毒杀先王,造成武林动荡,司马高望也捞不到好处。他定是受人指使。”独孤泰说。
“王兄,让我去云山把司马高望带来问问便知。”虞朝宗对虞天策说。
“好,司马高望不是主使也是同谋,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虞天策说。
“云山在京都东南,我回南禺山可以顺道同去,也许能尽点绵薄之力。”左玄站起来。
“好。还请武淳、刘君安两位在京都多留几日,等司马高望带来可以对质。”虞天策对刘、武二人说。两人答应下来。
“我儿墨慎去猨翼山打探,还须回京都向殿下禀报,我便留在京城等他。”墨攻说。
“我离开天池山已有许多日子,先回去了,如果殿下有什么需要我再来京城。”独孤泰告辞。天池山乃北冥本山,在虞国东北,距京都一千七百里。
虞天策一一允了。
虞婉兮的贴身丫鬟翠薇守在浣月轩外,见众人出来,赶紧跑去告知虞婉兮,虞婉兮带了墨惟、楚瑶往王府大门走,与墨攻一行在大门口相遇。
“楚瑶,你为何也在王府?”左玄看见了楚瑶先问。
“回师父,徒儿跟踪。。。。。。”楚瑶毕恭毕敬地开始回复。
左玄连忙打断。“不必讲了,你随我一同回山吧。”
“是,师父。”
墨惟心里一乐,这左掌门是怕忌惮人家长生门的事让大家知道了耻笑,刚才还担心刘君安、武淳两位叔父会说什么,却是白白费了功夫去准备了。
众人相互别过,各自回住处去了。虞朝宗点了十个门客,收拾了行李,去与左玄、楚瑶会合,一同前往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