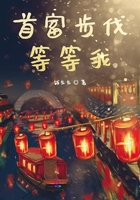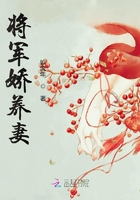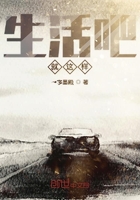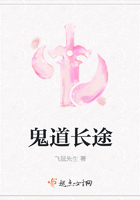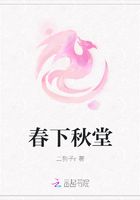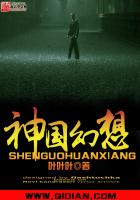当“杏花之香”出现到花宫的时候,终于又勾起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
他们本是法门寺里十八个坐禅的和尚。当时,还是名不符实的十八罗汉。但命运却把他们带到了疆外。
他们最远到过天山之外,最近也只徘徊于焉支山下。
之所以远到天山之外,只因为一个云游胡僧带走了法门寺一件信物。一件足以承受信仰之物。
而当时正是他们十八个人在看守此物。
宝刹失物,当然是他们的失职。而让物归原主,则又是他们的义务。
因为这件法物在当时可是国之利器。是帝都还在长安的老皇帝亲自请进法门寺的。
时,帝都已崇佛法。落在长安的古寺法门寺,自然成为佛俗两界公认的国寺。
能被皇帝亲自请进国寺的当然就是圣物。
这圣物入寺当日,整个长安城可是经声隆隆,法幢云盖。
和尚们直把个金刚菩提,从法门寺念到巍峨皇宫,又从帝宫圣元殿里,念回了法门寺。
这一路上可是拈花净水,敬信非常。
莫说是念经的和尚佛袍袈裟,满面喜光了。圣物开光的沿道,更是挤满了手捧佛香佛花的信众。大家齐声念诵,宛然圣喜当日,又似在超渡来世。
整个长安城都为之激动。满长安都在为这件大事奔走相告。
那阵势可是法门寺自开寺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就连北西军务府,虽负满城戒备之务,但护卫铁士,可也是个个身笼佛性,宛然在景在场的金刚护法。
圣物从太和大殿请出,替老皇帝宣诏的殿前御使,更是素口斋心,清手洁面,一路上可是把圣物如颗心脏捧在手里,一步一步地从朝阳宫走进了法门寺的。
御使如此虔敬,一是因为代表了虔心礼佛的皇帝,另一个当然是借此佛事向全天下宣诏天朝事佛敬佛的信心和诚意。
当然,也在向远音胡地告示万源归佛,天下一心的信念。
场所如此之大,自朝元以来,也是闻所未闻。
这从帝朝皇宫请进法门寺的到底是件什么样的法物呢?
请进佛寺的无外乎:法经、法器、法骨。
法经?法器?法骨?
不错,是法经!
虽不是法器、法骨,但的确是堪称国之宝典的一部法经。
这部法经之所以典贵,是因为它是由胡汉两地高僧数代密修,证验参悟,共心印证,最终由胡汉两文互字共契而成的一部奥义圣书。
此书不同于已经明修见世的般若大书,据说是参透了佛典各级智慧,粹集密、显二宗真源妙谛后证印而成的一部奥义古书。
书虽无名,但名堂却大。
虽是一部书,澄流见源头。
此书既然如此奥妙环玮,諔诡可观,佛俗两界岂能小觑?
对皇帝来说,这书能见证胡汉两地数代共修的友好;而对经堂智慧来说,这书胡汉互应,则能解破许多沉古的奥义。尤其能够证解那些古己失传的教义文字。
而且此书仅胡汉各书一本。是孤本。
胡本留汉。汉本留胡。
法门寺里请进的当然就是胡文本。留进胡地的当然就是汉文本。
书请进法门寺后,就被典于正殿经堂。
法门寺的和尚们沿途来回,哄嗡嗡念着金刚菩提,请回法经不说。而且,又在大宝金堂念经持诵,足足七日。
这七日来,法门寺可是人信沸腾,佛光弥照。
法门寺开寺千年,也未必逢遇如此盛大的法声法事。
寺里寺外,可是高僧云集,都为来瞻仰这部奥义圣经。
念诵谢闭后,佛经自然被当为寺宝国宝镇进了内阁藏经堂里。
而守护此书的责任,自然就由罗汉堂尽事。
时,罗汉堂正有入堂法修的十八个“罗汉”。个个法相硕健,精神抖擞。虽算不是金刚罗汉,但个个心智实在,纯朴可信,到领个守书的任务,还是很可靠的。
对罗汉堂的法座来说,守住此书无疑于守住寺命。
而对十八罗汉来说,不就是要守住一本书吗?
他们才不去认识此书的意义。
法座让守,岂侮陈命。
这一守经年,相安无事。
这法经自然安然匿陈于法寺秘阁。
与法书初入寺门时相比,几年下来后,前来观瞻宝书的人也不如先前那么热了。
因宝书镇殿秘处,纵入寺瞻佛,留心宝书,想见的人,就是想见,又岂能轻易见得真书?
心昧之余,想看真书的,也只有跪进大佛香鼎前烧香祈祷,磕头敬仰,祈愿法源广流,播福众生。
莫说一般信众见不得宝书真容,就是常年供养佛寺的朝官富绅,方丈、法座也是不让见的。
莫说这些供佛供寺的慈善人家了,就是皇亲帝戚,没有上朝允准,也是轻易不让见书的。
更莫说慕名远来,不明底细的游方僧人。
对于这些游方僧人,寺院方丈可是大留诫心的。
首堂法座常告警寺僧,家贼难防。尤其,要谨防那些外游而来到寺中驻足云饭的僧人。因僧家对此类圣物,最易起得盗心。
除非那些盛名已久的大德高僧,慕名前来,或可开个先例。
但要入秘阁观书,也须请了上朝国书,才能允应入阁。
就算是入阁观书,惟其,也不过是在佛眼晦光下观瞻观瞻而已。
书躺在神龛当中,可是半指也碰不得的。
这一年,秋冬时分,恰有一胡僧到寺来访。
方丈,法座皆尽陪同。自然要观瞻寺宝。
这胡僧身份另类,法寺方丈岂能将其视同入寺瞻佛的普通信众,野游僧人?
因胡僧手持正朝信书,且有所来地的国书,方丈、法座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可是,虔敬有加,处处周到。
胡僧入寺当日,倒没有提出观瞻宝书的要求。而是在法门寺里呆够了七日,即别之时,才微言请求,能否有幸观瞻贵寺宝书?
瞅那胡僧身戴仪态,当是胡人国僧。且又手持两朝国书。方丈、法座自是毫无诫心。
胡僧仗着能通胡语,请求看书。这既合理,也合情。更令法寺僧众自生了好奇。
因汉地僧人,多不通胡语。就是法门寺方丈,也是汉生的土豆,哪里会得胡语?那宝书中到底说啥?也正新奇。
胡僧说要看书,方丈、法座自然允应。呼隆隆便前拥后戴,进了罗汉守护的藏经的内堂。令法堂开锁,于那明晦佛光当中,见那宝书现身于鎏金神龛。
与随的法堂、执事个个伸胫交鹤。说实话,虽然书在法门寺里,但真正见过翻页书的也没有几个。就连方丈都一脸好奇,热惺惺地蹭到胡僧跟前,望眼欲穿哪。
胡僧倒悠容静颐,自在从容,合掌念持几句,遂从香龛当中请出了法经。借着晦昧佛光,随手翻了几页,唧哩咕噜绕了几句,只说法义奥晦,智浅难懂,非修得般若上乘智慧,碰不此书,阿弥陀佛,打转个深佛礼,便把经书放回了原处。
斋习不久,胡僧便出寺离别,往塞外去了。
这事都己过去两三个月了。
这一日,朝里突然传诏,请法门寺方丈请那本经书入国殿。
原来,西域国有王来访,说举国礼佛,自己当然也信佛,欲观瞻法门寺里胡文为书的宝典。
因是国是身级,且曾友惠族国,恩于前朝,皇帝便请国寺方丈入宫,携宝典令其观瞻。
方丈殷足,法鼓开道,法座及十八罗汉恪守。欣欣然,赴到宫里。
沿途自然少不了那些个个身笼佛性的护卫铁士。
宝书送到了朝阳大殿。
皇帝亲开佛龛,取出宝书来送到了国王手上。
不了国王看后,久不言语。
上皇窦疑。
再三追问之下,才说那不是佛经,而是西域遍传的乐歌。
国王这么说,方丈才紧张了起来。
明明是法龛当中请出来的佛经,怎么就变成了胡歌?
国王见方丈不信,便随传随往乐师,拿出他手中的乐本,几番对照,几乎一字不差。
方丈这才信了。
随之,知道祸己至矣。
皇帝当面无说。及国宾退席,才龙颜大怒。斥法门方丈捉急查明真相,还来真书。
方丈一身冷汗战战回寺。
寺中叫来法座及罗汉来问,皆大惊失色。
宝书怎会成假了呢?
那宝书自入寺可就一直睡在金刚神龛里,从来没有启过锁印,开过光隙。请进来是怎样的,请出去就是怎样的。
怎会有假?
众僧登时慌乱不已。
慌措间,才想起胡僧窥书一事。
要说启过锁印,开过秘龛,只有那胡僧来时惟一有过一次。
莫非被偷梁换柱,动了手脚?
寺众登时唏嘘不已。
要有嫌疑,嫌疑就在胡僧那里。
要有问题,问题也只在胡僧处。
方丈嗔怨法座不慎,法座又怒斥金刚渎职。
这可干系到全寺僧众的性命哪,天子震怒,什么事干不出来。
现在怎么办?
自然是追那胡僧,要回真经。
于是,这守经的十八个和尚,便急急出寺,沿路打探着追了出去。
这一追自是岭越山岗,沙城戈壁,渐渐追进远处胡地去了。
真是:古寺无由得宝书,宝书无由出古寺。
可怜十八金刚人,为找胡僧到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