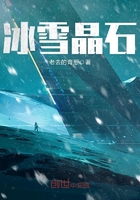杨广捏着纸条左思右想,越想越是坐立不安。犹豫了许久,终于把虞世南叫到跟前。
“伯施,第二场的名次确定下来了么?”
“已经确定下来了,臣正要前往宣读。”
“头名可是《夏日绝句》?”
“正是。”
“你能确定这两场的头名字迹乃是一人所出么?”
虞世南斟酌了一下,回道:“是的,此人诗词实为上等,奈何字写的……写的太过豪放,让人一眼就能识别。”
“如此便好,第三场没有必要了,拆名吧。伯施有劳你善后了,请顾言上楼议事。”
“殿下,殿下这也未免太过草率……于礼不合,于理不合啊!”虞世南惊讶地说道。
“既然两场都是一人夺得第一,第三场还有什么必要?本王心意已决,速速去办。”杨广不耐烦地说道。
虞世南皱着眉头无奈地应下。
杨广紧紧攥着纸条,靠着椅背看着楼顶,喃喃道:“父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做?孩儿十多年的励精图治都要功亏一篑了么?”
“殿下,这……这两首诗虽然笔记想同,但注名却不同。”虞世南去而复返禀告道。
“哦?”这一奇怪的现象将杨广从沉思中拉回来,“却不知所注各为何名?”
“《六月初二虎踞楼书》注名乃是陶德阳,且这三个字更像是顾言所书,《夏日绝句》所注乃是范遥,此名字迹与正文倒是相同。却不知这范遥是何人?”虞世南疑惑地说道。
“嗬!”接到字条后一直绷着脸的杨广笑着拍了一下手,“伯施莫不是忘了?本王前几日可有给各位提起过此人啊。”
“啊?莫非……此人是陶家的那个信使?”虞世南恍然大悟,有些惊讶,“只以为此人观察细致入微,善于把握时局,却不知未及弱冠诗文也是一绝。”
有一员小吏来到虞世南身边,双手递过一张宣纸,轻声说了些什么,虞世南扫了一眼,递给杨广,“殿下,此人第一场还有一坐,因是曲子词而被黜落。”
“是非成败转头空?”杨广看了一遍,摇头笑道,“这范遥不过十四五岁,第一首词描绘自己淡泊名利,怎么第二首诗就要做人杰鬼雄了?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多愁善感。”
“殿下,这韩家……?”虞世南是知道杨广内心偏向主动靠拢的韩家的,不由多问了一句。
“头名还是要给陶家啊,出了这档子事,更加不能得罪陶家了。韩家自己烂泥扶不上墙,实力不足,也怨不得本王,赶紧完了此间事,请顾言一同议事。”杨广叹了一口气吩咐道。
“等等,把范遥也叫上来,这陶文成收的好徒弟啊!”虞世南刚施完礼转身,杨广补充道。至于虞世南怎么样去面对诸多世家的疑问,抗议以及不满,杨广显然不会在意。
文会突然中止的消息以及陶家夺得头名的消息传开,果然令会场炸开了锅。众人或是委婉地询问缘由,或是直接敲着桌子质问,还好大家都是斯文人,没有动手。期间还夹杂着起哄声,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
咳咳,串台了。
“德阳兄,晋王府似乎出了什么大事啊。”
“何以见得?”
“文会仓促终止,且那个小吏神色紧张,看来还不是什么好事呢。”范遥眯着眼看着从楼上慌慌张张跑下来的小吏,在柳抃身前快速说着什么。
“不过,我陶家目标既已达成,接下来已与我等无关。”陶德阳双脚搁在案几上,后仰着身子,好整以暇地喝着茶水。
“德阳兄高兴的太早了,那个小吏已经往这边过来了。”范遥推了陶德阳一把。差点让陶德阳摔了一跤。
陶德阳赶紧坐好,努力装出一副好孩子的样子。
“这位便是范遥范公子吧?殿下请上楼一叙。”
“啊?哦。好。”范遥以为小吏是来邀请陶德阳这个陶家代表的,没想到居然是邀请自己,不由得有些惊讶。
“陶公子,这是殿下让朱大人写的信。请陶老先生亲启。”这位小吏双手奉上信件,又对着陶德阳说道。
陶德阳听闻这信不是杨广亲笔,似乎有些不悦,生硬地接过信。
“范公子请随我来。”
范遥与陶德阳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虞世南下了一楼和杨昭说了几句,一起开始向众人解释起来。
随着小吏上楼,范遥一眼就看到杨广与柳抃等几人正在商议什么。范遥犹豫着该不该上前,杨广却已经看到了他,向他招招手。
“范遥,士别三日当刮目想看啊,几日不见,竟成了陶老先生高徒,还在文会连胜二场,深藏不露啊。”杨广和蔼地说道。
“殿下谬赞了,小子蒙先生错爱,收在下为徒,实乃侥幸。况且今日第一场头名应该是德阳兄才是。”范遥假惺惺地谦虚。
“嘿,小友就别谦虚了,那么难看的字,在场还有谁能写出来?我说怎么第一场王異说是陶德阳所做,心里还纳闷,陶家子弟怎么可能那字那么丑,而且连名字都不署。还要我帮忙写上。”一旁的柳抃笑道。
“小子刚师从先生不过两日,字确实难看了些……”范遥有些不好意思,“那时确实匆忙,忘记署名……啊?原来柳大人那时候是在帮忙写名吗?”
“自然!不然小友以为我在干什么呢?”柳抃奇怪地问道。
范遥干笑两声,也不说话。
“范遥,前番密谈之事你可记得?”杨广突然出声问道。
“啊?”范遥吓了一跳,杨广当着这么多人直接了当的问了。看来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杨广的心腹没跑了,连忙答道,“小子记得。”
“那本王就开诚布公了,上回听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从蛛丝马迹之中就能点破本王所思所想,那你就来帮本王分析一下这件事如何?”杨广作势递过来一张纸。
范遥苦笑地看着杨广手上的字条:“小子有选择的余地么?”
“当然……没有。”
“荣毗遏绝张衡事,上闻而嘉之,赉绢百匹,转蒲州司马。”范遥看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这荣毗何许人也?”
“本王为了探听……关心京中消息,派遣张衡在前往大兴的沿路,以畜牧为借口设置了不少马坊。大多州县都不敢违抗,唯独这个荣毗……”杨广咬牙切齿地说道。
哦,不就是自己弄了个快递,然后被老爸发现了么,这有什么。范遥一点都不在意地说道:“晋王大可放宽心,皇帝陛下没有直接……”范遥斟酌了一下用词,接着道,“直接对殿下采取什么举措,想必这件事也不算什么大事,殿下收敛一点即可。陛下只不过是借荣毗警告一下殿下而已,应该也没有真的放在心上。如果陛下问将起来,殿下大可说是关心陛下龙体。给自己糊弄个理由也就过去了。”
“哦?你当真是这么想的?”杨广不放心地问道。
“这确实是小子的真实想法。”
“一派胡言!”突然有人横插一言,“想必,应当,糊弄,哼!这些都不过是你的想象而已,主观臆断毫无根据,关心陛下龙体?如果被心存歹意之人解读为希望陛下龙体有恙该如何?私设邮驿之罪可大可小,若被小人安上盗置邮驿,阴访京师的罪名就危险了。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种大事岂容一个黄毛小子插嘴?殿下,不可轻信,此事还需尽早上表请罪才是。”
杨广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被这一系列猜想激起了波澜。
范遥循声望去,疑惑地看着一个“仙风道骨”的半老头抚着嘴上的长毛振振有词。心里不由浮起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哪根葱?
“王胄,琅琊王导八世孙。”柳抃看出了他的疑惑,在旁边悄悄介绍道。
王胄?没听说过。范遥不屑的瘪了瘪嘴,懒得与这种出身名门世家看不起别人的人多说话。
毫无根据?老子知道杨广最后当上了皇帝这根据还不够?关心龙体却是有两种解释,但这也要看是谁说的,如果是杨勇敢这么说,杨坚肯定当场龙颜大怒。但是杨广就不一样了,以杨广现在的受宠程度,再加上有杨勇的对比,不论说什么,杨坚肯定都是往好的方向理解啊。
“殿下,此事不被发现还好,既然已经被发现了,还是尽快请罪为妙啊!”王胄见杨广犹豫不决,继续劝说道。
“别啊,殿下,此事本来只是小事,陛下也不过是顺口一提,将这荣毗升了下官而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件事不多提也就过去了,但是殿下如果上表请罪无异于画蛇添足,这分明是告诉陛下,此事有内情啊。”范遥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杨广在任扬州总管期间确实没有任何一次触怒杨坚,一狠心,顶着王胄凶狠的目光坚持说道。
“殿下,臣赞同范小友的意见,陛下既然没有直接下令晋王府整改,想必只是把这件事当作小事处理。以殿下这十几年孝感天地,勤政爱民的表现,想必陛下也不会非常在意殿下偶尔的小错误。”范遥感激地对柳抃点了一下头,对之前怀疑柳抃舞弊的念头更加不好意思了。
“哼!柳顾言为何如此听信小人之言?”王胄不满地看着柳抃。
柳抃白了他一眼,也不多说。
看来这王胄在晋王府的人缘不怎么样啊,范遥在心里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