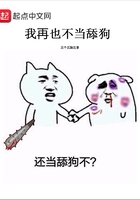现在我们合作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物品;有些人作这件事,有些人作别件事,但是生产品的分配是极幼稚,极不合理的。这很象我们都去工作,制造一大袋我们所需要的物品,每人辛勤工作,使袋充满,于是群起争斗,看谁争得袋中的物品。强有力的自私的人所得过于所需,软弱的谦让的人所得极少,或竟毫无所得。这是缺乏同情及意识的表示。
良知即所谓“道德的意识”。它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辨别是非。良知在野蛮人中是极弱的,有许多差不多没有是非的观念。勃尔顿说:“东非洲人是没有良知的。所谓反悔不过是悔恨错失犯罪的机会。能劫掠及残杀者为英雄,犯罪愈残忍者推尊愈甚。”
达尔文称良知为“人类一切本能中之最高贵者”。这一种本能比他种本能更足使人类示别于别种动物。人的良知经过长时间的培养,能控制自己,使他的欲望完全听命。除了在特殊情形之内,饿者不会再想偷窃食物,受害者也不致残酷地复仇。在高尚的人中,一切本能都服从良知的命令——责任发言时,一切私欲都哑口无言了。
求进步的愿望(兼指个人的及种族的而言),在野蛮人中是极欠缺的。目前有许多野蛮人所处的情境还同数世纪之前初发现时相同。我们容易以为进步是人类自然的状态,但是不是如此的。
古人并不看重这个观念。即在今日,大部分人类并无改良自身、风俗或制度的愿望。即在文明人中,改革家常受猜疑,认为和平之骚扰者,在人性中有一种静止的基本倾向,即使不是静止,至少是转圈子。野蛮人是受这种倾向的宰制的。野蛮人造屋用他祖先造屋的方法,想祖先在一千年前所想的思想。贝克爵士(Sir Samuel Baker)在论“尼罗河流域的种族”一文中指出非洲中部的每一部落都有他自己的形式特别的草屋,然而各部落的草屋,其形式之永远不变正象鸟类的窝一样。他们的服装、言语、风俗和宗教都是如此。
克里克印度人(Creek Indians)笑那些向他们提议改革生活的风俗和习惯的人。豪沙(Houssa)的黑人说:“因为我的父亲效法祖父做的事,我也做相同的事。”利文斯通(Livingstone)谈起几种非洲的土人:“我往往把铁匙送给他们,虽然他们很爱铁匙,但是并不能更改他们用手取物吃的习惯。他们用匙取乳,但是不用匙倾乳口中,他们把乳注在左手中,凑近嘴吃。”泰鲁(Tylor)说底克斯人(Dyaks,Bornes岛的工人)非常反对改变他们的任何习惯,连有人用白人的方法砍伐树木也要反对。能够改变,且认改变为人类的适宜的活动者,只有几个种族,而且在这些特别的种族中也只有寥寥的数个人。
在人类进化的时期中,人性中的各种本能没有一种比人道的本能有更大的发展的。人道就是“胞与”的精神。凡人都是同胞。他们应当互相有同伴的感情,即兄弟之间所有的同情和一致的感情。我们都来自相同的生命的源泉,我们都同样的易感受苦痛,同样的有弱点,走入同样的最后命运。我们应当互相挽着手,我们应当结伴。
现在的世界是一灰色的世界。我们就算不互相为难,还有不少的忧虑——如饥饿、火灾、地震、风浪、疾病、死亡等等的忧虑。我们应当互相信托,互相亲爱,互相同情和扶助,忍耐和宽恕。
下文是从达尔文的书中引来的:“当人类进化,由小部落联合为大国时,各个人应当知道一些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应当扩大他的同情对待全国的人,虽然那些人和他并不相识。这一点是已经达到了,只是还有一种障碍,阻止他的同情扩张到对待各国的人。经验指示我们,倘若这种人的容貌或习惯同我们有极大的差异,要经过长时期后我们才会把他们看作我们的友伴。”
“超出于人类范围之外的同情——这就是对于别种动物的仁慈,似乎是最近获得的善性之一。野蛮人除了对待他所宠爱的动物外不会有这种同情。这是一种最可贵的德行,是在我们的同情逐渐扩大,逐渐温柔时所发生的,直到后来他们扩大到对待一切有知觉的动物。这种德行一经有人实行和尊敬,即由示范和教导传达于青年,到后来无形之间变为公众的舆论。”
慈悲主义是用以称高等的仁爱,即仁爱之心推及于全动物界。慈悲主义是人类同情的最后目标。同情的本能以对于部落中人为起点,由部落而扩大到同盟,由同盟而扩大到国家,由国家而扩大到同种,由同种而扩大到异种。它一方面在人类中不绝的变为浓厚和深切,一方面不绝的扩张到地球上的万物。它最后达于感情的最远的边境。凡是有病痛的人和动物的地方,人类的同情将如天使般的去安慰他,医治他——且降临到踏在我们的脚下的,生长在草中,地中和深水中的那些为我们所忽视,但是知道苦乐的动物。
8.残余的风俗和制度
人是象羊。他们做许多事情,想许多事情,并非因为这些事情很有用,不过因为以前的人曾经做过或想过而已。他们是模仿他们的祖先。每一代都经历过前一代人所曾经历过的许多动作,虽然这些动作的功用在早先是存在的,但早已消失了。
文明是一列车。它拖着不少属于古代的东西——不只是残余的本能,且有残余的风俗、信仰、观念及制度。
风俗极象本能。他们是行动的方式,为一部落或一国的全体人民所遵守。他们可以称为部落的或国家的习惯。
普通以为野蛮人生活于自然界中,有为所欲为的利益,非文明人所能及。这是再大没有的错误,野蛮人是没有一处自由的。无论什么地方,野蛮人的日常生活都受风俗及常例的束缚,并不因为不见诸明文便减少它的约束力。有一著作家说:“非洲的野蛮人中,违反时尚所受的苦痛,正同文明人中一样。”
澳洲的土人甚且不能随意处分他所猎获的禽兽,必须遵照常例分派——一腿分给家族的一人,一腿给别人,脑部给第三人,以此类推。
在南美洲的姆巴亚(Mbayas)人中,“已婚的妇女不许吃牛肉或猴肉,女孩不准分得一尺长以上的肉或鱼。”
在萨莫耶德人(Samoyedes)中,妇女不许吃鹿头,或穿过火后面的草舍。
野蛮及半野蛮人中,办理公事都有一定的很惹厌的方式,是前人传下来的。办事的定法倘有所变更,要引起强烈的反对。
野蛮人的自然而生的保守主义,以及他依恋旧例及旧习惯的倾向,可以用来说明文明人崇仰古代任何遗物的原因。野蛮人停止不进的倾向,我们还没有脱除。
文明人在服式方面往往互相模仿,其愚蠢真不可及。妇女为什么披戴仓门形的帽子,管状的裙呢?不过因为其他妇女是如此的而已。他们没有赏鉴力及创始力,改变服式,只能照样办理。
倘若到一时期,妇女对于艺术具有真正的辨别力,他们就不会只因模仿别人,穿着得象怪物般了。
“decimal”(十进)这一字是一形容词,从名词“decem”引伸出来的,decem是一拉丁字,其意为十。十进制度是数的制度底名称,就是每逢十进一位,十个一为一十,十个十为一百,十个百为一千,以下照此类推。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十进的制度呢?为什么不用八进、五进或十二进的制度呢?我们用十进制是因为它是最良的制度吗?还是以前有某种环境逼着人去用的呢?我们自小就用这十进的制度;我们一点不知道有旁的制度;我们大半是机械的沿用它,永不想到会有其他任何制度。
数的十进制并非最良的制度。人类之采用它是在草野时代受某种环境支配的结果。
在有任何数学之前——在有几何、三角、代数或算术之前——人是用手指计算的。他们不能心算,他们尚未创造数目及其他数学上的符号。
数学开始是用手指计算,人的手指有十,这件事实,这个环境,就是产生十进制度的原因。
倘若人每手只有四指,不是五指,他现在或者有一个八进的制度以代十进的制度了。八进的制度正同十进的制度一般好,或者更要好些。倘若人在每手上有六个手指,不是五个,那么我们现在将有一个逢十二进一位的制度,或者要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好得多,那是毫无疑义的。
十二进的制度是一种比十进的制度更富于柔性的制度。十只能被二及五所分,而十二可以被二、三及四所分。
当我们说“three score and ten”,我们是用旧时的残余的手指法计算,每一score等于二十,墨西哥人就用它代“一个人”,因为正相当于一人所有的手指和足趾的数目。
希腊及拉丁语是残余的语言——已经失其效用的语言,但是还没有失其存在。
无音的字母是字的残余的部分。一切无音的字母以前大概是有音的。但因用它们的那些人的习惯改变了,有许多字母也变成没有用了。
试以Knight:一字为例。K及gh是无音的。
但是我们的祖先是读音的,象德国人现在读那个Knecht字一般。所以在法文字中Temps之意义为Time,p及s是无音的。但是罗马人(法文这一字是从他们得来的)是读Tempns的,各个字母都有音。
我们适正生在正要使许多英文字的拼音变为合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在Tho字之后加上ugh,使这个字加多了一倍不需要的字母呢?为什么Through这一字我们不照它的发音去拼呢?
人生太短促了,不能花费了半生去学习拼音。我们应当每音有一字母,每个字母有一个音。那么言语中所用的字,无论谁(不论他以前所见过这个字没有)都能在数日之内学会拼了。
我们在言语中所不用的音,我们在文字中应将代表那个音的字母除去。
我们所用的二十六个字母是早就有的。这些字母的现有的形式是从原来的模型遗留下来的,不过经过许多改变而已。字母经过了许多人的手到我们的手里所以变为现在的特殊的形体。英国的字母是从罗马来,罗马又从希腊得来。希腊人受之于菲尼基人,菲尼基人又从埃及的书卷的抄写者得来,抄写者又受之于雕刻者,他们在人类史的最古的时代把稀奇的文字刻在青石的坟墓上。
A,第一个字母,原来是鹰的图形,经过长期的剥蚀而成这形体;B原来是鹤的图形;C象御座;D象手;E象蛇;H象筛;K象碗;L象雌狮;M家颚;N象水准线;R像嘴;S象圆;T象套索;X象椅背;Z象鸭。
人类婚姻的最初的形式是掳掠婚姻。男子大都向别族劫掠妇女,用强力带她回家。
强力和结婚之间的关系已经根深蒂固,到后来娶妻久已完全用不着强力的时候还没有脱去那种貌似掳掠的形式。它后来就渐渐的成为一种纯粹的仪式了。
文明人的婚姻的各种仪式中有许多从古代结婚的形式遗留下来的东西,订婚戒指是旧时作俘掳的证物,在妇女应许作奴隶及专诚事奉丈夫时所收受的。新郎来同新娘去结婚是掳掠而去的变形。度蜜月是带到远处去。新夫妇别离女宅时亲友的投掷物品是旧时有人去抢亲时亲属用武器来抵御的模形。
在政府的形式由****而急剧的变为民主的各国中,常有不少****的形态遗留于新秩序中。英国的元老院在以前是扶佐国王的立法的主体。但是它的权力已经逐渐的移到众议院去了,众议院比元老院更真实的代表人民。英王的情形也是如此。原来国王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它的权力已渐受限制,特权渐被剥夺,初则被元老院所夺,后又为众议院所夺。
我们的工业竞争制度是一种残余制度。它是从古代战争的时期遗留下来的。它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不适用于分工及合作的世界。文明人最富于同情的动物。他们有替人家设身处地的性质。
他们的理想是“金箴”。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逼着我们互相争胜。它是使人心化硬的东西。它是一种人吃人的制度。它不但不能注射“胞与”的感情,且逼着我们互相吞食。这种制度将要消灭了。现在已由这种制度过渡到一种建筑于同情和合作之上的制度。
所谓文明人的“文明”是一种改造的东西,它所由引伸出的是野蛮人的“文明”,这是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能找到的证据的。在这种引伸出的文明中,我们随处能找到风俗、法律、信仰、言语、理想及制度的旧形态,这在目前是不再有作用的了,但是象我们身体上的阑尾、毛发及我们性质中之打猎和战斗的本能一样,并没有消灭,不过多少总有些衰颓而已。
我们能辨认这些残余的形态,俾可更敏捷地脱离他们的羁绊,同时回过身去,背朝着它们,努力向一更完满的世界进行,这于我们有极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