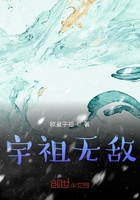麻辣滋味,重庆火锅
浸泡在重庆的时光里,脚踪所及之处,空气里总是漂浮着一种特殊的气味,让人忍不住要痛痛快快地打上几个喷嚏。满眼大大小小、光怪陆离的火锅店招,引得人不由自主地侧身进堂,只见翻滚着辣椒花椒的火锅绽放出艳艳的红。一片毛肚就一口老荫茶水,在荤素与生熟、麻辣与鲜甜、嫩脆与绵烂、清香与浓醇的美妙融合之间,在蒸腾的袅袅烟雾里,回味麻辣,品味重庆。
从码头到华堂
那是一个冬日,江风呼号。临江吊脚楼里,人们夹袄围脖加身,依然紧闭门户,生怕漏进来的江风吹散了早餐所聚的能量。偶尔有晚睡晚起的麻将客,撑开临江的窗户,“哗啦啦”将夜来的排泄物倾下,倏忽间稀释在翻滚的江涛中。刺鼻的恶臭随风且散,而一股又麻又辣的鲜香滋味引得他再次探头出窗。
上游不远处,船桅林立的小米滩船头上,一群粗布短衫的粗豪汉子正围着烟雾腾腾的瓦罐或蹲或坐。饮一口烧酒,从瓦罐里打捞出一大夹筋筋吊吊的东西,稀里呼噜塞进嘴里,骂一声“龟儿子的”,便拉着同伴吆五喝六,划起拳来。
麻将客缩了缩被江风吹得发紧的脖子,关上窗,顾不得跟家里人打招呼,便提着水烟袋出门,循着香味直奔码头。
几天后,码头边上的大众饮食摊多了一副泥炉,炉上砂锅里翻腾着辣椒、花椒配就的麻辣牛油卤汁。旁边的长条桌上一溜粗瓷碟子,装着生切成薄片的毛肚、肝腰和牛血旺。一群夹袄短衫寻着香味围拢来,看看翻腾的砂锅,再看一眼碟子里的牛下水。
“这些东西,也敢拿出来卖钱?”
“尝两块嘛,不好吃不要钱!”
等到碟子空了,一群人抹着额头的细汗,发出阵阵感叹:“硬是好吃!”其中一个笑着问道:“伙计,这些喂狗的东西,吃了得不得死人?”
“得不到吃才要死人呢!”
也不知过了几年几月,码头和街边上,挑担子零卖贩子随处可见,担头泥炉一具,炉上砂锅换成一只分格的大洋铁盆,盆内翻滚的,依旧是又辣又麻又咸的卤汁。腰包里只有铜板的码头苦力、贩夫走卒和城市贫民围着担子派开,站在摊前,怀揣自备的酒壶,自选一格,拈起碟里的“水八块”生片,且烫且吃。吃饱喝足之后,笑嘻嘻地吼一句“伙计,结账”,潇洒地在案板上拍下几个铜板。
时间到了民国15年,下半城南纪门专杀从川黔大路赶运来的菜牛的宰房街(现长江大桥桥坎下),颇具生意头脑的马氏兄弟廉价收购不易售出的牛毛肚和血旺,在此开了一家以毛肚为主要菜品,仿市井“水八块”的制作和吃法的红汤毛肚火锅馆。将泥炉从担头移至桌上,分格铁盆换成赤铜小锅,将毛肚漂白洗净,去梗,外加一碟芝麻酱和蒜泥的调和蘸料,重庆毛肚火锅由此正式得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火锅也从沿街摊点,跃升于庙堂之间。火锅已俨然成为重庆美食的代表和城市名片。以至于人们说:“到重庆不吃火锅,就等于没到重庆。”
抗战时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专业火锅店,甚至冷饮店、咖啡馆、大餐厅也卖起火锅来。店内或圆桌或方桌,矮桌配矮凳,高桌配高凳,桌面中央挖一个圆洞,放入泥水炉,卤汁用的是铜锅或铝锅盛装,装菜用的是精致瓷盘,有的店还备有冰柜。茶壶、茶杯齐备,顾客边吃火锅边喝茶,以解油腻。菜品也从单纯的牛下水(肚、肝、腰),发展到牛肉、鲫鱼,以及各类荤素。抗战时期,许多从前方撤至后方的外省人也渐渐爱上了火锅。无论是贩夫走卒、达官显宦、文人骚客、商贾农工,还是红男绿女、白发垂髫,都欣欣然为座上宾。当时最负盛名的是临江门杨海林开的“云龙园火锅店”和杨述林开的“述园火锅店”、保安路兰树云开的“一四一火锅店”、五四路杨建臣开的“不醉无归火锅店”,还有在南岸海棠溪桥头由李文俊开的“桥头火锅店”。
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人们尚为温饱发愁的那个年代,火锅成为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于是乎,人们开始在家里,凭着记忆炮制口味各不相同的火锅。虽然锅内尽是萝卜白菜,但唇齿间的麻辣鲜香,也让围坐在一起的老老少少其乐融融。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暑假,第一次去到江北姑妈家。瘦瘦高高的表哥从姑父手里接过一张当时最大面额的人民币,拉着我飞也似的出了门。
坐轮渡过江,表哥领着我在大街小巷之间梭巡。时近中午,表哥拉着饥肠辘辘的我来到一座不知名的桥头下。
一字排开的小吃摊点上,食客满座。看着举筷挥箸的食客,巴不得胡乱找一个座位,赶紧要一碗鲜亮的红汤面。表哥似乎并不着急,在各个小吃摊前梭巡徘徊,最后在一口已经围坐了七八个人的特大号铁锅前就着高大桌凳坐下。
盛夏的中午,头顶上烈日暴晒,铁锅下炭火熊熊,锅里汤汁翻滚。不等菜上桌子,我们早已经汗流浃背了。环视围锅而坐的食客,临锅举箸,居高临下,虎视眈眈盯着筷子间夹着的菜品,顾不得胡撸一下头上的滚滚而下的汗珠。更有吃得性起劲的,干脆脱掉上衣,赤膊上阵。
夹起一片毛肚,学着表哥的样子探进滚沸的锅中。也许是探得太深,被热气一燎,手不由自主地松了。眼看着毛肚在锅里随汤翻腾,却怎么也打捞不起来。邻坐一位眼镜大叔手疾眼快,夹住毛肚往碟子里一探,飞快地丢进嘴里,一边嚼一边笑:“鸡公叫,鸭公叫,各人拈到各人要。”引得一众食客哄笑起来。
好不容易烫好一筷子扔进嘴里,那个麻,那个辣,那个烫,不敢细嚼,只在口舌之间来回呵了几口凉气,便囫囵吞下肚去。只留下唇齿间的麻辣和食道肚子里滚烫的熨帖。
一顿火锅吃下来,我们成了“落汤鸡”,衣裤皆湿。走在江岸上,微风一吹,怎一个“爽”字了得!
寻找记忆的味道
品尝过无数有名无名的火锅后,坐在重庆古朴典雅的桥头火锅店内,无数有关重庆火锅的记忆碎片,倏忽连缀在一起,赫然间映化成一幅重庆火锅的“清明上河图”。看着一个个正襟危坐的食客,为着体现全民素质,温文尔雅地举箸而食。突然怀念起多年前烈日下差点连舌头一起吞下肚去的“桥头”大火锅来。
渐渐地,除非应酬,那些高尚典雅的火锅已慢慢从我的生活中淡出。常常流连于街边小店,彩条篷里的夜火锅,呼三五好友,以最本真的方式,围着火锅,赤膊上阵,汗水和着油汁流淌,喝得晕晕乎乎,吃得忘乎所以,不亦乐乎。
移居成都后,最爱的依旧是火锅,只是成都的火锅少了些火爆麻辣,多了些绵软平和。即便是照常呼朋唤友,啸聚火锅边,依旧觉得不够酣畅淋漓。每每回到重庆,吃火锅,找寻记忆中“辣得死去活来,麻得翻江倒海”的味道,几乎成了固定的节目。
偶尔在网上看到,抗战时期一些曾在重庆居住后移居到台湾的同胞,在离开重庆数十年后,发表怀念重庆火锅的专文,提到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楷杷山,火锅小吃店,伴我八年度磨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几十载风雨之后,对于火锅的记忆依旧刻骨铭心,这让我不能不引之为同道。
火锅对对碰
麻辣火锅肇始重庆,却为川人所共享。但加上不同的城市名称后,就有了各自的性格和脾气。而不同的性格和脾气,自然会碰出各式各样有趣的火花来。近年来,重庆火锅与成都火锅时常发生有趣的碰撞。
巴蜀未分家——也就是重庆没有直辖之前,成都人会指着重庆火锅的招牌对外来的朋友介绍:这是我们四川的特色哟。重庆人也默认四川火锅等于重庆火锅。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可到了今天,重庆人开始为麻辣火锅正名。重庆火锅历史悠久,并以此为骄傲。从当年码头船工们自创的陶炉煮汤料烹制无人问津的牛下水开始,到今天,重庆火锅已历悠悠百年历史。重庆火锅看重自己的老招牌,推出一系列以老字号、老传统、老工艺为概念的“老灶火锅”,以期人们从“老”字上看出火锅的本源来。成都火锅虽然不能在这点上争锋,但一向嘴硬的成都人会说:火锅可是老祖宗的玩意儿,几千年前就有了。想当年清朝嘉庆皇帝摆出1550个火锅的千叟宴的时候,重庆火锅还在江边上陪船工们喝冷风呢!这样,成都人便在泸州或宜宾江边上的船工们身上去找火锅的渊源。反正是祖宗的玩意,弟兄姐妹大家都有继承权。所以,成都人更愿意把火锅叫做成都火锅或四川火锅。
行走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里,你会看到冠以不同地域名称的火锅店招:重庆火锅,成都火锅,四川火锅。看得人晕头转向,不明所以。对于大多数巴蜀以外的食客来说,是很难在看似一模一样的“麻辣烫”之中找出什么差异的。为什么吃起来同为麻辣味道的火锅,会有这么多的名称呢?
其实,细心者会从店名和口味上发现重庆火锅和成都火锅的区别。
重庆人粗犷豪放,表现在火锅上也是“大江东去式”的豪放,连店名都大有气吞山河之概,“巴将军”、“巴倒烫”、“刘一手”、“不醉无归火锅”,听来便颇有重庆的豪侠气质。体现在口味上,以厚重麻辣见长,对麻的感受永远不及对辣的渴望。成都火锅在店名选择上,充分显示出蜀文化灵秀深邃的特点,“皇城老妈”、“芙蓉国”、“狮子楼”,让人感知一斑。口味上也如冬日里在皇城根下晒太阳的老妈妈,在相对清淡中追求麻与辣的均衡。
无论如何,重庆火锅来源于民间,升华于庙堂,无论是贩夫走卒、达官显宦、文人骚客、商贾农工,还是红男绿女、白发垂髫,其消费群体涵盖之广泛、人均消费次数之大,都是他地所望尘莫及的。作为一种美食,重庆火锅已成为重庆一张色彩缤纷的“麻辣”名片。到重庆,吃火锅,已经成为固定项目,以至于人们说:“到重庆不吃火锅,就等于没到重庆。”今天的重庆火锅在不断地碰撞和学习中,不断融汇深厚的川菜文化,还兼容、博采众多兄弟菜系的特征和长处。人们不仅可以品尝重庆火锅的“老三篇”——毛肚、黄喉、鸭肠,还有火锅鸡、火锅鱼、鱼头火锅、肥兔火锅、牛筋火锅、龙马童子鸡羹锅、虫草鸭羹锅、海鲜火锅、串串香等品种口味和吃法各异的火锅。
随着岁月的推移,重庆火锅逐渐风靡全国,名扬四方。在北京,大大小小的火锅店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上海,重庆火锅猛烈冲击上海滩;在南京,重庆火锅扎根大小饭店、百姓人家;在深圳,“山城火锅”随处可见;在天津、昆明、贵阳、拉萨、西安……重庆火锅已流传全国,香飘四海。
链接——话说火锅
在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美馔佳肴数不胜数,地方风味千姿百态,风格迥异。有一种美食东南西北各方都有,名称却五花八门,口味也不尽相同,那就是火锅。最有名的是四川的重庆火锅、东北的白内火锅、北京的涮羊肉、湖南的大边炉、上海的菊花锅等等。从词义上讲,“火锅”既是食品名称,又是炊具名称。今日火锅的容器、制法和调味等,虽然已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但一个共同点未变,就是用火烧锅,以水(汤)导热,煮(涮)食物。
这种烹调方法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可以说它是火锅的雏形。《韩诗外传》中记载,古代祭祀或庆典,要“击钟列鼎”而食,即众人围在鼎的周边,将牛羊肉等食物放入鼎中煮熟分食。虽然还不能认定为早期的火锅,但从围坐烹具旁,直接从中捞取食物进餐来说,与今日的火锅有相似之处,可说是火锅的萌芽。《中国陶瓷史》中介绍的“樵斗”,是放在火盆之中,以炭火温食,可能是暖锅的原型,东汉的墓葬中已有出土。北齐的《魏书》中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可能是当时火锅一类的炊具。三国时期出现了一种类似火锅的“五熟釜”,锅中分五格,可调五种味道,类似现在的“多味火锅”。1984年,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了一幅墓葬壁画,画中绘三个契丹人席地而坐,围着一个火锅,有一人在涮羊肉,画上有桌,桌上放着两个盘子,还有酒杯、酒瓶、羊肉块等,描绘的是我国辽代人涮羊肉火锅的情景。
历经秦、汉、唐代的演变,直到宋代才真正有了火锅的记载。宋人林洪在其《山家清供》中提到吃火锅之事,即其所称的“拨霞供”,谈到他游五夷山,访师道,在雪地里得一兔子,无厨师烹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沃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半吊子),候汤响一杯后(等汤开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涮)熟,啖(吃)之,乃随意各以汁供(各人)随意沾食”。从吃法上看,它类似现在的“涮兔肉火锅”。五六年后,林洪在京师朋友家也见到这种吃法。他认为除兔子外,还可涮猪、羊肉,并称之为“拨重供”。铣,是一种有柄有流的小烹器,类似鬲,和今之砂锦(或称吊)子相似,而我们现在也有用陶质的砂锅来做火锅炊具的。此记载说明南宋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吃火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