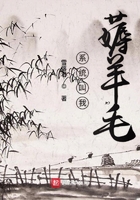“国公饶命,饶命!求国公饶命!尊夫人的死与下官无关啊!求国公高抬贵手!饶下官一命!”
中年发福的知府一只手捂着鼓得像怀七月双胎般的肚子,单手爬向坐在铺满密信账本的长案上的黑影。浓黑的血从他七窍中流出,脸上又粘着土,血和灰尘还有眼泪混在一起,样子真是凄惨。
黑影一脚将他踹得翻了个面,抬手弹指,冷眼看着知府肚子里刚安分下来的东西又开始蠕动。
“啊——!”
“我招!我全都招!国公快让它们停下来啊!”
黑影再打响指,跳下长案走到知府面前:“说。”
知府扣着地砖缝爬到黑影面前,伸手想揪住黑影的直裰下摆,却又被踢开手。他捂着手趴在地上,涕泪横流:“下官真的只是奉令行事啊,国公!”
“别废话。”
“怜州县主执袁相手书,命下官翻看国公返京前的档案,下官不能不从……啊!”
黑影用脚尖碾断知府胫骨,冷笑:“不能不从?”
为保军将安心,晋朝校尉以上武官的家眷档案无朝廷明令不可查阅。彼时袁相权势已被晋皇削去四成不止,凭不再炙手可热的他的一纸手书难道就可为所欲为?笑话。
“是下官要讨好县主!是下官贪得无厌!是下官擅做主张用国公的家眷讨好县主讨好袁相!”
脚掌前移,黑影又碾碎知府髌骨:“你当本公蠢吗?”
踏平那个村子的骑兵明里归郡尉管辖,但他们的军备之精良,分明是皇族直属的铸造司才做得出的东西。
“说。贵妃母族张氏、后党、兴王、皇帝,到底谁给你下的令。”
“是皇后娘娘!是娘娘密旨!”
“密旨在何处?”
“烧,烧了。”
黑影踩在知府手上,脚尖慢慢施力:“说实话。”
“下官句句属实!国公!下官真的句句属实啊!”
黑影把脚从知府手上移开,踱回长案坐下。他披在身上的半旧斗篷里露出一双白得发青的枯瘦的手,那双手里护着的是一个赤红的襁褓。襁褓里没有婴孩,边缘有些发黑,不像是旧了,反倒像是浸透襁褓的血迹终于开始干涸。
“她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他骤然抓紧襁褓,真的有鲜艳的液体从被他用指缝挤压的薄被中流下,“若不是为了救差点被你们活活烧死的村名,她本可以活……哈,多可笑。你们说她是害人食人的妖魔,她却甘愿为了你们视作草芥的庶民去死。哈!可笑!”
知府全身抖着,忍不住抬头去看黑影被月光照亮的脸。那张脸曾被无数闺秀爱慕,此时则流着泪挤皱成一团,有些狰狞可怕。
“本公最后问一次:到底谁给你下的令?”
“是,皇后娘娘。”
黑影哼笑。他亲自审过的战俘比刑部拷问过的犯人还多,又怎么可能被他们蒙骗过去。更何况,知府也不是他第一个找上门的“仇家”了。
其他人开始的时候不照样把所有的责任推在袁世杰那奸相身上,最后不也是供出了自己真正的直属上司?这看起来圆滑世故胆小类鼠的知府虽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但终究也只是人。
他会供出他的主子来的。
黑影动作轻柔地抚平襁褓上被他抓出的皱褶,抬眼看向知府的腹部:“肺、胃、肝、脾、肠,都只给他留一半。”
“不!啊!住手!”知府拖着一条废腿在地上打滚。
黑影知道知府此时所承受的感觉有多折磨人。他以身饲鬼的第一天体验到了同样的痛苦,当然,他将体内的厉鬼都收为己用后就不再受此折磨。
但是还不够啊。
“要不眼球也只各留一半好了。”
“不要!”知府疼得从地上弹起,颤颤巍巍又爬到黑影脚边,“是陛下!我是陛下安插在袁党中的暗线,我从来只直接听命于陛下!”
黑影弹指两次,只让知府眼上和肺里的东西停下,其它脏器上的依旧在啃咬“食物”。
“国师算出您的妻子是黄金狮!黄金狮的出现是灭国之兆,陛下得知后令我务必全力帮助县主查出妖魔食人的‘真相’并将其剿杀!”
“这么说,她的狮骨已经被送到京中了?”
“是!其余黄金狮在袭击袁贼府邸时被国师一网打尽后,全部十具狮骨都被献给了陛下!”知府一手捂着满是血的左眼、一手按着腹部,扭着身子朝黑影又靠近一寸,“我知道的全部都说了!您就给我个痛快吧!求求您!让我死吧!让我死啊!”
黑影从长案上站起左手抱着襁褓,单手拔出长剑。
知府看着黑影手上长剑剑锋的冷光忽然解脱般笑了,还对黑影磕头:“多谢国公开恩,多谢国公开恩。”
“今日起,我不再是晋朝元帅安平国公,只是方周。”
方周手中长剑落下,从只被他踩成半残的知府右手手指开始,依次从关节处将知府四肢切断。直到将其切成人棍,他又用剑尖插着知府肩膀将之翻面朝上,切断其喉咙而不伤及血管。
“让他活到明日。”
他看着知府的眼收剑回鞘,抬步走出屋门。
门外月凉如水风寒刺骨,两个穿夹棉厚袄的小厮尽心守着院门,不曾听见知府书房中的异动,以为一切如常。方周低头叹出一口热气,跃上屋檐向他的家所在的方向离去,身形疾胜闪电。
翻过三五个山头,三年前被她施法用天障保护起来的村庄就在眼前,方周却忽然方向一转,落到山阴面的一个坟包前。
“肃琉,我越来越像个恶鬼了。”
方周解开斗篷靠着无字坟碑坐下,小心抱着怀里的空襁褓。
他的所作所为残忍吗,过分吗?
当然是。
可是这些比起肃琉的遭遇又算什么?
火焚、生剥整皮、活剐筋肉,这样在仧朝之后已被废除的酷刑,他们竟然能用在她身上——他们竟然下得去手——他们竟然敢对她下手!
“啊,苏柳家的,你果然在这。”是个属于农家妇人的大嗓门。
方周有些费力地睁开眼,只能勉强看到个模糊的人影。
“苏柳家的,你是不是又出去找人寻仇了?喂,你怎么了?难道被人伤到了?”
农妇在方周眼前挥手,方周却没能应她,只咳出一口血。
“喂,苏柳家的,你别吓我。快醒醒!”
“苏柳家的!”
“……”
“喂,肃琉家的,该起床干活了。”
青裙白衫的新妇围着巾帼,叉腰站在清晨阳光刚刚晒到的床铺边。床铺上不规矩地躺着个长发蓬乱的糙汉子,让她等了一刻还是用棉被包着身子把脑袋埋在枕头上没反应。新妇忍无可忍,伸手抓着被角要把被子掀开。
棉被确实被掀开,但新妇在棉被重新落下前被拉到了床上。
“你果然是在装睡。”新妇皮笑肉不笑。
“哪有新婚第二日就吵着要下田的姑娘。乖,叫声‘夫君’听听。”
新妇一拳砸在她丈夫的下巴上。
“这屋子是我的,这床是我的,这床上的你也是我的——少废话,快起来跟我去把今年的禾苗种下。”新妇抬手捏住丈夫的鼻子,一字一顿地笑喊,“肃、琉、家、的。”
方周忽然睁眼,却看不见喜欢素面朝天的妻子。他撑着地坐起,发现自己也不是躺在他为她搭建的茅屋农舍里。此处四壁昏黑,只有他面前一盏铜灯点豆。他低头,目光落在她在他手腕点的一点朱砂上,忍不住又想:若是自己能预料到今日,当初还会不会抛下她去征战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