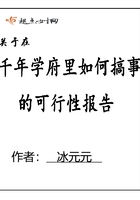魔君在笔尖留的一点魔息刚好够破妖都的结界。
本来妖都因护城结界的存在,城门和护城河都没有建造的必要。魔君多年未至妖界,他记忆中的懒散妖族可不喜欢做太麻烦的事。妖皇骨天也不像是喜欢浪费钱财精力的君主——护城河底薄苔不生,城墙上的刮擦痕迹还都是宴漠出招时动作粗糙才留下的——如此崭新又毫无用处的防御工事,他只要派一位魔将带十数个魔兵就能在一旬内完成。
其实骨天以命来养的结界怎么可能真的就被他用一点魔息就破了?那好歹是他帮扶过的妖皇。
妖将的尸身开始消散,魔君眯眼,盯着从尸体颈后的某一点漫开的细纹。
宴漠和方周规规矩矩站在魔君两侧,没等来魔君继续攻城的命令,只听见一声脆响。
“咔!”
像是只有蝉翼厚度的琉璃制品碎裂,刚显出淡灰色实体的结界转眼间即被裂纹布满,又刹那崩碎。结界才显出一点细纹时从里面泄出来的风就带着些若有似无的古怪味道,至笼罩住整个妖都的结界彻底消失,从里面吹出来的风带来的浓重气息才能被确定成是血气。
比预料中的倒是淡去不少。
魔君轻笑出声,摘下一直挂在腰间缠红丝流苏扇坠的沉香木雕扇,展开在鼻前轻摇:“还真是份吝啬的见面礼。”
方周嗅觉寻常因而没察出异状,宴漠则是直接拧了眉,将一只不知何时点燃了的香炉举在魔君面前,难得语气严肃地躬身道:“请主上移驾。”
魔君压下宴漠手里的香炉,转头吩咐方周:“去洗干净。”
“是。”方周也不问,从乾坤袋里拿出水囊向那妖将灰飞烟灭的位置疾行。那边没有尸体,只有一滩鲜血残迹。
妖族不该拥有的鲜血残迹。
宴漠却又端起香炉,挡在魔君面前:“请主上移驾回宫。”
魔君打着扇子没说话。
“属下等会为您另寻他法。只是现在,属下恭请主上移驾回宫。”
魔君不喜不怒,判断好风向后朝前踏一步,移形到城墙垛口上坐着。只给宴漠留下一句话:“你早就明白本座是来求什么,现在再拦有什么意思?”
……
时间将至晌午,日头烈,离开古树的树荫大概就只能往周围深邃到让人恐惧的林子里才找得到避暑地。现在气温略高,烘得枯坐了一两个时辰的雅沙差点又要再睡过去。
魔将宴漠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怜香惜玉,给云罗的药量太足,结果她到现在也没醒过来。自然,要雅沙解去余毒并不难,不过她暂时不想。
雅沙弹指展开一个结界,盘腿静观片刻,微微蹙眉。
“呲。”
有什么东西刮蹭到了她的结界上。
从她把酒收进乾坤袋后就开始在周围徘徊的那些东西。
雅沙叹出一口气,附身查探睡在她右侧的云罗的脉搏,再凝出两道魔息放进云罗眉心,然后抬头细打量着身旁这一棵三人合抱的古树,选一个合适的树杈把云罗给扔了上去。
替云罗摆出一个足够舒适的姿势,雅沙为求稳妥,在她身上又叠加着布了几层结界。
做完这些,雅沙理了理自己的衣袖袍脚再走上前,抬右手贴在触感像是皂泡的结界璧上。
“因为云罗之前出手暴露了踪迹,所以才跟了过来吗?”
没人回答她,只是原本温和的风忽然没了声息,空气粘滞得叫人不安。
雅沙微微偏头,那张和云罗十分相像却又平庸至极的脸,因为她嘴角嘲讽意味太浓的笑,美得可怖:“我真的很好奇——既是正统,你们怎么总喜欢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
“呲嚓——”像是刮在骨头上的一声长音,浸得人牙根酸麻。
“呵。”
雅沙低头轻笑,足尖发力且右手成爪,瞬间冲到结界之外,揪着故意刮蹭的那东西向左侧挥扫。地面上干土卷着枯草扬起一条百十米长的尘烟,却看不见与雅沙交手的实体。
有东西同时从两侧攻来,过十数。雅沙伸手抓住最先靠近她的两者的“脖颈”,对上后继者时右腿侧踢,左脚发力使身体极速转了一周。空气被她带出一个旋涡,不断向她扑来的东西都被剿杀。
于是风又停了。
雅沙叹气,从袖袋中取出一条缟色发带将披散在后的长发拢成一束。
“真的还想继续啊?”
渐渐向她包围过来的这些“人”,以上仙的修为都只能勉强看见点模糊的影子。当年玉子卿从它们组成的杀阵中把她们姐妹俩救起来的时候,因为看不真切,似乎也只以为这些不过是阴邪之气聚集成的精怪。
不过即使能像她这样看得一清二楚,实际上和只看得见影子也没什么区别。
毕竟用孤魂野鬼缝补出来的东西本来也就没什么能入眼的实形。
无眼无口无心,四肢残破扭曲,行走移动时还会有浑浊黏稠的液体从它们身上掉下来。像是一滩又一滩,被从沼泽里甩溅出来的淤泥。
这些被称为“魂偶”的东西和淤泥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它们曾经确实都活过。
看着还在从地下不断冒出来的魂偶,雅沙有些头疼。
撞到她手上可就真的要魂飞魄散了啊。
她和云罗不同,仙家推崇的慈悲可一点都没记到心上。所以哪怕眼前这些东西生前也是安于平宁的无辜生灵呢?
差点忘了。
这些魂偶本来就是给云罗准备的吧。
雅沙苦笑抚额:“是了,若能看见你们的是云罗,怕是连剑都不敢拔出来吧。”
四周无风,但若是凝神细听,能听见千万号哭。
或寿终、或枉死,这些被强行聚集在一起的残魂们,无论生前有过多么美满幸福的回忆,现在都只剩悲和怨。
凡修行之人,魔修也好,仙修也罢,不必用心也能从他们的号哭里听懂他们的悲伤。那是真正的辜枉,本应入轮回转生的魂魄却被人用术法拘着,做他们不愿不敢不能的事。莫说年月,分分秒秒都是比地狱酷刑更可怕的折磨。
若是云罗,必然恸愤异常。又怎么还能拔鞘亮剑?
可惜,她不是云罗。
雅沙脱下广袖及膝的麻布氅衣、撤去腰间围裳,只着身上便利行动的衣裤前踏一步,脚尖下即有一圈焰心银紫的白色火焰荡开。火焰没有温度也没有声响,安静地把那些被她击散后再无法聚集的残魂“泥迹”吞下,一点一点,烧到灰飞烟灭再无痕迹。
新爬出的魂偶受火焰威慑,半怒半惊地吼叫着退远几丈。
焚尽了残魂,那白色的火焰就拖着焰心聚集在雅沙身前,凝成一束,最后化为一柄被银紫色藤曼缠绕的纯白长杖。
雅沙伸出左手握住悬空半尺的长杖,以杖尾在地面轻点。
坚韧到足以刺穿岩石的根茎从土里冲到了地面,而她站在根茎生发之处,浅笑盈盈。
魂偶中也分等级,大部分是一开始就冲到雅沙面前来的这一种,只会用进食一样的动作来攻击。但百千个魂偶之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相对完整的,会做一些思考,能操控比自己还不如的其他魂偶的“灵偶”。
百余米之外,就站着十数个拥有了“意识”的灵偶。
不过灵偶之后应该还有更“权威”的操纵者。
地面上的火焰暂时被收束后,魂偶们再向雅沙慢慢聚集来。谁想走不到三步,他们又被强制停下了脚步——无数根茎从他们脚底穿出,套索一样将他们圈在原地。
白色的火焰顺着根茎延烧开,雅沙没注意看在根茎束缚里挣扎的魂偶,她闭上了眼睛,忽然伸出右手掐住某一人的脖子。
“什么时候!”那人惊骇,隐藏于空气中的身形完全暴露。
雅沙手上并未用力,只是用魔息散了对方的伪装,并限制了些他的动作而已。她闭着眼转头面向那人,笑容不改:“什么时候?从一开始啊。”
从第一次撞上魂偶,她就一直在找这个做魂偶的人。
十二年,他终于自己跑到她面前来了。
令人惊喜,不是吗?
“你们对云罗有什么企图?”
那人看着雅沙闭合的眼,笑容轻蔑。
雅沙骤然收紧手指,微笑仍旧:“说。”
“你,你不过,是为了保护仙胎才被,咳,才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这,耍什么,威风!”那人被掐得呼吸不畅还要努力说出一些话,刚好手中刻画的一个符阵完成,立即往雅沙的额顶拍,“庶子雅沙,还不跪下!”
那符阵赤红,印上雅沙头顶后迅速展开成一张蛛网样的东西将她罩住。
雅沙慢慢松开了钳着那人咽喉的手,唇边的笑也逐渐落下。
那人挥开雅沙的手后跪在地上猛咳几下,然后站起来看着雅沙狞笑,右手成爪,渐收成拳。与他手上的动作同步,原本只是罩着雅沙的红网落到雅沙皮肤上,一经一纬地往里扎,最终全埋进她皮肤里。
周围魂偶的低叫声节奏突变,似乎紧张又兴奋。
被主人以咒役使的活物,会和它们变成一样的东西。
一样不伦不类不生不死卑贱如泥的可怜虫!
“呵。”
雅沙忽然又笑。
不愿意服从可以直接命令,吗?
于是她落到一半的右手忽然扬起,三段根茎从她脚底刺进那人心脏。同时草木灵们忽然被强制服从的惊泣声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细细梭梭,她只好再放出更多的魔息去安抚。
“你……怎么可能?”
那人瞪大眼,只看到雅沙嘴角上钩,然后又一只藤刺进他眉心,在他颅内生发出万千新芽。
红网还嵌在雅沙皮肤里,她却不管,依旧闭着眼面对远方。
“雅沙?这世上哪什么‘雅沙’。”
红网附着的地方终于变成裂痕,然后像是石壳绷裂,一片一片掉落在地又幻化成蝶翩飞远去。少女已经算是白皙的皮肤剥落之后,显露出来的则是雪一般的颜色。
“你们连我的名字都听不完全,如何能叫我跪下?”
她挥手让藤曼根茎将那人甩远。落进灵偶们的包围后,那人的尸体便成了它们的食物。
记忆尽失的可悲东西,也只知道吃了。
因承受不住她倏然外放魔息带出的冲力,用来绑发的那根麻布袋子已经断成了几节。她过腰的长发再披散开,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只不过新长出来的都是纯粹的白色。然后白色向下蔓延,追着黑色的部分一直到地上,蜿蜒两道,把杂色吞没。
远方忽然有炽烈的火光炸开,她微扬起脸,却还是不睁眼。
操偶师衣衫褴褛地从灵偶的包围中站起来,嘴上还叼着灵偶的半只“手”。他瞪着雅沙继续狠狠咀嚼嘴里的东西,满脸怒意地把离他最近的一只魂偶直接捏碎。
也没指望真能把他一击毙命。
她低下头,指尖聚了一点魔息打在眉心,把最后一层不遮相貌只封魔息的伪装也除去。
不知从何处凑来的菟丝子的根攀上了她的手杖,缠绕的线条松散,不过始终拉扯不断。在菟丝子之后到来的藤茎们一时没找到攀附之处,柔嫩的茎尖在菟丝子纤细的根附着的地方犹疑不前。它们如此天真的行为显然取悦了她,那苍白却水润的唇勾起了弧度,轻阖的双眼里也一样盈满了笑意。
她伸出了手,指尖划出优美至极的弧度,将它们接引到了手杖顶端。那双手上又褪下了一侧薄膜,最后露出来的颜色白得不可思议,似乎还带着一层微光。她的手指纤长,淡金色的甲盖上只有少量与金属相似的光泽,更多的是玉一般的温润。
她对着百余米外陆续转向她的灵偶们微微侧首,蚕丝一样柔软的白发滑过肩头:“真可怜。”
带着紫色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口中溢出来一声微弱的叹息。
“真可怜啊。”
焰心银紫的白色火焰贴着着生在纯白手杖上的根茎展开,转眼已笼罩住了整片森林。
火焰依旧无声无息,连温度也没有。魂偶们仍没有一只能够躲开,他们被连接到那柄手杖上的根和茎牢牢锁在了原地,只能在火焰里痛苦地扭曲,然后将曾经的执念化为模糊的言语,变成最后的哀嚎。
求而不得,得又复失。
更多的泪水从她眼里流出,滑过那依旧上扬的唇角,在落地之前散作点点荧光。
火焰将吞噬之物焚得一点不剩,然后乖乖地缩回到手杖中。那些根茎也是,陆续离开了手杖,一点痕迹也不敢留下。
背后忽然响起一声痛呼。
此时此地,只有她能听到的痛呼。
她半转过身,面对着因妄想偷袭她而被白色火焰缠住的灵偶,还是坚持闭着眼睛:“虽然你们多得了几分灵力,不过被这火焰沾上还是会疼的吧?”
那灵偶惨叫着远离了她,在回到同伴们中间前自己动手把沾上了火焰的右臂整个扯了下去。他们无血可流,因为本就五官模糊,所以也不可能从它的表情上看出来他有多痛。只是那饱含恨怨的目光如有实质,难以忽视。
她依旧在笑,右手握住手杖上端,和左手一起将手杖抬平。深浅不同的紫色纹路自她左手掌心生出,逐渐将手杖完全包裹住,然后又消散,露出一柄七尺长的纯白利剑。
“与其继续让你的这些可怜手下来消磨时光,还不如我们全力拼杀一场。”她持剑而立,慢慢睁开一双比水晶更冰冷透明的、莹紫色的眼,“您说是吧,亍候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