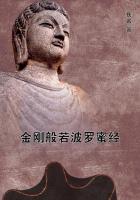乔治·伊利奥特(eorge Eliot)翻译的德国人戴维·弗莱德里克·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所著的《耶稣平生评考》的英译本于1846年出版,这是一本对相信《圣经》的人们所持的最根本信条提出严峻挑战的书。就在最保守的基督徒认为《圣经》正在遭到欧洲学者的围攻之际,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那些年的美国陷入内战,很容易被评论家丑化成不信教和亵渎上帝的达尔文进化论,也让美国的信徒们变得六神无主。
在达尔文新发现的挑战下,许多宗教信徒找了个变通的办法,他们认为上帝之道神秘莫测,坚信在物种形成过程中曾有过未知的阶段,就在这个阶段,上帝将灵魂赋予了他创造的生灵。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设法将他们的信仰和进化论的观点调和了起来。经验证明,宗教与科学之间没有必要互相对立、僵持不下;一代又一代的信徒都曾遇到过两者无法相容的难题,并且都设法解决了这些难题。在1973—1974年在爱丁堡大学举办的吉福特系列讲座上,历史学家欧文·查德维克(OwenChadwiek)对“十九世纪欧洲人心态去神化进程”作了猛烈抨击。在1901—1902年举办的这一系列讲座上,威廉·吉姆斯(williamJames)曾作过题为“宗教体验种种”的演讲。查德维克对达尔文主义的兴起对宗教的影响所作的评估是:这种思潮同样影响了美国人的宗教观。“让我们假设时光倒流,大约于1840年,我们这些人出生在一个每周去教堂,但又不特别信神的人家,一个受过教育,又不特别精通科学的人家,”查德维克说,“我们在母亲的膝盖上就知道《创世记》第一章里七天的说法是不能当真的,而且诺亚的洪水也不曾淹没整个地球……我们也许应该将亚当和夏娃想象成凯撒和凯尔普尼亚(Calpurnia)那样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应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和宗教信仰之间作选择。”查德维克当时详细解说的正是这个非常具有学术性的、虽然广泛流传但乃不失其精妙的观点。
但是,当时“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确在打拉锯战,在美国,这场拉锯战导致了1925年在田纳西的对顿(Dayton)举行的斯古帕斯(scopes)审判。这场论战仍在许多文化斗士心中继续,他们听不进当年奥格斯汀的劝诫:假如通过理性分析发现的新的真理与当时对《圣经》的解释不符,那么错的是人对《圣经》的解释,而不是被发现的真理。
“基督教国家”
对于公众人物(包括神职人员)来说,有时可能会很难抵御将政治和宗教混合起来的诱惑。在政界中的神职人员的角色总是很复杂的。
在独立战争之前,殖民地的民众就对英国国教的主教可能前来美洲定居忐忑不安;在十七世纪,“主教们掌握着极大的政治权力和神权,”历史学家埃德温·s·高斯台德(Edwin S.Gaustad)曾写道,“主教是政府的官员,手握重权的元老院成员,是政府迫害、压迫民众的工具”——即便到了十八世纪,“每每想到宗教官员在美利坚行使类似权力的可能性,殖民地的民众就会怒火中烧,这种情绪促使他们与英国决裂。”
在十九世纪,查尔斯·费利(charles Finney)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复兴主义者之一,他是一个极有魅力、永不疲倦的人。1821年,他在纽约州的亚当斯学院学习法律,据他的回忆,“有一次,神意降临到我身上,就像穿过我的肉体和灵魂。我能感受到那种特殊感觉,就像一股股电流,一次次地穿过我的身体。的确,那种感觉就好像一股又一股关爱的暖流……我就好像感受到了上帝的气息。”费利是我们现在称为基督复兴会的设计者,历史学家马克·A·诺尔认为,费利“将传教和社会改革成功地结合了起来”,从废奴运动到“减酒运动”到奥伯林学院首创的男女同校。费利说“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改造世界——消除各种罪恶”,而且他相信教徒“必须在制定一套反映上帝法律的人间法律方面施加影响”。
费利将教会的目标放在万事之首,连他本人的舒适也不例外。当他从纽约搬到奥伯林教授神学,诺尔写道,“他穷得不得不将‘我平时外出传教时随身携带的箱子卖掉’。”那又怎么样,费利说:“假如我没有得到帮助,”他写道,“我想最好就不要得到帮助。”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有名的传教士都像查尔斯·费利那般超脱,在二十世纪,曾有一个名叫比利·圣对(Billy Sunday)的深受欢迎的宗教复兴传教士。按照著名学者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的话说,他“认为基督徒的生活的内容要比仅仅遵守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正规条例更多,并且必须坚持按照英美新教教徒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行事做人。”圣对支持禁酒令,呼吁总统发放战争债券,以支持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击进步的改革运动是“毫无意义的、无视上帝的社会服务”。他在外交立场上也同样不含糊。他在谈到威廉二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我给你们挑明了说吧,这是比尔(他本人)与伍德罗(当时对介入“一战”有所犹豫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德国与美国、地狱与天堂之间的斗争。”圣对还说,“一战”的目的是“打败一伙嚼面圈、吃泡菜、嗜血成性的德国野蛮人”。查尔斯·考夫林是一个天主教神父,他通过定期的广播传教,在全美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1934年,《财富周刊》称他为“自有广播事业以来,收音机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考夫林的广播生涯是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起家的;在三十年代行将结束之际,他变成一个反犹极端分子,这个举动最终断送了他的广播生涯。另一个极端保守派杰拉尔德·B·温拉德也重蹈覆辙,他从反对学校教进化论,发展到在他的出版物《捍卫者》中大肆攻击犹太人。
考夫林和温拉德的结局,使得通过提倡政教分离的途径在肉体中寻求精神升华的洗礼派的传统显得更具吸引力。于是,一场运动便应运而生,不错,其中部分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洗礼派是受到迫害的少数派,如果他们能说服英国国教和信众会这些多数派在美国革命的年代不去干涉他们的内政,宗教迫害就会停止。约翰·里伦(John IMand)是一个积极宣扬麦迪生一杰弗逊观点的、口才出色的倡导者,另一个洗礼派艾萨克·贝克斯(Isaac Backus)也是,他在1779年写道:“真正的宗教只能指信徒自愿服从上帝的意愿,每一个理智的人都有同等的权利,自己判断什么是自己的上帝的意愿……”
涉及公众世俗生活的宗教事务是年复一年、永无休止的事。1875年秋,格兰特总统利用当时民众中的反天主教情绪,到德沫因去呼吁采取新的修宪措施,切断政府对天主教会学校的经济资助。“假如我们在近期内再就我们国家的生存发生一次冲突的话,我看,分界线将不是梅森一狄克森线(Mason—DixonLine),其分界线的一边将是爱国主义和知识,另一边则是迷信、野心和无知,”格兰特说,“我们要鼓励提倡免费学校,坚决不把资助免费学校的一个美元用在任何教会学校……让我们把宗教事务留给家庭的神坛、教堂和私立学校,完全由私人赞助维持。让我们将教会和政府永远分隔开来。”
当然,新教教会是个例外,在这一个问题上,它是理所应当地和公立学校混在一起的。当时很快将成为参议员、并有入主白宫野心的、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姆斯·G·布雷恩(James G.Blaine)采用了一个特别的立法手段,提议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条款作出以下修改:“任何州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也不得立法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州为资助公立学校所纳的税收,或来自任何公款的款项,或赞助公立学校的公有土地,永远不得由任何宗教教派控制。以这些目的筹集的款项和土地也不得由各个宗教教派和分支瓜分。”格兰特和布雷恩的提议均未成功——这又一次证明,在林肯时代,在民众中占大多数的中间势力认为共和制的政府架构足以应付执政的需要了。
足够多的美国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们听到的政教分离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迎合信奉新教的多数派的政治家打出的保护伞,但是这个新教多数派似乎又不愿意打乱开国先贤所定的框架。尽管如此,在那些保守势力的眼里,移民、神学地位和进化论这些问题,都是基督徒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将美国这个共和国变成他们在现代化风暴里保护基督教的安全港湾的关键因素。乔纳森·萨马引用长老会神父艾萨克·A·康米尼森(saac A.Coimelison)在十九世纪末说过的一句话,他称美国是“一个没有教会的国家,但不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说到这里,还算过得去,但是,康米尼森后面的话则超越了开国先贤及其立场温和的继承人所设的界线。“恰当地说,基督教是这个国家的国教;不错,这个地位不是由哪条法律条文确立的,而是被另一条同样有效的法则确立的,那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法则——一个出于需要而定的法则,只要广大民众还是基督徒,这条法则就仍然有效。”1892年,最高法院的每个法官无一例外地宣告:“[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发现同一条明确无误的真理……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老罗斯福上校的信条
但是,美国除了是一个自称信奉基督教的民众聚居的国家之外,从来就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怎样下定义是有区别的,一边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另一边是一个信奉公共宗教、可以使用各种宗教的信条(无论是否是基督教)来塑造行为和道德准则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有区别的——有根本性的区别。
公共宗教在得到恰当的理解和应用之后,可以成为一种正义的力量。在二十世纪开始时,它的确起到了这一作用。当时的美国正处在一个宗教改革的进步时代。从减酒运动到星期天休假法令,许多当时的进步运动得到了那些认为行善是基督教的一个关键因素的宗教改革派的支持。当时进步运动的领袖之一西尔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信仰与开国先贤相比更加正统:他相信行动和言语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他认为,“应该以他们的行动评价”一个人(引用了《圣经》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