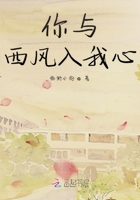然而,就在那个夏天,宗教和宗教自由通过两个具有实质性的途径得到了保护和发展。首先,1787年7月13日,星期五,政府颁发了《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为这个正在向西拓展的国家制定了政策。“在以上领地,任何遵纪守法,平和待人的个人,均不得因其信仰方式和宗教倾向受到骚扰。”法令说,并且在之后的条例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宗教、道德和知识是一个德政和民众福祉所必需的要素,所以,我们将永远提倡开办学校和各种教育机构。”
同时,宪法禁止将宗教信仰作为担任联邦官员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政府不得强迫公务员信奉某种宗教或任何信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争取宗教自由的过程中走出的一大步。康涅迭克州副州长奥立弗·沃考特(Oliver Wolcott)感叹:“知识和自由在这个国家是如此根深蒂固,我相信合众国永远不会堕落到一教独专、百教俱废的地步。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而任何这一类的冒险,对于自由民众的权利的危害都是极大的。所以,我认为加一条保证我们不受这种可能压迫的条款不完全是多此一举。”
本杰明·拉希在制宪大会之后的一次演说中,再一次提及公共宗教。他说他相信“上帝在制宪过程中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就像当年为以色列人在红海中开道”或“将‘十诫’送到西奈山上!”(有一些人,可能是和那些不响应富兰克林祈祷倡议的人们属于同一阵营的人,认为拉希在宗教问题上走得太远,对以上的那段话提出批评,但是,拉希的言论没有超越当时已经建立了很久的传统界限。)
分而治之
宪法草案出台后,被送往一个多元化国家的各个地方征求核准。
“他们是一群由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组成的大杂烩,”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写道,“就是从这个大杂烩中,诞生了一个现在被称为美国人的新种族。”克雷夫科尔在描述美国人的宗教习惯时,看到了麦迪生在纸上提出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现。天主教徒、路德教徒、自然神论者、卡文主义者和教友会教友同住在一个区域。这样,所有属于不同教派、所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混合在一起;“这样,从北美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宗教门派观念的淡漠,就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开来,这是当今最明显的美国人的特征之一。”克雷夫科尔写道。
然而,他所说的“淡漠”,还可以理解为那些一心要在这片大陆上扎根的各色人等中间的互相包容和尊重。“对持异见者的迫害、自高自大的宗教感、对门派之争的津津乐道,这些都是世人所知道的传统宗教所具有的不可缺少的成分,”克雷夫科尔写道,“这些因素在这里已不复存在;在欧洲,宗教狂热被控制了起来,而在这里,这些狂热在万里之行之后,早已烟消云散;在欧洲,火药被包了起来,而在这里,在敞开的空气里,那火药已被燃烧殆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杰姆斯·麦迪生所依靠的正是这一点。在1787年11月22日出版的《联邦党人》第十期中,他对一个民主体制和一个共和体制这两个概念作了重要的区分——这一区分将用来保护被美国人看成是美国民主标志的那些权利和自由。在一个共和体制中,政府的职能是由散布在广大地域里的民众推选的代表代理行使的。麦迪生写道,这两个特征——代理权力和地域的幅员——最有可能在限制一时冲动和监控特殊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取得成效。麦迪生认为,美国宪法为解决像美国这样一个仍在发展的国家可能碰到的大多数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和制补充方案”。从而形成了参议院与众议院之间、总统与参众两院之间、司法分支与立法及行政这些分支之间、各州与联邦政府机构之间互相制衡的格局。
在麦迪生为自己提出的限制少数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全国百姓头上的权力的主张提供论据时,首先转向他知道他的读者最关心的一件事:宗教。“某个教派可能会堕落成联合政体中的某个政治派别,”麦迪生写道,“但是,如果许多教派散布于这个联合政体的全部体系之中,那就能够防止一派独大的危险。”麦迪生这里是说,各派利益的多样性,以及各派之间的监督和制衡,能防止某一极端派别的利益压倒公众利益的做法。这就是共和体制的天才创造之所在。尽管任何一个派别或党派(或教会)可以就一个问题喋喋不休,在它还没有让不同州、不同级别政府里的许许多多的人看它的高明之处之前,还是要受到宪法的限制,使它无法独断专权。用麦迪生的想象来比喻,在联邦中的一处烧起的野火,如果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就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难以控制的燎原之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广大民众的意愿,野火就不成其为野火。
麦迪生以宗教作为引子展开了这场讨论,然后很快谈及其他问题。
“使用纸币的狂热、强行取消以往债务、平均分配财产或者其他离奇荒诞的政策可以搞坏联邦的一部分,但不那么容易侵蚀整个联邦;以同样的道理按比例推论,这样的弊政可能只能影响某个郡或专区,而不是整个州。”这是一个对人性和政治的精辟论断。不过,宗教依然是麦迪生最担心的一项,他在1787年10月给杰弗逊的信中说:“当宗教被激发成热情,那种能量,就像其他的激情一样,会被民众的同情心激发起来。但是,热情只是宗教的一个暂时状态,时间久了,就连掌权的人也会不喜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麦迪生和美国,需要的正是克雷夫科尔观察到的现象:教派越多,某个教派在政治中施加过多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小。“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la),这个****独裁者的邪恶信条,”麦迪生在信中继续写道,“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依据公正原则掌管一个共和国的唯一可行的国策。”宗教的利益和其他的利益集团一样,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尊重它,但又不偏向它。“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根本不需要政府了。”麦迪生在1788年2月6日第五十一期《联邦党人》中写道:“假如人心都像天使,所有外在的和内在的政府监控机制就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事实上,不论是人,还是政府,从本质上讲,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一个共和体制,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对冲破人世间的阴暗面和野心、走向正义的社会制度来说是必要的。
“政府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人类的公正,”麦迪生说,“那是一个民治社会的最高理想。”
宪法草案在各州核准过程中的气氛既极具戏剧性,又极其严肃。
那些决定是否接受费城宪法文本的人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细心权衡之后才作出决定的。其间自然不乏党派之争和报章上的激烈争论——《联邦党人文汇》是一系列支持宪法草案的报刊专栏文章的汇编——但就整体而言,争议是在善意和宽容的气氛中进行的。“送交你们核准的宪法草案不是仅仅为你们写的,而且是为那些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写的。”托马斯·格林里夫(Thomas Greenleaf)以“Butus”的笔名,在1787年11月1日的《纽约杂志》中这样写道。l788年1月9日,《马萨诸塞卫报》在谈到即将举行的州议会投票表决时,发出一个既具宗教性又具爱国性的呼吁:“愿这个团体的每一个成员在投票时,都能怀有上帝在这一吉祥的日子里惠顾美利坚的信念……”
就连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在表示疑义时也表现出良好愿望和实用的观点。“至于这是否就是一个建立政府的最佳方案,我不敢说,”弗朗西斯·霍普金森在1788年7月给杰弗逊的一封信中说,“时间肯定会作出结论;但是,我已被别人说服了,如果没有一个卓有成效的联邦政府,不用过多久,各州就会陷入耻辱和最危险的混乱。”一个名叫本杰明·盖尔(Benjamin Gale)的反联邦分子称宪法“是富有创意、阴晦、神秘、复杂和昂贵的一种政府形式”。但他认为宪法会被核准,但要控制总统权限将需要“流血”。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宪法值得一试。“有些人将其吹捧成一部出自神意的文本,另外有些人则不以为然,将其归结为老恶魔的阴谋,”古弗米尔·摩利斯在1788年2月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是一部出自一些诚实的人们之手的作品,我认为别人也会看到那是明摆的事。谬误自然难免,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物呢?”
对含有基督教义的公职就职誓词的反对
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乐观。有些教徒们担心这份文件太过世俗。
在康涅迭克州,元老人物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认为宪法前言应该重写,以强调美国对上帝的依赖,并提议用以下的段落:
我们这些合众国的民众,怀着对世间万物的创造者、世间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唯一的、真正的上帝的存在和完美以及对他无边的神力和他的法则的权威的坚定信仰,也就是:他要求所有具有道德良心的凡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有人间的正义力量,都是神意所归,均属神意使然,因此,我们仰仗他的祝福和承蒙他的保佑,实现了独立,就独立而言,我们各州有必要认同和制定一部联邦政府宪法,同时,为了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正如本引言所述,特规定……
威廉姆斯认为,政府官员应该强制性地认同这段话,这样,就等于建立了一个有意执政者必须通过的宗教测试。威廉姆斯的观点受到1787年12月17日,星期一的《康涅迭克酸果报》上署名“土地拥有者”
的奥立弗·埃斯沃兹(Oliver Ellsworth)的猛烈抨击。他反驳说,要强迫一个文职和军职官员信教或去教堂就是剥夺他的权利。“在合众国,任何一个偏向某个基督教教派的测试都是最最荒诞不经的,”埃斯沃兹写道,“如果这个测试偏向信众会、长老会、英国国教、洗礼派、或教友会中的任何一个,这就意味着多于四分之三的美国公民无法担任任何公职……”
威廉·威廉姆斯认为“有关联邦宪法的讨论本来一直是一件非常冷静、不感情用事、合乎情理和皆大欢喜的事”,他称,读了埃斯沃兹的批评后,他感到意外。他在1788年2月11日,星期一出版的《美国信使报》上著文,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文中,他回忆在州制宪大会上的情景。威廉姆斯说,假如一个人不能宣誓皈依基督教,那么他就不应该在政府中任职。他称,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修正过的前言“成为伟大民众的心声,同时,恰当地承认神意通过这些民众,在这一伟大、前所未有的场合得到表现,此外,按照神意的规律,这一场合得到了至高无上的神的保佑”。在州制宪大会上,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孤立无助的立场。在发现“要加这一段是那么困难和难以预测”后,威廉姆斯说,他放弃他对宪法文本的反对意见。“我认为为此作证是我的责任,我也的确为上帝作了见证”,他写道,为自己在联邦官员具有基督教意义的就职誓词上的立场辩解,是在核准宪法的辩论中应该提出的话题。在结尾时,威廉姆斯说他将不再回应诸如“土地拥有者”之类使用化名发表的文章。
然而,即使到了这份儿上,威廉姆斯的对手还没过完瘾。他们在围攻时的口气几乎称得上得意洋洋。一星期之后,一个化名“伊拉胡”(“Elihu”)的人,抓住威廉姆斯有关宪法应该对上帝“恰当地承认”的观点作了文章。“一个俗人可能会将上帝想象成一个昏聩老朽,他会因为在宪法的前言中没有得到承认,或得到一席尊位而感到被冷落和失敬。但是那些起草这部宪法的伟大哲人们,不认为他们这些凡人能为这个统管宇宙的主宰增添荣誉和光彩,也不认为上帝会为这种低级的吹捧而自得,他们对主的完美有着更高的崇敬。”
“伊拉胡”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证。“起草宪法的人们取得的最辉煌的那一部分和最精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没有留下精雕细刻的痕迹,他们。不去用迷信来暗示超自然的影响,以哗众取宠,”他说,“我们面前的宪法通情达理、浅显易懂,让我们懂得一个政府的结构仅仅是人类智慧孕育的发明;没有哪个神明下凡传授其中的奥秘,就连上帝也没有托梦提议怎样写其中的某一章节。”按照《独立宣言》,所有的权力都是通过一个来自上帝的宪政体制的创立受到保护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制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以信仰为动力的过程。
还有人说宗教自由对民主政体和商业发展均有好处。坦曲·卡克斯著文向宾夕法尼亚西部诸郡的民众担保,政教双方在自由的空气中,各自都会兴旺发达——自由将导致经济发展。“毫无疑问,美利坚在所有教派和团体中建立的完全平等和自由这一过程中表现的解放性和美德,将结出一个硕果。因为当这一喜讯传到备受主流教会压迫的英国、爱尔兰、荷兰、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民众耳中,将会大大鼓舞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会立刻高呼,美利坚是一个‘希望理想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