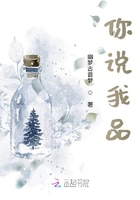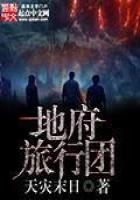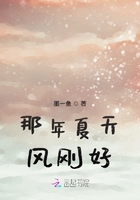周健林感激涕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又听田元璋说道:“孙秘书,你把当年周先生在东海大学的毕业论文取来。”
“我拜读了周先生六年前毕业论文的大作,拜读完毕,十分敬佩。”田元璋露出满足的笑容,又开言道:“足下才高八斗,诗韵高雅,确是难得的英才呀!”
“哎!哪里,哪里,田书记过奖了。我不是什么八斗,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论文,更谈不上风雅,倒不如拿来烧了更好。”
“啊?周先生为何如此说话?”
“如今,天下正处多事之秋,正是有为之士建功立业之时,我却搞酸溜溜的那一套。实在不合适宜。唉,惭愧呀!”
“嗯!你如此见高识远,更令人钦佩。只是,我不明白当年你有进身仕途的路径,怎么就没有走下去呢?”田元璋有些不解地说道。
孙富才把论文答卷取来,田元璋将卷纸展开,微笑着又看一眼,说道:“这是六年前你在东海大学毕业应试的论文《论经济与法》。不但文笔雄劲,气势磅礴,而且立论精辟,有理有据,谋国深远,陈述治国要略,精深之至,实在是不可多得之佳作。如果天下的有为之士都能像你这样,我们东海何愁不发展,国家何愁不日益昌盛。”
周健林知道为了这份策卷,当年来惹出了多少大事,自己当初又是如何在时势和学校之间左右摇摆,他不知道田书记为什么要拿出当年自己一时书生意气写出的文章。
“听说周先生当年在东海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田元璋精神矍铄地说道。
“是的,这毕业都快有六七年了。”
“那我们还是老同学。那你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学下去,反而出国留学选了一个不相关的行业。”
“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田元璋微笑着,看着周健林,爱才之心溢于言表,说:“健林啊,我听说早年在东海大学是学经济学的,你对东海经济发展分析的精辟透彻,但中国的国情复杂,想要实施下来可有些难点啊!”
周健林道:“为官者之命系于民命,相比起来,还是民命重的。谁在老百姓心中有了威望,那官位便稳了;谁失了民心,凭你天子皇上,也是兔尾难长!”
孙富才听了脸上不禁变色。他转过脸朝田书记看看,见他专心致志地听讲,并无厌色,便放下心来。
“其三便是吏治。国政清明,方能使民以国为家,愿效死力保家卫国。此乃千古常理,断无二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国家初步富强,外患虽说没有,但是内政还是堪忧。官员执法有所懈怠,权贵阶层守法已不甚严谨,官场中已隐隐然有怠惰荒疏阿谀逢迎之风。奋发惕厉、法制严明之气象已经有所浸蚀。田书记定深知吏治积弊乃国家大危祸根。一国为治,绝无一劳永逸之先例,须得各个部门各个阶层保持清明,方可累积强大国力。刷新吏治,振奋民心,使东海实力更上层楼,则东海大有可为也。一直以来,在中国官场都流传着这样一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可以说这是很多腐败奉行的经典名言,也是很多腐败分子在位期间执政的方式,结果引起地方民众的强烈反感,因为一直以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官腐民变,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一个地方的执政者如果贪得无厌,那么,一些投机钻营份子便有机可乘,他们用行贿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给社会带来许多不良的风气,久而久之,便成了玩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