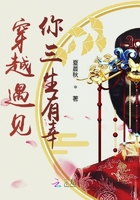那女子看到来人,却是忽然收了脚,转而弯腰去捡地上的匕首。青狼寨主觉着自己总算捡回一条命,忍不住咳嗽了起来,甚至还能感觉到口腔中的些许血腥。
不过刚刚歇息片刻,那华服男子骤然上前,右手卡主他的喉咙道:“你将人掠到了何处!”
青狼寨主刚要挣扎,便听“咔嚓”一声,却是痛得合不拢嘴。
但见他的侍从蹲在身侧,惋惜道:“殿下,他下巴掉了。”
青狼寨主痛得冷汗直流,下颌无论如何也合不上,唯有口水愈发肆无忌惮地自嘴角落下。
华服男子骂了一句“恶心”,而后道:“沈通,替他接上。”
沈通不由自主地在衣衫上蹭了蹭手,面对着虬须大汉一般的青狼寨主,仍然觉着下不了手。正在犹豫之间,但见那黑衣的女子扯了半片衣襟下来,一只手捏其下巴,一只手扶其后脑,“啪”地一声将下颌复原。
青狼寨主连忙擦了擦口水,道了一声:“多谢女侠。”
女侠却并不领他的情,即刻以匕首抵了他咽喉道:“说!”
青狼寨主只得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方知这两方的人皆是为昨日的小白脸而来。且不说那什么殿下只带了些许官兵,女侠也只有不足十人随行。区区三十余人,竟是自山下一路冲将而上,视青狼寨百余弟兄为无物。
燕榕端坐在青狼寨主的虎皮椅上,一字不差地听他陈述。依此人所言,似是还有另外一行人也在此处截了林馥的去路,那些人武艺高强,却又不是普通山匪,究竟是什么人?
蒙了脸的黑衣女子始终未曾揭面,只是双手抱在胸前一语不发,从她紧锁的眉头来看,亦是挂念林馥的安危。她听了许久,却是向庆安王殿下抱拳道:“既是我要寻的人不在此处,这便先行一步了。”
燕榕亦是抱拳道:“后会有期。”
青狼寨主忍不住回头去看,他甚至没看清楚小美人长什么样,她竟然走了!
死到临头,这汉子还是一脸痴傻的好色模样,教沈通也觉着不可理喻,他忽然咳嗽了一声,吓得青狼寨主连忙回头。
“你再说一遍事发经过。”庆安王又道。
一行人离开青狼岭已是深夜,庆安王再次提了行军速度,必须于天亮前赶往宁仓府。沈通知晓殿下自幼锦衣玉食,饮食穿着也十分挑剔,今日却是如强盗般抢了劫匪的口粮,没吃上一口热食便策马上路。
沈通连忙跟上,“殿下,既是太傅未曾遇险,我们要去何处寻她?”
庆安王沉声道:“宁仓府。”
“明知此行路上艰辛,太傅仍旧会往宁仓府方向去?”沈通不解。
“她要做的事,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无人拦得住。”庆安王又道。
沈通觉着殿下说得在理,不由夹紧马腹,猛地抽了马儿两鞭。
且说昨天入夜时分,宁仓府府库官安国栋正在酣然睡梦之中,忽有士卒扰了他的清梦,禀报宣抚使大人深夜入城。安国栋当即斥责那士卒道:“胡说八道,哪里来得宣抚使!”
说罢却忆起近日之京中传书,说太傅被贬谪为宁仓府宣抚使,奉旨巡查宁仓府及宁远城战事。那宣抚使大人原先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也不知犯下了什么过错暂时被贬到这穷乡僻壤。安国栋不敢怠慢,连忙披了衣衫戴了冠,急急忙忙地出城迎接。
二人刚一见面,安国栋不由暗自腹诽。宣抚使大人果如传说中一般容貌过人,可是精巧的一张脸尽是污泥,头发凌乱衣衫褴褛,甚至没有乘车而来,反是率众骑马——可那马也不是战马,杂色相间、高矮不一,莫不是在农户家偷来的?
安国栋这般揣测,却也不敢说出来,更是不确定这位宣抚使的真假,只得讪讪道:“大人可曾携了吏部的调遣函及印信?”
宣抚使大人听罢,却是从怀中取出了皱巴巴的调任令,勉强辨别得出吏部盖章。宣抚使本人的官印竟已摔烂了一角,她却是大大方方地举到他面前,“林馥。”
“我于青狼岭遇寇匪劫掠,而后又遇悍匪追杀,故而弃了车马。”林馥大步上前,“近日边关可曾有异动?”
安国栋摇头道:“今日观测到遥城方向狼烟四起,许是夷人已在滋扰边境。”
“边境?”林馥蹙眉道:“遥城乃是边防小城,蛮夷以往滋扰的乃是百姓聚居的宁远城,今年怎会改了方向?”
安国栋又哪里知道蛮夷的动向,许是往年数次滋扰不成,知道以卵击石不可取,今年改了策略。
“若想进入遥城,必先至宁远城,可宁远城并无战事,除非宁远、遥城之间的岭山城有变,致使辅国将军首尾不能相顾。”林馥忽而专向身旁之人,“沈全,你速去宁远城。”
沈全得了指令,更是顾不得休息,连夜往宁远城而去。
安国栋不知宣抚使为何这般紧张,却听她又道:“安大人请随我出城。”
安国栋原本还想睡个懒觉,只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既是宣抚使要求他提起精神,他自然不敢怠慢。只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宣抚使所说,南夷军队自遥城入境,欲偷袭宁仓府一事。遥城对面乃是千年不化的皑皑雪山,平日里罕有人烟,夷人怎么可能直攻遥城?
林馥此行随从不过寥寥几人,待她出了城楼远远望去,但见宁仓府地势颇高,易守难攻,并无许多高大树木,却是有山坳可以伏击。居高临下,既不怕对方埋伏,亦没有火攻偷袭的可能性。
但见宣抚使忽然蹲身伏于地上,以右耳轻轻贴近地面,然后缓缓道:“步军为主,至少五百人疾行而来,距此处约八里地,半个时辰将至。”
安国栋从来没有觉着似今日般如临大敌,他乃是文臣出身,并不知宣抚使的判断从何而来,只是学着她的模样伏在地上,亦是贴了右耳过去。
“轰隆”、“轰隆”,虽说是疾行,也没有丝毫步伐紊乱的迹象。安国栋立即起身道:“宁仓府尚有一千守军,此处视野开阔易守难攻,况且我军粮草充沛,守上数月不成问题。”
林馥反是摇头,南夷都打到家门口来了,粮多兵广的情况下竟然还要坚守不出,是何道理。
“大人借三百士卒与我,我去伏击敌军。”林馥道。
安国栋记忆之中,林馥似乎是永兴三年的进士科一甲状元,竟然还精通行兵作战?
“大人乃是陛下亲封的宣抚使,怎能以身涉险,前去迎敌?”安国栋道:“况且敌军不明,三百军士也不知够不够。”
林馥等的便是他这句话,“不如大人再借我两百?”
安国栋的眼睛瞪得老大,他一个宁仓府守城将,被一个衣衫褴褛的文臣借了一半兵力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