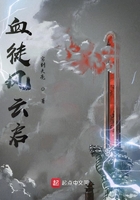“许久不见,几位别来无恙?”
不知何时,吴起的目光早已投落在了三人身上。他的眼神空淡到了极点,宛如寒潭般深不可测,没有丝毫情绪起伏含在其中。他就这么静静地注视着昔日的三位故人,幽幽的火光中有一丝淡漠的疏离感。
云樗和桑柔方才还讨论得起劲,听闻吴起熟悉的声音,心下皆是一惊。
“三位老朋友既然来了,又为何急着要离开呢?何不坐下来喝杯酒,陪吴某人叙叙旧?”他的语气跟他的眼神一样,没有丝毫起伏变化,更没有久别重逢后的喜悦,从头到尾都只有一种调,一种疏离淡漠乃至冰冷的调。
长鱼酒瞬间懵了。
他曾无数次想象再遇到吴起时,他的脸上将会是怎样一副表情——是讶异,还是开怀大笑,抑或是唏嘘感叹?或许他们会席地坐下喝一杯,或是上城里最大的窑子里去喝一杯,或是……他却独独想不到会是今日这般光景。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也许你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就已经猝不及防落入了他人制定的计划中。
吴起看着他们三人的眼神,就好像是在看三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语气到眼神都充满了疏离与淡漠,仿佛他们从未共同经历过生死的风雨,仿佛他们从未一起并肩作战过,仿佛他们不曾在禹王城的酒楼里喝得酣畅淋漓、畅谈各自的志向,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梦境,醒来时依旧两手空空。
长鱼酒不明白。感情这东西,为什么说淡就淡?它最初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是那么得坎坷、艰辛,那么得小心翼翼,可变质起来为何如山庄塌陷般干脆迅速?或许对于吴起这种人而言,感情根本就是块随意可以丢掉的破布,一旦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利用价值,就必须立刻舍弃。或许他从未了解过吴起这人……
“托大人的福,一切安好。”长鱼酒模仿大胡子的话,以一种近乎嘲讽的口吻淡淡答道。
他不是那种会用热脸贴别人冷屁股的人,吴起用这种疏离淡漠的态度待他,他自然不会予以热情回应。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奇妙,你不说我便也不问,你对我冷淡我必定要对你更冷淡,不然好像是我占了下风、吃了大亏,而感情便是以这种莫名的方式,逐渐变冷变淡乃至最终消失殆尽。
“听说你们把慎到的寻剑山庄给毁了。不但毁了山庄,还毁了他的剑,毁了山庄里的所有人。”吴起的语气依旧淡淡的,透着一种疏离甚至冰冷的敌意。他用了陈述句,说明他对三人的行踪根本了若指掌。
“是。我们毁了慎到的寻剑山庄。不仅毁了山庄,还毁了他的剑,毁了山庄里的所有人。”长鱼酒并不否认。
吴起的脸上不仅没有分毫哀恸之色,反而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嘲讽,这让长鱼酒看更不明白了。不管怎么说,吴起与慎到同出法家,又都是申不害座下得力使臣,两人多少也该有些交情吧。可是听吴起提到慎到时的语气,就好像他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更别谈什么同门之谊了。
室内的幽幽火光描摹出他冷硬的下巴线条,一双幽深不见底的双眸中似有火苗跳动,狭长眉目连成一条微微弯曲的弧线。他的冷酷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商人们终于将全部货品卸了下来,但他们并不急着离去,而是恭敬地候立在一旁,等待吴起进一步差遣指示。
吴起讽刺地勾唇一笑,道:“她不过是个想要寻求你们帮助的可怜女人,可你们却杀了她。”
这句话,也是陈述句。看来长鱼酒三人在寻剑山庄的一切行踪,经历的一切事情,这位丞相大人都早已了若指掌。
云樗想要开口反驳,被长鱼酒制止了。
“她要行不义之举,我等自然有权利拒绝帮助她。”长鱼酒朗声道。
“不义之举?”吴起饶有兴致地眯起双眼,冰冷的语气微微上扬,“这个词很新鲜。什么是不义之举呢?”
“她妄图谋害丈夫慎到,篡夺寻剑山庄庄主之位,将上古名剑占为己有,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心肠歹毒,是为不义之举。”长鱼酒沉声道。
“哦,原来如此。”吴起假模假式地点了点头,仿佛幡然醒悟过来一般,目光中流露出一种虚伪的了然。
“可我现在,刚好也想请你们帮一个忙呢。”他锐利如鹰隼的目光在三人身上逐次扫过,然后严肃地点头道,“不错,是你们。”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可愿意帮我这个忙?”虽是在乞求别人的帮助,可吴起言谈间却连丝毫乞求的语气都没有,甚至不带任何商量的口吻,反而有种自上而下的压迫感,压得长鱼酒三人喘不过气来。
“丞相大人有求于我等,我等岂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尽管气势上受到压制,但长鱼酒依旧保持从容镇定,“不过,这要取决于你想请我们帮你做什么。若是又要我们行些不义之举来替你铺路,我们一定会拒绝你,就像拒绝玉麒郡主那样,拒绝你。”他的语气渐渐有了冷酷的杀意。
“像拒绝玉麒麟那样,拒绝我?”吴起嗤笑一声,道,“怎么,难道你想杀了我?”
“为什么不?”长鱼酒反问道。
吴起叹了口气,似乎觉得很惋惜。
“哎……我又岂会让你们去行些不义之举呢?不不,那太无趣了,一点也没意思,一点也不好玩……”
他摇了摇头,轻笑一声,掷地有声的话语在寂静密室中响起,“我要你们行的,是逆天之举。”
长鱼酒三人瞬间愣住。就好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冰冷寒意从头顶一直窜到心间,于是心也凉了半截。
“逆……逆天之举?”云樗喃喃道。
长鱼酒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快走!”他拽起云樗和桑柔,转身就跑。
吴起依然在笑,目光里带了几分轻蔑讥诮。那是他一贯的笑,一贯的目光。
“你们现在才想到要离开,已经来不及了。不过既然来了,不如就帮帮你们的老朋友呗,何乐而不为?”他淡淡的语气,没有一丝一毫的起伏,冰冷无情。
不管是离开这间昏暗的密室,还是离开这座昏暗的城,都已经成为不可能。自打他们踏入郢都城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注定要被卷进这场政治旋涡之中,注定无法明哲保身,注定无法置身事外。事到如今,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
吴起没有动。
他沉默地伫立在原地,看长鱼酒三人做最后的无意义抗争,那眼神,就仿佛在俯瞰一群渺小的蝼蚁。
就在那一瞬间,长鱼酒三人同时觉得脚底一软,一种说不出的酸麻奇异的力量陡然自他们体内升腾而起,于五脏六腑间疯狂流窜涌动,所经之处穴位尽数被封锁,经脉好似被冻住了一般,僵硬无比,举步维艰。
桑柔惊呼一声,踉跄着摔倒在地上。
“这,这是怎么回事?”云樗又惊又怒,却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不断失去知觉和意识。
“你……”他挣扎着抬起手臂,指着吴起大声责问道,“你,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却一点点也不设防,就连自己什么时候中了毒都不知道,真可笑。”
吴起轻蔑的声音在密室里响起,那嘲讽的口气宛如一盆冷水,无情浇在三人心头上,让人全身发寒。
“我想你们应该早就知晓我的真实身份了。”吴起道,“我乃法家献玉使者,七十二使臣位列第二。还有,申不害在追杀你。”他将目光投向长鱼酒,显然最后那句话是对他说的。
长鱼酒也在淡淡地注视着吴起,注视着他那一双眼睛。那双深如寒潭的双眸,冰冷得再也寻不到一丝昔日的情谊,有的只是疏离冷漠与讥诮。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吴起——冷漠,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玩弄他人的感情。
吴起轻笑一声,接着道:“那你想必也该知道,我是听命于他的。”
长鱼酒此刻几乎已经虚弱得说不动话了,但他仍然拼着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着开口道:“是,我知道。”他的语气出奇地镇定,听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中毒的人。
“那你也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吴起说的很简单,但长鱼酒当然能够理解他在说些什么,当然也理解他在做些什么了。
“你……你无耻!”云樗骂道,“枉我们一直把你当朋友看,你竟然这般作践我们的感情。你这个出卖朋友的可耻叛徒,注定不得好死!”
“都是快死的人了,居然还跟我谈感情,你这小神仙,还真是有趣儿!”吴起骤然仰天大笑,似乎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大概感情对于他而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罢,原本就可以轻易地舍弃。
吴起大笑着,又将目光投向了长鱼酒,“俱酒,你现在知道,你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大宗师是谁了么?即便不知道,我想你心里大致还是有些眉目的吧。”
长鱼酒心下陡然一惊。
那个最为敏感,他最不愿意去触及的话题,终于还是被吴起提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