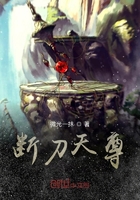下面该轮到李大嘴了,他对着李朝阳冷笑了一下,捡起铺子上的那三颗骰子,随手一甩,骰子竟然甩出三个“六”来。
又输了,李朝阳失望的摇了摇头,一脸的晦气。他从身底下数了十个铜钱扔给李大嘴,然后坐在那里唉声叹气。
李大嘴侧过脸对着黄文焕得意的笑了下,然后继续开赌。
没有人发现异常,赌局照常进行。唯独站在李大嘴身后的黄文焕看出了端详,他看到李大嘴在抓骰子的时候,手背挡住了别人的视线,手心里把那三个“六”排在最上面。随后用手朝一个方向用劲一撒,骰子在空中只是在侧面旋转,落地后并没有翻滚,那三个“六”还是在最上面。
他当时差一点就喊了声来,李大嘴真是作孽啊,他竟然在骗自己同屋伙伴们的血汗钱。
黄文焕觉得难以置信,李大嘴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也太卑鄙了。在座的诸位,家里哪一个不是家徒四壁,家里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又有哪一个不是嗷嗷待哺,他们就等这银子拿回家了。要是把他们的钱都给骗走了,那他们回去怎么向家里面交代啊。
他开始感到不安起来,本来想站出来拆穿他的,但是他一想起李大嘴以前对他种种的好,又开始犹豫了。
黄文焕刚到这里的时候,举目无亲,和他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就是李大嘴。当时黄文焕的铺子底下没有稻草,是李大嘴主动发动屋里面的人,每人从自己铺子底下抽出一份稻草匀给他的。后来过了几天他又生病了,又是李大嘴和吴二柱两人轮流背着他,走了七八里的路把他送到了涟州城里,并给他垫付了药费。为此他一直对李大嘴和吴二柱二人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再加上前不久李大嘴刚刚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实在是不忍心当众揭发他。
但是要是这样听之任之,他心里又觉得实在对不起在座的各位兄弟,他现在感到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
赌局还在继续进行着,黄文焕站在李大嘴的身后一直在看,他渐渐的发现李大嘴也不是次次都在作弊,他只针对李朝阳一个人,只要李朝阳撒出的点子一大,他肯定会甩出更大的点子吃掉他,看来他是故意在整李朝阳。
李朝阳和李大嘴两人素来不睦,这点黄文焕是很清楚的。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像冷水进了油锅里一样吵个不停。李朝阳这人的嘴比较阴毒,总喜欢对李大嘴冷言冷语。为此,李大嘴对他很是不满意,他曾经对自己说过,以后有机会要好好的教训他一下。
现在的李朝阳已经赌红了眼,压上去的铜钱也越来越多,他现在已经开始失态了,眼睛老是盯着自己身下的那些铜钱,就希望马上能翻本回来。
黄文焕担心的看着他,他很想劝告他叫他不要再继续赌下去了。但是张了张口,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了。他知道即使自己说了李朝阳也不会听的,他现在一门心思的就想着把自己输掉的钱再赢回来。
黄文焕看不下去了,他决定离开这里到涟州城里去,身上这些银子既然吴二柱不肯要,那他就把它存到“信泰来”银号里,免得和他们一样白白的给糟蹋掉了。
一想起“信泰来”银号,黄文焕心里忽然涌出一种异样的感觉来,他忽然想起昨天救他的那个姑娘,他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她看他的那种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欣赏?敬佩?好感?还有……他忽然觉得自己一心想去“信泰来”那里并不是真正要去存钱,而是只想找个见她一下的借口而已。
他拉开破烂的屋门走了出去,出了门,远远的他就望见吴二柱仍旧坐在那块礁石上一动不动,几只在海里捕食的海鸥,不停的在他头顶上盘旋鸣叫着。
要是这样能让他好受点,那就让他这样吧。黄文焕叹了一口气,他不打算再打扰他了,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调头就离开了。
涟州城内还是老样子,和昨天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天气虽然不好,街上的行人还是很多,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没人记得昨天在“信泰来”门口那个被打得小伙子。
黄文焕沿着街道慢慢的往前晃,边走边看着街道两边的铺面。身上的上虽然还感到隐隐作痛,但大体已经无碍了,估计过个两三天就没事了。
街道两旁,各色各样的商品让他目不暇接,他东看西看的瞧个不停,反正今天时间宽裕的很,他有的是功夫闲逛。
经过一家酒肆的时候,他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叫他:“文焕老弟,文焕老弟……”
他转回头去,却看见曾三从那间酒肆里出来,正站在门口在向他招手叫他过去。
怎么会是他,他喊自己干什么?黄文焕皱了皱眉头,心里充满了疑惑。他并没有走过去,而是微微朝他点了点头,然后站在原地客气的对着他打了声招呼:“曾三哥,今天不用在铺子里帮忙啊?”
黄文焕对曾三这个人接触不多,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次见到他就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他总觉得这个人心眼挺多的,因为他发现在他看人的时候,眼睛总喜欢滴溜溜的乱转。
曾三见黄文焕没有过来,便自己走了过去。他脸上带着笑,摇了摇头对着黄文焕说道:“没有,铺子里面活不多,余掌柜正好又不在,我就抽空溜出来了。难得有个半日空闲,我也找个机会让自己休息休息啊。”
黄文焕本想和他打声招呼就走的,见他走过来了,便不好意思不理他了,他只好站在原地陪着他说话。
“文焕老弟这是要到哪里去啊?”曾三望着黄文焕问。
“哦,我这是准备到‘信泰来’那里去一趟。”黄文焕没有瞒他,和他实话实说。
曾三的眼睛亮了下,他当然知道黄文焕从余掌柜那里刚得了十两银子。他实际上找黄文焕的目的就是问他借钱来的。他刚刚在酒肆里输光了银子,正准备要回去,正好看到了黄文焕,便盘算着问他借点银子回去翻本。
他关切的问黄文焕道:“文焕老弟这是去存银子还是去取银子啊?”
“我是去存银子,银子在身上摆着不放心,我想把它存在那里放着,还能拿点利钱。”黄文焕随口对他答道。
“哈哈哈哈,文焕老弟你真是有趣,你是做大生意的人,怎么会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啊,那‘信泰来’商号那里,一年下来才有几个利钱?”曾三这是在和黄文焕没话找话说。他一面说着一面想着后面的话题,看怎么才能从黄文焕手里弄到银子。
黄文焕只是对着曾三笑了一下,并没有做答。
曾三把嘴凑近黄文焕的耳边,用手指着酒肆里对黄文焕说道:“我里面有两个兄弟,是走盐路的,他们平日最佩服的就是胆子大,讲义气的汉子。像你这样人,他们一定很乐意交往的,怎么样,要不要我给你们引荐引荐啊?”
曾三根本就没有打算让黄文焕和他们见面,他其实和那两人也并不熟悉。他这样说,是在为后面的话做铺垫。
黄文焕心里“咯噔”跳了一下,他当然知道“走盐路”是什么意思。明代重农抑商,农业和商业的赋税都很轻,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盐税了,盐税收入甚至占到整个国税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如此高的税费下,官盐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于是,那些私盐贩子就孕育而生了。
涟州临近南海,这里的制盐业很有名气,所以私盐贩子也最多。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和那些“抬缸”的商家不同,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带着武器武装押运私盐,如果遇见官兵,就拿出刀枪真刀真枪的豁出命去干,因此这些“走盐路”的大都是一些胆大妄为的草莽好汉。
黄文焕知道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他也不愿意和这些人多打交道。便连忙朝曾三拱拱手做答道:“小弟这边还有急事,你老哥那边,还是等下次有机会再聚吧,小弟这就告辞了!”说完,转身他就要走。
曾三没有借得银子,哪里肯放他走。他一把拉住黄文焕,嘴里对他说:“黄老弟,别走啊,小弟还有话要和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