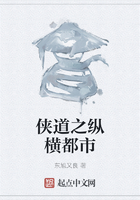偏房门户大开,一幅书画对门而挂,书画下方的是一张长条红木桌案和两张红木椅,桌案上摆着一个香壶,这一切都是李伯坚后来才让人布置的。虽然简易得很,但可能已是这尖山寨上最讲究的房间了。
夕阳西下,日头刚好斜照至红木桌案。与昏黄的阳光相映,从香壶里透出的每缕青烟都清晰可见,那上升的烟迹也寻得来。此时只要一丝微风,吹一口气,便可吹散这青烟。可这青烟袅袅便在杨氏二人面前徐徐飘升。
杨柔媞看着杨休那气愤模样,想安慰几句,牵着杨休的手,置在自己腹上,淡然道:“伯父,确实是李伯坚这贼寇玷污了我,我又怎会不记恨与他?只不过如今恨意已散罢了。”
杨休知道杨柔媞别有它意,又听杨柔媞续道:“但我不否认,这些日子以来,他确实待我不薄。”
“柔媞,你糊涂啊!”杨休听到这里,把手缩回,皱眉叹道,“这些东西,你回家里难道就没有吗?回家的话,自然也是衣食无忧呀。”
杨柔媞摇摇头,唤了声“伯父”,苦笑一番,低头摸了下自己的腹部,续道:“你难道觉得我还嫁的出去么?”
杨休不作声。杨柔媞贞操已失,而且还是被一贼寇所玷污,这名声早已不再,先不说回到饶州,只会给人留下话柄,纵是杨柔媞出生名门,想要再嫁,恐怕寻常人家也难以接受。
杨休再三思量,杨柔媞回到饶州,着实也难以回到往常日子。
可是每想起这是尖山寨,这是一个山匪窝子,杨休就难免心有不甘,叹道:“那总不可能一直呆在这贼窝里吧!”
杨柔媞细声道:“可我也没见过他们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杨休听得出杨柔媞说这话明显底气不足,摇头道:“柔媞啊,你虽然随你爹游历多处,但这武林混乱,人心险恶,你是有所不知。是,我听说过这李伯坚从未有过烧杀劣迹,但他们终究是山匪,这抢掠之事难道干得少吗?你是久居这九顶山,所以没看见过他们下山劫掠百姓的模样。难道你,不就是他们抢掠来的吗?”杨休忽然语止,想到杨柔媞自小性情敏感,便又补了句:“刚刚伯父多言了,你也不用往心里去。”
“无碍,伯父。”杨柔媞点点头。
杨休见杨柔媞如今淡然自若,似乎不再过问这些事情,不知是该喜杨柔媞有了这般悟性,还是该忧杨柔媞已打算呆在这贼窝之中。“柔媞,伯父问你,你可是对这李伯坚有情?”
杨柔媞低头叹道:“怎会有情。我现在是对他,既无情也无怨。要怪,只能怪造化弄人。”
杨柔媞黯然神伤,那双眼眸早已不如往日动人,杨休见状,忍不住眼中含泪,他抬起头来,尽量不让眼泪往外流,微道:“柔媞,苦了你了。”
“伯父,你怎么又说这话。柔媞说了,柔媞不苦。”杨柔媞手捂着肚子,“柔媞如今有这孩子相伴,足矣。柔媞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性命不是自己的,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心头沉淀多了一份东西。那些日子里,柔媞真的是生不如死,可最后有了这个孩子,让柔媞死过一次,又重新活过一次。”
杨柔媞看着杨休,淡笑道:“我要为他而活。”
杨休见杨柔媞眼中执念甚重,续道:“那……总要给孩子换个地儿吧。”
“换个什么地儿,有娘没爹的地儿吗?伯父,柔媞的性子,你是知道的。”杨柔媞皱眉道。
当杨柔媞念及此话题时,杨休方才想起杨柔媞母亲当年难产而死,她乃杨综一手带大,纵然家中丰衣足食,锦缎玉帛无一不缺,但杨柔媞这一辈子缺的,便是一份母爱和一份来自娘亲的关怀。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杨柔媞才执意留在尖山寨,不想这孩子落得与她同般下场。
“虽然这里乌烟瘴气的,但我相信伯父也和这寨里的人接触了,除了李伯坚外,定有其他人给伯父留下些许好印象吧?”
杨休这点倒不否认,回想来到尖山寨后的种种,慎道:“胡雄,虽然粗鄙不堪,但也算得上是条热血汉子;那个站在李伯坚身边的,在这山寨里也算得上是一个知书达理之人,若是不说他是尖山寨的人,我还会以为他是哪个村落的教书先生;还有刚刚那个与你一起的女子,穿衣打扮看起来伤风败化,但看你的样子,仿若她对你还好;而其他人,似乎对你也是恭恭敬敬。”
杨柔媞听得杨休虽然不喜欢尖山寨,但对这帮人的评价不偏不倚,会心一笑,与杨休还道:“伯父,我都有点不知道这江湖上,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了。他们待我,都挺好的。”
杨柔媞见杨休沉默,迟迟不语,猜晓几分杨休的心思,问道:“伯父?”
“嗯,这些我都知道。伯父还是觉得,这事有所不妥。”
“伯父,你可是介意门第?”
“说不介意,那肯定是假的。虽然你非我所生,但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和我亲生没分别。试问有哪个做父亲的,愿意把自己含辛茹苦养了十几年,如今已长得亭亭玉立的闺女,嫁给一个山匪头子?”杨休直言不讳道。
恰巧梁玉娘端着茶进了来,这杨休才罢口不再多说。梁玉娘听得见,但佯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梁玉娘为杨休和杨柔媞沏了茶,一杯端到杨柔媞面前,由杨柔媞双手接过。
“杨妹妹,小心烫手。”
“谢谢姐姐。”
这姐妹相称,更让杨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个喜忧来。
“杨大侠,喝口茶吧。”梁玉娘将茶端到杨休面前。
“谢谢姑娘了。”杨休虽然心里有些不愿,但还是予梁玉娘赔礼道歉,“刚刚杨某因被你们当家的激怒,在走廊里讥讽了姑娘几句,还望姑娘不要往心里去。”
“瞧杨大侠说的,没事儿。奴家既然叫得柔媞妹妹,那自会把她当作自家人,而她的伯父自然也是奴家的伯父。长辈教诲,晚辈总要听的。”梁玉娘虽然语气难改风情,但至少听起来不算逆耳。
而正当杨休和杨柔媞二人坐在偏房中叙旧时,李伯坚等人则还在聚义厅上等候。
贾世英站在聚义厅门旁,仿若有心事,久久不语。
“哑巴。”李伯坚唤了声,然而贾世英却全然未觉,他站在门口低头不语,出了神。
李伯坚又唤了声,贾世英这才反应过来,“啊,当家的。”
“想什么呢?若是在想杨休,不足为虑。”李伯坚知道贾世英定在算计着什么,但仍不明其心意。
“非也。”贾世英长叹道,“当家的,可知道五毒教之事?”
“向来没有听说过,是什么狗屁玩意儿?”李伯坚不屑道。
李伯坚的答案和贾世英所料不差。李伯坚虽然被称为“西李刀”,但与另外齐名的三家相比,“东裴剑”、“北曲钩”、“南岳锤”皆是名门望族。李伯坚孤身一人担当起该名号,实乃因为他的武功高超。然而若非贾世英当初告知,李伯坚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武林中人封为“西李刀”一事。李伯坚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山匪,而非江湖人士,他从不关心中原武林纷争,更别说这远离中原的五毒教之事了。
“当家的,你可知道在你‘西李刀’之前,是谁与另外三家齐名?”贾世英抛砖引玉道。
“这过去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正是那在百年前被五毒教灭了门的唐门。”
“唐门?你是说在巴蜀使暗器的那帮人?”李伯坚生在巴蜀,虽然已是唐门灭门之后的事情,但唐门在巴蜀之地却是家闻户晓,尤其唐门出了不少英杰遗闻,至今都在巴蜀广泛流传。
“正是。唐门历代偏居巴蜀,鲜与外部发生争端。但当年五毒教入中原,第一步便是需拿下巴蜀,而拿下巴蜀之要,唐门首当其冲。”贾世英皱眉道。贾世英心明李伯坚向来不喜武林,所以他才特地道明唐门被灭,并非唐门滋事,而是麻烦找上门来,想借此告诫李伯坚。
“我管那是个什么教,但凡是怀歹意上我这九顶山的,都得问问我这手上的昆吾刀。”李伯坚讽道。
“当家的,此言差矣。”贾世英还未开口,却听一边的姚不明插话道,“老姚我学过医术,当家的是知道的。而这但凡学过点医的人,都对这五毒教略有耳闻。那五毒教自诩五仙教,五毒教是外人的说法。听说五毒教教众的武功平平,但他们的蛊毒之术却是古怪得很,当时中原地区无人能解,只要中了蛊毒,都只能坐以待毙。这学毒的,就怕遇到学医的;而这学医的,就怕遇到这五毒教。”
“老姚说的并非虚假。当年唐门被灭之事,在武林传开后引起轩然大波。中原各派皆派人前往巴蜀讨伐五毒教,也吃了不少亏。幸得后来某位上清宫道长不知从哪得到那解蛊之法,这才迫使五毒教退出唐土。”贾世英续道。
“既然有了这解蛊之法,那还怕什么?”李伯坚越听,越觉得五毒教玄乎。而这越是玄乎,李伯坚则越想会一会那五毒教。
“后来这解蛊之法随着那位上清宫道长消失而失传了。”贾世英念道,“当家的,虽然如今武林各派皆派人前往巴蜀,但万一不敌,纵我们只是一个小山寨,也不可不防。”
坐在一边的胡雄终于按捺不住,嚷道:“怕他个鸟!平时大伙都不怕死,怎么如今听说来了个什么教,就都变了脸色。人家都还没来就这个怂样了,若是来了,岂不一个个都要尿裤子了?”
李伯坚本听贾世英说得入神,后被胡雄如此一搅,大笑道:“哈哈!老胡说的是!好一句怕他个鸟!”
“胡雄,你知道些什么!”贾世英怒斥胡雄道。贾世英见胡雄毫不在意五毒教之事,李伯坚本来对五毒教不了解,仗着自己武功盖世,心高气傲,如今被胡雄这么一闹,贾世英他更别想李伯坚对五毒教有所防范。
李伯坚瞧经贾世英这么一训,胡雄一脸不满,两人将要在聚义厅上斗了起来,又觉得好笑,又不得不上前劝阻道:“好了,好了,哑巴,你这回就当一回真哑巴吧,我心里有数。”
“唉,当家的,你每次都说心里有数,可哪次是真的有数?汉州刺史这边诬陷我们盗取官银,饶州杨休如今又上九顶山来讨杨柔媞,那边南诏国五毒教又卷土重来。”贾世英说话时每一句掷地有声,生怕李伯坚没听进去。
“哑巴,你没听见当家的说他心里有数吗?”
“尽是老胡你在这捣乱!”
“你尽管听当家的就是了,遇到啥事儿俺们一起扛了便是!”
“你真是愚钝不堪!”
贾世英和胡雄关于五毒教的争论刚刚歇下,又起了争端,双方久久争执不下。
“你们使劲吵,吵出个结果了,再和我说声。吵不出来,打一场也行。这么多兄弟看着,也不怕抵赖。”李伯坚看事不嫌事大,起哄道。
被李伯坚如此一闹,当场众人立即吆喝,纷纷要求贾世英和胡雄直接打一场。借着现场混乱,李伯坚悄悄从聚义厅的首座上离开,入了后院。这才意识到已入夜,他一直呆在聚义厅里,竟也未察觉杨休已在偏房呆了半日。
他心里一直放心不下的,是杨柔媞。倒不是担心杨休会不会早已偷偷携走杨柔媞,而是心系杨柔媞与其腹内的胎儿,他方才瞧见伙夫们也在聚义厅内,也不知杨柔媞吃了没。
李伯坚缓步走到偏房门口,却听见房里杨休和杨柔媞尚在叙旧。
“柔媞,你想清楚了没?”
“嗯,柔媞心意已决,如今不是柔媞想不想跟李伯坚,而是这孩子只能跟李伯坚。”
李伯坚听杨柔媞如此说道,内心为之一怔。怔的是杨柔媞主动想留下,怔的是杨柔媞不再怨恨他李伯坚;怔的也是杨柔媞留下不为他李伯坚,怔的是杨柔媞至今未对他李伯坚有任何情感可言。
李伯坚将昆吾刀揣在怀里,倚在走廊墙边,望着屋檐后的那轮明月。月光洒在他身上,映得脸庞明亮,但缕缕寒凉也渗得肌肤。
“柔媞,那我要如何向你爹交代?”
杨柔媞许久不语,李伯坚也提着双耳以待。他屏住呼吸,不敢发出半点声响。虽然当时聚义厅里传出的嘈杂声不断,但在此刻的李伯坚心里,整个尖山寨都是安静的,安静到半丝夜风吹动野草的声音,李伯坚都听得清清楚楚。
“伯父。”杨柔媞道,“还望伯父回去转告我爹,原谅柔媞的不孝和任性。只要他还愿意认我,柔媞这一辈子便愿意尊他为父。只不过,这段时间柔媞是不回去的了。待以后,若有机会,我便会去他老人家请罪。”
“傻丫头,你何罪之有?莫说这些话,这全是那李伯坚之过啊!”杨休叹道。李伯坚在房外听到时,深深舒了一口气。杨休续道:“柔媞,那伯父就不勉强你了。待伯父此行重任完成后,再来看你。”
“伯父要走了?”
“嗯,伯父此行,还要与众多武林同道共议大事,也没办法在此地多留。你可以再多思索几日,好好想想,等伯父手上的事情忙完了,伯父再过来探看你,你到时再与伯父细说这些天你在尖山寨上的事情,可否?”
“那柔媞就不留伯父了,在此祝伯父一路平安。”
李伯坚听得房内三人离座,梁玉娘道:“杨大侠,那奴家去通报当家的一声?”
“何须通报?”杨休嘲道。
梁玉娘走出偏房,正撞着站在门外的李伯坚,被活生生吓一跳,这才意识到李伯坚一直在门外,而杨休也早已察觉到。
受了惊吓,连忙捂着胸口的梁玉娘轻声唤道:“当家的。”
“你们都吃过了吗?”
“什么?”李伯坚这一问让梁玉娘摸不着头脑。
“我说你们都吃过了吗?”
梁玉娘这才反应过来,李伯坚是心系杨柔媞,笑道:“都吃过了。方才奴家见伙房里没人,便自己煮了点小菜,端进偏房。”梁玉娘见杨休和杨柔媞尚在房内,便多往外走了几步,与李伯坚暗道:“那个……当家的。”
“嗯,我知道该怎么做,你去忙吧。”李伯坚把昆吾刀揣在怀中,低头细语。
“那就好。”梁玉娘拍了拍李伯坚的肩膀,随后而去。
李伯坚听得杨休与杨柔媞在房内叹道:“柔媞,那你要好自为之。”
杨柔媞见杨休从自己怀中掏出一个梨形埙来,递到她手中,又听杨休叹道:“伯父是一介粗人,向来出门在外只带兵器和乌骢马。如今这身上只有这个梨型埙,伯父送给你,也当做是留给念想。
饶州杨家人本是制埙起家,世代相传。虽然杨家早已致富,如今以商贸为主,无需制埙计生,但只要是像杨综或杨休这样常年在外的杨家人,身上都会佩戴这么一个埙,以表向先人祈福平安。而像杨柔媞,虽然她没有埙,然而她自小在杨家成长,总能吹上一两首埙乐。
杨柔媞接过梨型埙,楞了一下,迟迟不知该如何应答。
“怎么,不喜欢?”杨休见杨柔媞尚未接过埙,问道。
“不,柔媞喜欢得很。”杨柔媞笑中带泪道,“谢谢伯父。”
“那……柔媞你多保重。”
李伯坚听得杨柔媞和杨休的脚步渐近,可他丝毫没有躲避的打算。忽然脚步声止,又听得杨休道:“好了,柔媞,天色已晚,你就早些歇息吧。”
“伯父,我还是送送你吧。”
“不必了,你现在身怀六甲,不方便。”杨休一边推辞,一边往门口走,顺道将门关上。
“那柔媞恭送伯父了。”杨休瞧见房内的柔媞与他行礼道。待房门彻底关上,杨休瞧了身旁的李伯坚一眼,长叹一口气,却不多言语,仅示意李伯坚与他一同离开房门前。杨休自然是知道李伯坚在门外,纵然李伯坚尽力想隐藏自己的鼻息,但那浑厚的内功却是怎么藏也藏不住。
这两人时而抬头望月,时而低头探路,直至并行走到大院中央,稍离那偏房远些,李伯坚才开口微道:“你挑地儿吧。”
杨休面不改色,续道:“我打不过你。”
李伯坚见杨休淡定状,事实上当李伯坚听见杨柔媞说她愿意为了腹中的孩子而留下来时,他便知道这场架,是打不起来了——他自己也不想打,他未曾想过杨柔媞会愿意留下来。如今放了心,这比武反倒没了心思。他本以为杨柔媞会跟着杨休走,所以才躲在偏房外,以防万一。
但这到了李伯坚嘴上,则是另一番说辞:“你知道就好,这种比武我不稀罕。”他依旧不肯在杨家人面前示弱。
月夜下,他们二人在院子中散步,都不时转头看看偏房,看看杨柔媞熄灯歇息了没。
“呵。”杨休冷笑一声,他知道李伯坚是嘴上逞强,“你觉得你能在几招内败我?”
“三招。”李伯坚应道。
“年轻人,不要太狂妄了,九招。”杨休笑道。
“那我便谦虚点,六招。”
两人尚未讨论出个结论,便瞧见偏房中有人影浮动。那人徐步走到桌前坐了下来,自然是杨柔媞。杨柔媞忽然将手中物提起,碰到嘴边。尔后从房中传出一阵哀婉的埙乐,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杨休听罢,他自然听得出杨柔媞这吹的是一曲《梅花落》,是想借梅花自喻品性不改,但隐约之中却藏着另一种落寞的哀痛。而李伯坚,虽然不懂礼乐,但其埙乐中表达的情感,他还是感觉得出的。然而此时感觉得出,让李伯坚更为五味杂陈,李伯坚很庆幸自己不懂礼乐,也不想听懂。
“李伯坚,我杨休将侄女托付给你,你定要照顾好她。否则纵你逃到天涯海角,我杨休也定不饶你。”驻足的杨休见李伯坚低头不语,唤他道。
“不用你说,我也会照顾好柔媞。”李伯坚笑应。
可这一声笑,却不自然。
李伯坚知道他能够保证杨柔媞衣食无忧,但无论他对杨柔媞千依百顺,恐怕始终无法让杨柔媞接纳自己。在杨柔媞眼中,李伯坚就永远是个毁了她一生的男人。
“喔,是吗?”杨休谈笑间手搭石桌,顺手用单指划过院子里的石桌边缘,便见那石桌的桌柱与桌盘断开,桌盘直接续着杨休的手劲盘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