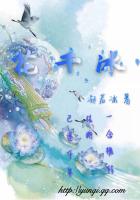莱凤举想不到此行这般顺利,不到半天的功夫就抱得美人归,坐在高头大马上,他的脖子一直拧着,紧盯着身后四平八稳的花轿,唯恐到嘴的羊肉飞了。
一出慕苏城,莱凤举就换上平常的衣服,另外雇了一顶素轿给冰清坐,以避人耳目。湘水已成兵家必争之地,他是断断不敢走了,只能踏踏实实若走旱道,从慕苏城到平阳郡起码有三天的脚力。莱凤举倒不怕花钱花功夫,只要冰清轿子坐得舒服,他不在乎多给轿夫三天的工钱。
冰清端坐在轿子里,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莱凤举的嘘寒问暖,她从不接茬,莱凤举也不计较。第二天一早,一行人走到叠阳城地面上,冰清忽然唤住轿夫,请莱凤举过来说话。
莱凤举受宠若惊,跳下马背,小跑到轿子边上听命,冰清只把帘子撩开一条缝,轻声说:
“莱公子,全凭脚力到平阳郡也太慢了,还是坐马车吧。”
“马车颠簸,我怕你坐着难受。”莱凤举一脸的情深意切。
冰清用袖子掩了掩嘴角,笑道:“坐轿子是舒服,就是慢。怀河郡王两天后就发兵了,咱们要在他发兵前赶到平阳郡才好,凭轿夫的脚力,两天后也堪堪能赶到平阳郡,可咱路上若遇到什么事,耽搁一会子,就赶不到了。到时候碰上怀河郡王的兵马,不定出什么事呢。”
莱凤举想想也对,士兵里难免有可恶的,若半路看到他们,难保不起歹意。
“行,全凭娘子吩咐。”莱凤举豪迈地直起腰来,给了一个轿夫一包银子,让他去城里雇车,再寻个女孩子来跟着,在路上伺候冰清。
“爷不差这几个钱,你雇一辆可靠的车,找一个可心的人,别糊弄我!”
轿夫应了一声,把银子揣在怀里,急煞煞地去了。
“娘子要不要出来走走,这里风景还好,道路也干净。”莱凤举把手伸进轿子。
“公子,你我一没拜过天地、二未参见高堂,还是放尊重些。”冰清蒙着盖头,十指相扣,放在膝头,端庄而冷静,莱凤举讨了个没趣,只得作罢。
莱凤举一转身,冰清暗暗松了口气,袖子里的剪刀沉甸甸的,手柄已被肌肤捂暖,每天夜里,她都要紧紧握着它才能入睡。
将车帘撩开一条缝,见窗外晴空万里、柳丝轻摆,满眼是绿意清凉的阳光。
这里就是闻笛的故乡吗?
正想着,轿夫已经带着马夫来了,莱凤举见那马夫一脸忠厚老实相,马车也敞亮,很合心意。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叫耿子。”
“去平阳郡的路你熟不熟。”
“小人跑过三趟,爷放心,一天多的功夫,准到。”
“哥哥,你走车就罢了,干吗拉着我?”远远传来一声娇音,冰清心头一动,撩开车帘望去,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丫头边扎辫子边跑过来。
耿子指着花轿,说道:“梅儿,这位爷带着家眷,你跟哥跑一趟,路上伺候夫人。”
“我不要,我才不伺候人!”她生得娇俏可爱,眼睛活泛,眉宇间一股英气,穿着葛布短打常服,一根大辫子又粗又亮,话也说得响快,倒像是武家出身。
“梅姑娘,你过来。”冰清声音清亮。
梅儿哼了一声,心想倒要见见这位夫人的真面目,伶俐地跑到轿子前,她一把掀开轿帘,见冰清一身红装,还披着盖头,她惊呼了一声:
“哥,是个新娘子!”
莱凤举脸红了。
他一路上话不敢多说,事不敢多做,就是要避人耳目,这丫头可好,咋咋呼呼地,恨不得把整条街的人都吸引过来。
“爷别见怪,我这个妹妹不懂规矩。”耿子脸都白了。
“扶夫人上车!”莱凤举甩甩袖子,上了高头大马,又把沉甸甸的一包银子递给轿夫,轿夫千恩万谢地去了,耿子瞪了梅儿一眼,梅儿满不在乎地做着鬼脸,就是钉在原地不动。
冰清自己站了起来,也不理梅儿,自己向马车走去,虽然蒙着盖头、穿着长裙,可脚步匀软,走起路来一样翩然生姿。
梅儿见冰清裙摆系着八角金铃铛,却纹丝不响,好奇地问:“你裙摆上系得铃铛是哑得吗?”
“当然不是,这铃铛是驱邪的,若是哑的,怎么震住小鬼呢?”冰清笑道。
“那你走路,它怎么不响?”
“但凡大家闺秀,走路讲究平、和、端、稳,裙尾的铃铛声音越轻,姑娘就越有身份。”莱凤举得意地说。
梅儿哧地一声笑,昂首说:“这有什么,我也会!”
冰清抬起头,把盖头挑起一角,见梅儿扯掉金铃,系在辫子上,脚尖点地,身体平飞而出,如蜻蜓点水,几下就去得远了,不仅铃铛一声不响,她足尖在地上借力时也不起一丝灰尘。
莱凤举目瞪口呆,好久才叫了一声好。
“怎么样,新娘子,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梅儿笑嘻嘻地跑回来,把铃铛系回红裙。
“所谓的平、和、端、稳是走给别人看的,好看却无用;姑娘这身功夫是防身健体的,既好看又有用,自然是姑娘厉害。”冰清说。
“算你明白。”梅儿得意。
“姑娘的武功练了几年?”
“自小练起,有十年了。”
“这样吧,我们出钱,请姑娘保我们一路平安。”冰清说。
“你还当我是一等侍卫啊?我不过会点三脚猫的功夫,遇到歹人,我自己跑还来不及,谁理你们?”
“若真出了事,姑娘只管跑,你跑得了,才能找人来救我们。”
“原来我不是你的一等侍卫,而是你的信鸽,罢了罢了,什么都好,我陪你走一趟吧,好好一个有身份的新娘子,本应该羞答答的不说话,为了把我拐上车啰嗦了这么半天,我倒不忍心了。”
说着,她伸手扶冰清登车。
“姑娘好心,必有好报。”冰清轻声说。
梅儿正要说话,却看到她袖中的剪子。
“新娘子,你——”梅儿一头雾水。
冰清示意梅儿不要做声,紧紧握住她的手腕,把她拉进车厢。
等马车走出十多里路,冰清才放下盖头。
“哇,新娘子,你可真漂亮!”梅儿又是一惊,“你是不是外头那个公子绑去做压寨夫人的?怎么还带着家伙?”
“他不是歹人,也没那个本事,”冰清揉一揉眉心,靠在车壁上,“姑娘,你不必保护我们,这一路上,我只求你帮忙,别让他碰我。”
“他不是你郎君啊?”
“不是。”冰清淡淡地说。
“哎,是不是你爹娘逼你嫁给她?我看他挺有钱的,贿赂了你爹娘不少银子吧?”
“他是贿赂我的叔父,我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我是在叔父家长大的,他用得也不是银子,而是求生的机会。”
“那你还嫁,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吗?”
冰清笑了,笑得孤寂。
“嫁有嫁的用处。何况,叔父抚养我一场,难道我连条生路都不给他吗?”
梅儿不说话了,她觉得这个新娘子心事太多,绕得人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