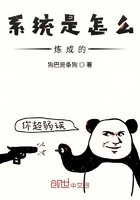关于那封信上的内容,也只能归结到这儿了,在这儿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一个谜。
我也曾经做过无数次的假设和推理,最后只得出了一个自己认为比较合理的结论,那就是他们被困在了那个地方,而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至少有两个人逃出了那场变故,不然就不会有那位少数民族青年口中所说的那封信。
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在你们看来,我的这个目的实在是太无聊了,那就是我要找到我的二叔吕祁,并不是说我有多执着,我只是走南闯北的时候碰碰运气,顺带打听下我二叔的线索罢了。而我讲述的这个故事,也成为我寻找二叔唯一的线索了。
在那个故事发生的十年后,在武汉卓刀泉一家普通的茶楼,也就是2009年年底,发生了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如何的不平常暂且不提,先说我吧,我叫吕桓,是个茶楼老板。我并不认为我是什么很不平常的人,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励志好青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经历实在是太励志了!励志到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是多么的狗血。
小时候我听二叔说,我的父亲吕玄,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失踪下落不明了,我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在我的映像中,我的亲人,只有二叔吕祁,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二叔既当爹又当妈,把我养大。这时候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不是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虽然我没爹没妈,但是我有一个有钱的二叔。从小我就养尊处优,根本就不用吃苦的。
说到我的二叔,他是明面上是个古董商人,说白了,其实是个土夫子,常年跟着徐叔下斗,在斗里摸到好东西挣了不少的钱,因此我的家境可以说是很殷实的,比一般人要好。
但是自从二叔失踪以后,我便知道了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我自己一个人靠着二叔留下来的老本读完了高中,就决定自己出来闯荡了。我的老家在湖南,2006年的时候我来到了武汉。
武汉这里和我家乡不同,我家乡那里依山傍水,风景再好不过了,而且气候宜人,春秋相连,长夏无冬。但是那种地方,不适合我这种有志青年,那时候的我,并不喜欢深山老林里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向往的是商业繁华的大城市,想去见一见世面。
我会来武汉这里,不为其他,只为自己创业。反正在老家那里待着也是待着,年轻人就应该要好好的闯荡一番,因此我来到了武汉这么个“建筑工地”,在这里开了间茶楼。
明面上我是个茶楼老板,其实我也是个土夫子,我继承了二叔的衣钵,但我是个散盗,几乎没有见过大墓,我名气很小,因此知道我的人也很少。
要说起倒斗这门儿活,那是门很高深的学问。别看土夫子都是一副山野村夫的模样,其实内地儿里懂得的东西,可不比那些个专家学者少。盗墓涉及到很多的知识,比如奇门遁甲、各个历史朝代墓葬的格局、以及墓葬的风俗。更多的还有一眼判断出冥器年代,各种各样的机关术、以及寻龙点穴这样的绝活儿。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谈到盗墓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最多人知道的,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他为了补充军饷,从而设立了一个特别的队伍。内设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两种官职。在后来,盗墓便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即为摸金校尉。
盗墓这一行里,南北两派历来都是合不来的。北派比较有讲究,开棺前要在墓室的东南角点一支蜡烛,然后才能开棺。如果在开棺的过程中,蜡烛灭了,这就说明是有鬼在吹你的蜡烛。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停止开棺,把所有东西放归原位,速速退出古墓,否则就要惹上不好的东西。
而南派就不讲究这些了,管你三七二十一,上去就直接开棺,所以南派的做法就比较的粗鲁了。对于现代的盗墓贼,已经很少分什么南派北派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多老祖宗留下的机关巧术都已经失传,所以现代的盗墓贼,要是遇上了一些比较难破解的机关或者墓门,直接就上炸药了,不像以前古代的盗墓贼靠破解机关来倒斗,所以,现在只要是被倒过的斗,就没有一个是不塌的。这对于文物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再说这倒斗的活儿,是没地儿学的,基本都是家族传承下来的,或者是师传徒。而我家上两代都是倒斗的,到了我这一辈,很多行里的技术活都失传了,因此我可以说是土夫子中的“青脸。”很多东西我都没有见识过。
我干这一行,平日里跑路子比较多,比较有名儿的古玩市场,我也多多少少都逛了一圈,比如说京城的潘家园,琉璃厂。因此结识了不少天南地北的朋友。有做古玩生意的,有做玉器生意的,也有做字画生意的,各种行业的都有。
我开的茶楼里平时来喝茶的人挺多,收益也算不错,对于我这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混得算是不错的了。这样的生活,是大多数人都很向往的,但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现在就说说那件很不平常的事情吧,那一天,我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人生就像被卷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之中,再也无法从中挣脱出来了,只能越陷越深。
那一天我闲来无事,就跟往常一样,在茶楼里翘着二郎腿,喝着茶看着报纸。就在这时候,打门外进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眼就能注意到她的那种。
只见她进来了,就站在门边一动不动,环视着四周,像是在打探着什么。至于她的扮相,那就更扎眼了,是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手上还抓着个黑色的皮包,三十多岁的模样,很是风骚,裙子短的都不能再短了,上身也是袒胸露乳,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旁边有些进出的客人,魂儿都快被她勾了去,眼睛都看直了。但是那女人好像并没有把那些饿狼似的眼神放在眼里,依旧淡定自如。我都有种想把桌边上放着的的大抹布给她披上的冲动,因为她穿得实在是太省布料了。
我无奈的朝里大喊了一声:“周禹,招呼客人。”
那女人看向我,赶忙说道:“不用了,我不是来喝茶的。”
这声音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好多旁人也惊得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女人看着面容精致身形妖娆,没想到这声音却是破锣嗓子,极其的沙哑,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仿佛喉咙里堵着一口痰,说话犹如破风箱一样,呼啦作响。
我咽了口口水,不知道作何回答。那女人看我没说话便缓缓的向我走了过来,走到我面前打量了我一下,开口道:“小兄弟,你是这儿的老板吧?我是来找人的。”
我放下报纸,这下距离近了,我就又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她的脸白得不像话,毫无血色,就像一面粉刷过了的墙,完全没有活人的样子,难道,她患有皮肤病?
我下意识的捂住了口鼻,装作患有感冒咳嗽的样子,离她远了一些。不是我不待见她,而是万一被她传染了皮肤病怎么办?我才二十三岁,以后我还得娶老婆呢,这要是毁容了,那可怎么行?我可是吕家的独苗啊。娶不到老婆就没有儿子,那样的话,先人估计会被我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于是我捂着口鼻道:“我是这儿的老板,请问你找谁?”
她看我这个样子,随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瞧你那样儿,我有那么可怕吗?”随即便凑了过来,接着又道:“我是来找江允的,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找他。”
“江允?”
我看着她煞白的脸,以及鲜红如火的红唇,怎么看怎么诡异。不过面子还是要给的,虽然我很不想和她说话。
于是我努力的挤出了个笑容回答她:“对不起,你找错地儿了,这里并没有叫江允的人。”说完我就拿起报纸继续看了,不再继续搭理她。因为这人奇奇怪怪的,看着就不像个好人。不,简直就不像个人。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人一点儿自知之明都没有,虽然我没有明面上表达我要送客的意思,但是我已经做的已经很明显了,只要是知趣的人就自然会离开。没想到她站了一会儿,居然就在我旁边找了个位置坐下了,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她的这一举动,很快便引起了茶楼里其他客人的注意,纷纷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我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侧头对她说:“我都说了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你还是去别处找吧。”
她直勾勾的盯着我,妩媚的笑着说:“怎么可能没有呢?我可是调得一清二楚,他就在你的店里,不会有错的。”
我的脸色瞬间就变了,调查?什么意思?怎么搞得跟什么特务谍战似的,难道她是个雷子?我的底子本来就不白,前几个月还倒腾了一个小墓,即便她不是雷子,也肯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本来我就对她没什么好感,还说什么调查得很清楚之类的?难道她偷窥我?感情我这是碰上女变态了啊?于是我也不给她面子了,不耐烦的说道:“这里真没有你要找的人,你要找别处找去,走好,不送!”
她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一脸愤怒的看着我:“嘿!你这人怎么这样?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不承认他在这里是吧?那好,我自己找!”说着就气势汹汹的上了楼。
我心里暗骂,什么人啊?!这里本来就没有叫啥江允的人,这人简直不可理喻。要知道,在楼上的包间里喝茶的,都是一些有钱的老板,能不得罪的还是不要得罪的好。她这是要是上去搅了局,那可就大发了。这是要踢馆的节奏啊!
我急了,追上前去就把她拽了下来。没好气的说道:“我说大姐,您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我这里真没有叫江允的人。”我作势就要拉她出去。
她瞪了我一眼,死命的拽着旁边的屏风,就是不肯走。那屏风可是我前些日子花了大价钱置办的。我心疼我那屏风,只好放开了她。这里人这么多,再这样闹下去肯定会让人看笑话的,我也就不管她了,回到位置上继续喝茶看报纸,看她一个人能耍什么把戏。
过了一会儿,她见我没理她,也终于沉不住气了,又来到了我面前,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我。我狐疑的接了过来,她说:“你看吧!就是这个人,他绝对在你这里!”
我拿着照片一看,是张很老旧的灰白照,看样子,应该是十几年前的照片了,没有塑封,但是照片保存完好,可以很清晰的看见照片上的内容。
只见照片上的,是一个十几岁模样的小男孩,面容很清秀,照片的背景里仿佛还有亭台楼阁,看样子,应该是个大户人家的孩子。
我盯着照片看了有一会儿,越看越觉得像一个人。
突然,我脑海中就一个激灵,这他娘的不是周禹那小子吗?怎么就成了江允了?
虽然周禹现在已经是个二十一岁的大老爷们儿了,但我还是能认出来的,因为照片里的人面部轮廓和周禹差不离。这张照片里的小孩,应该就是周禹没错了。
说到周禹,他是我茶楼里的伙计,也是我最要好的兄弟。我平日里经常出门在外,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因此茶楼里的一切都是他打点的。
至于他的来历,说出来可能有些好笑。因为他是我五年前,也就是2004年,我还在湖南老家的时候“捡”来的。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无家可归流浪儿,虽然风尘仆仆,但是看上去并不邋遢,十五六岁的样子,年纪与我相差不多,又因为经常能在街头上碰到他,我看他挺可怜的,于是就收留了他。
把他领回去后,我问了他的名字,他说叫周禹。我让他不要客气,把这儿当自己家,没想到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下来了,他挺感激我,对我很尊敬,平时总是左一句桓哥右一句桓哥的,他也一直是和我生活在一起,俩人年纪相仿,共同话题还是挺多的。
我曾经问过周禹他有没有亲人,他回答说是有亲人的,那是一个老流浪汉,只不过那个老流浪汉,在周禹他还没遇见我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具体怎么死的他没有说,我想应该是正常的生老病死吧。我也问起过他家在哪,他说在京城,详细地址他已经不记得了。这里和北京,一个南一个北,他们是怎么流浪到这儿的,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我没有多问。
我看着手上的照片,心里有些纳闷。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他又为什么会认识周禹?而且还说他叫江允,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为什么会有周禹小时候的照片。
难道她是周禹的家人?来找回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不过这个猜测未免也太牵强了,而且她刚才说了,找周禹是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她应该不是周禹的家人,不然知道了亲人的下落,这会儿肯定已经在吸鼻子抹眼泪了。
看来,周禹肯定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不然江允这个名字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在骗我?
不,不可能。
周禹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的,是绝对值得我信任的。他没有什么心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蠢得像个白痴,经常能给人气掉半条命。他也是个很重义气的人,对我绝对是两肋插刀,所以他不会骗我,应该是有什么苦衷,待会儿我要好好问问他。
我思来想去,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还是谨慎一点儿为好。
我看完了照片,抬起头,面无表情的看着她,指着照片上的人问:“你说他叫江允?”
她看我态度有了转变,于是立即应道:“是的,不然他还能叫什么?还请麻烦你帮我引荐一下,我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我考虑了一下,道:“可以,但是你不需要自报一下家门吗?”
她点了点头,道“我叫周元瑶,算是他的姐姐。”
此话一出,我只觉得五雷轰顶。
****!没想到周禹居然还有这么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姐姐!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啊!我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只见她又恢复了那个妖娆妩媚的模样,凑了过来笑着说道:“那么小兄弟,现在可以帮我引荐了吧?”
看着她凑过来的脸,我心说:大姐,你这脸刷得比墙还白,还是不要笑的为好,难道你就不觉得自己笑起来像个女鬼吗?
“不可以。”我淡淡的吐出了这三个字,面无表情的看着她,只见她又有要发飙趋势,胸口剧烈的起伏着,嘶哑着声音厉声道:“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出尔反尔?
我只觉得好笑,道:“这不是出尔反尔的事情,你说你调查得很清楚,那么你完全可以对你所说的江允的行踪了如指掌,然后找到他,何必这么麻烦再多我这么一个中间人?你的一举一动,让我很难相信你。”
她听完我说的话,脸上的表情很是精彩,片刻后又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相不相信我那是你的事情,我也不是什么江湖骗子。这里有两封信,还请你把它转交给江允。”说着就把周禹的照片塞回了包里,把信放在了桌上,转身走了出去。
我看着眼前的这两封信,一封很老,貌似还被拆过的样子。另一封很则很新,完全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