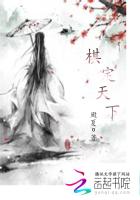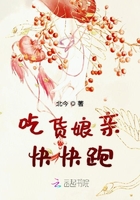2004年初秋的一天,当我给老同学国家民委《中国民族》民族团结杂志社社长李建辉先生送去我的两部满族历史人物的长篇小说时,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关于满族移民的好题材,我就这个题材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寻26。年前的北京知青》的文章。这题材很适合你写,一是因为你是满族,二是因为你有插队的经历,这次满族的移民与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很相似。”于是他便津津乐道地介绍起这段历史:
2000年7月21日,哈尔滨电视台一名记者给哈尔滨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研究所送来了一册题为《拉林阿勒楚哈京旗原案》的手抄本,经鉴定确认这是一册保留在民间、抄自于清政府公文馆所藏的公文档案,极具研究价值。档案中的“拉林”即指今黑龙江五常市拉林镇,阿勒楚哈即指黑龙江省的阿城市,清政府写成“阿勒楚喀”。所谓京旗,就是指乾隆五年、九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相继从京城迁移到拉林的阿勒楚喀的满洲八旗人,简称“京旗”。
《京旗原案》是对乾隆年间京旗闲散移垦东北地区最直接、最具体的记述。调拨北京的闲散旗人到拉林阿勒楚喀满族发祥地开荒种地,学习农业并练习国语骑射,恢复民族旧俗,既能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又可延续国柞。这是清中叶实施的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举动。
自公元1644年顺治皇帝率八旗劲旅进关建都北京后,为巩固政权,清廷把八旗兵视为“固国之根本”,实行“恩养”政策,以至清一代八旗子弟即从出生伊始便享领俸禄,坐吃皇粮。旗人只能吃饷、骑马打仗,不准做生意和务农。后由于八旗人丁增至数倍,再加上旗丁妻子儿女总数已达二三百万,旗人生计全靠朝廷放粮饷,给朝廷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而旗人的生计却每况愈下,负债累累者有之,典当旗地者有之,好逸恶劳,奢糜浪费,侵袭着旗人上上下下。八旗子弟不仅丧失了人关之初的淳朴之风,也丧失了当年格斗拼搏之气。清廷屡屡拨帑替八旗偿还债务,赎回典当的旗地,赈济八旗贫丁,动辄耗帑百万两,这就迫使清廷另辟途径,下决心将在京的闲散旗人移驻东北。
长篇历史小说《京旗魂》即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主要描写以谭荣、谭刚和索力两家京旗闲散迁移东北拉林、阿勒楚喀,和当地满族以及汉人流民共同生活中,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性格,所造成的种种矛盾。
在京城过着优越生活的京旗闲散一到东北这苦寒之地,巨大的生活落差和文化落差使他们感到十分苦闷和孤独。内心柔软,多愁善感的文人谭荣在拉林蛮荒之地除了生活困苦外,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文化饥渴和性饥渴,在他和几个女人的关系中充分体现出灵与肉的抗争。
谭钢和索力作为京城的两个“混混儿”,由于不同的性格产生了不同的命运。二人一直在“斗狠”。但由于谭钢单纯、鲁莽,最终斗不过心狠手辣、颇有心计的索力,最终死在索力手里。而索力虽然升了官,但却没有爱情,又失去了女儿,他内心也是孤独的。
两个汉人形象,刘顺儿是亦善亦恶,王岩是精明的商人,他对爱情的追求最终逃脱不了商人的利益观的束缚。
小说还塑造了几个对爱情大胆追求的满族女人形象,为了爱情她们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具有鲜明的满族女人刚烈的性格。
这次移民是对清廷的“恩养”政策的一种动摇,是以后持续向吉林,黑龙江移民的滥觞,而丰厚的京旗文化作为满族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与当地坐根满族及汉人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最终导致了东北地区的快速开发建设。
我在这部小说的资料收集、构思及创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除了上述提到的老友李建辉外,还受到了原哈尔滨拉林镇党委书记石国璋先生、历史学家伊葆力先生的大力支持。伊葆力先生和石国璋先生为抢救和挖掘、宣传京旗文化呕心沥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耐心和勇气,他们的执着和奉献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的创作。同时还得到了原五常市档案局局长郎国兴、满族文化学者那海州等人的帮助。
尤其要感谢是在小说付梓时,得到了陕西咸阳西秦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姚明通总经理的大力支持,姚总不仅是着名企业家而且还是文化产业的热情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创办的陕西大团结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宣传、推广、造就了很多文化艺术人才,为推动和发展文化产业作出了积极探索和努力。值得高兴的是,姚总已有意购买该小说的影视制作权,正准备和石国璋、伊葆力先生及一些支持京旗文化的有志之士,策划和筹备把该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作为热心于京旗文化的笔者,为此感到十分欣慰。电视连续剧的播放将更加有利于京旗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必将促进拉林地区的旅游业、文化产业和当地经济的发展。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