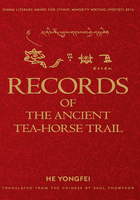而这位诗人,他现在又是自由的单身男子,对于爱情的追求再一次将他那浪漫的烈火引燃。对于这样一个不断追求着纯洁的美、纯洁的爱、精神自由和创造性的男子来说,他再一次堕入情网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的陆小曼与志摩当时认识的徽因并不相同,这时的她已经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她结婚四年的丈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可是陆小曼并不爱他。小曼是与志摩有着相像的性情的,她的骨子里天生追求着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可是这一切,这位高级军官并不能给她。因为性情爱好不合,婚后生活可想而知有多么的乏味且不愉快。可陆小曼是个骄傲的人,从不愿让世人看到她的失意,所以在外人面前,她表现出来的都是快乐的一面。
但是敏感细致的诗人发觉了。她的已婚地位并没有阻止徐志摩的追求,如果有点什么的话那也只是刺激他更加热情地去追求。“同是天涯沦落人,两颗寒冷的心偎依在一起便有了温度。陆小曼不同于林徽因,她虽亦是京城名媛,但她风华、招摇、妩媚、叛逆。王庚的庸常根本就无法填满她骨子里需要的激情,无法在她心河里溅起激荡的浪花。”
浪漫多情的徐志摩可以读懂她眼中的秘密,知道这位戴着快乐面具的女子内心深处并不像她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他明白,她需要热烈的焚烧。而徐志摩对林徽因苦苦压抑数年的情感,亦需要一次彻底的释放。
有很多人曾经将林徽因与陆小曼做比较,觉得这两个女人,虽然都是才貌双全的世间少有女子,但毕竟不同,陆小曼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位上流社会的倾城美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感情是一杯白开水,没有几多值得令人品尝的滋味,却也可口怡人。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爱情则是一杯深藏经年的红酒,一旦开启,那馥郁醇厚的芳香令人沾唇即醉。有人说,徐志摩和陆小曼相爱是为了将林徽因忘记,为了让自己从那段无果的爱情中解脱。也有人说,陆小曼本身就是一团火焰,林徽因清澈得就像一潭幽泉,所以,无论诗人有多么的爱徽因,徽因都是那样的平静,而对于小曼,这位浪漫的诗人,又似乎始终都不能满足他内心的热望。
陆小曼当时也算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恋情,自然引来公众的目光。加上徐志摩之前的离婚等等,她和他的爱情竟成了一件被人们议论纷纷的似乎是不甚光彩的事情。由于志摩和小曼的爱情纠葛在北京引起了人们议论纷纷,成了一桩丑闻,以至志摩只好在1925年离开北京五个月。他回到欧洲并到处旅行,不断写情书向小曼倾吐他的爱情。
梁启超在一封信中向他远在美国的孩子们报告了这件事。“昨天我做了一件我不愿做的事——在徐志摩的婚礼上当证婚人。他的新婚夫人以前是王守庆夫人。她爱上了徐志摩,同王离了婚。这是极端不道德的。我骂过徐志摩好几次,可是没有效果。由于胡适和张彭春一定要我担任这个角色,我就在婚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严厉批评了新婚夫妇。年轻人往往受到自己的感情所驱使,不能控制自己,破坏了传统的安全保障。他们掉进了使他们遭受苦难的陷阱。这确实是可悲和可怜的。徐志摩真是很聪明,我很爱他。这一次我看着他沉沦,很想救他。我真的在尽一切力量来救他。”他以一句体己的话来作结束:“这些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我特别写出来给思成、徽因和思忠。”
在此后两年中又有关于徐志摩生活的什么消息传到费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看来诗人并没有放弃他对于诗歌的热爱。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25年出版。两年后又有第二部,还有四本散文集。1927年他离开北京去上海教书,在那里他组织了新月图书公司并开始出版新月月刊。
安意如说,身为女子,通常会陷入一种矛盾中,即:你是要自己的夫婿出人头地,还是无风无浪,做个寻常居家男子,与你柴米油盐,度此一生。绝不是现在的女人才有这样选择的烦恼,否则古时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闺怨诗,也不会有人叹“悔教夫婿觅封侯”,更不会有人怨“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男人,若无事业,等同在这世上无自身的价值,失去现实的土壤,久了,自然会光彩黯淡,变得落寞暴戾。嫁给这样的男子,待时光洗去淡泊,剩下久泊无聊时,你还这样心无别念地爱他么?
陆小曼是颇懂得这一点的,对于她来说,如今这个男子的才情虽不至于叫自己“悔教夫婿觅封侯”,但她也不会放弃要他对自己有千万倍的溺爱。志摩又天性乐观,对于常人眼中看作难的事,他总是可以举重若轻地解决掉。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出众的能力,因为世上奇能异士大有人在,志摩并不是世间唯一。但他却有着一颗旁人所望尘莫及的对于浪漫的执着,为了所爱的人,他会做一切她所希望的事情。无论是文坛生涯的浮浮沉沉,颠沛流离,还是情感上的分分合合,聚聚散散,他可以因为爱而不顾一切。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无论对于人还是事,他极少怀芥蒂之心处之。
当思成和徽因北上定居于沈阳时,志摩回来了,情绪很低落,他回到他的故乡上海,他的教学生活、他的出版公司和他的新月月刊都要求他回来。第二年胡适邀请徐志摩到北大教书。于是他得以就近不时到沈阳去看望他的朋友们。北总布胡同的房子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每当他的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时,他就住在那儿。他既是徽因的,也是思成的受宠爱的客人,在这么欢乐的氛围中,他非常乐意同他们一起聊天。
有一个梁家的亲戚,在1931年作为十几岁的年轻人曾经在梁家见到过他好几次,她是这样描述她对他的印象的:“他的出现是戏剧性的。他穿着一身缎子的长袍,脖子上又围着一条英国制的精细的马海毛围巾。真是奇怪的组合!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的外表多少有些女性化却富有刺激性。他的出现使全体都充满活力。徽因是活泼愉快的,而思成总是那么热情好客。”
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金岳霖——他最亲爱的朋友之一。金岳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熟识的人都这么叫他——最重要的是,日后的徽因也这样亲切地称呼他,金岳霖是深奥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中国头号专家。丝毫不像他的专业所提示的洋怪物,他是高大瘦削、爱打网球的知识分子,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他比思成和徽因都要大几岁。在国外学习了几年之后,他回到中国并被安排到清华大学教哲学。
在后来的日子里,金岳霖是把自己从属于梁家的——徽因是吸引他的主要力量。她那众人都感知的吸引力,向他提供了在他那深奥的精神领域内所缺乏的人性的旋涡。在她这方面,他的广泛的人生经历和他天生的智慧使他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他当然是爱她的,但是无私地和坦诚地爱她。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
这一段日子里,北平的徽因的朋友圈是非常热闹的,她的家庭沙龙颇受欢迎——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像“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
对于陆小曼的任性,徐志摩只能一味地宠爱,但是她与徽因不同——她的个性太强了,常常令志摩有些为难,每每这个时候,他总会想起林徽因,那个在他最美好的年华遇到的水仙一般的女子。懊恼的时候,徐志摩常常仍会跑去向她倾诉内心的苦楚,对林徽因说:“看来,我这一生不再有幸福了!”而林徽因则极尽温和地安慰他,因为由始至终她都希望徐志摩能够幸福。在她的记忆里,始终觉得志摩仍是康桥上那个帅气干净的大男孩。她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那一晚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然而正是这样一首动人的诗作,1932年陈梦家在主编《新月诗选》时并未收录,而当时同样以笔名“尺棰”发表的《仍然》则被收入其中:
你舒伸得像一湖水向着晴空里
白云,又像是一流冷涧,澄清
许我循着林岸穷究你的泉源:
我却仍然怀抱着百般的疑心
对你的每一个映影!
你展开像个千瓣的花朵!
鲜妍是你的每一瓣,更有芳沁,
那温存袭人的花气,伴着晚凉:
我说花儿,这正是春的捉弄人,
来偷取人们的痴情!
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
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
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
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的沉静
永远守住我的魂灵。
对于志摩来说,毫无疑问,已经把徽因当作了自己的红颜知己,在他的心目中,徽因永远都是他刚刚认识她的时候那样美好。而在徽因的内心深处,徐志摩永远是她最信赖的蓝颜知己,徐志摩永远都是当初康桥上的那个多情男子,不曾有丝毫的改变。
思成是没有志摩这般浪漫的才气的,他更多的是一份踏实。而这一份浪漫的才情所流淌出的文字,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懂。可是对徽因和志摩来说,即便那是一张白纸,他们也会明白对方的内心。
《那一晚》发表在1931年4月《诗刊》的第二期,而这本期刊的主编正是徐志摩。徐志摩曾经作过一首名为《偶然》的诗,表明自己的心志。而徽因的这一首《仍然》实际上是对他的那首诗的回应。
徐志摩明白徽因的意思,你听,他说:
你先走
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
别叫尘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地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远去
这份感伤动人、含蓄的情谊在其唱和的诗作中得到了真切流露。徽因与志摩间心心相印地作诗唱和,乐此不疲,而这一份情感,旁人或许会看得出几分,却不会理解他们此刻精神上的欢愉与获得理解的慰藉。
或许,在这之前林徽因以为自己已经被岁月消磨了最后一点诗情,以为学术与生活的琐事将会取代了生活的全部。可是,志摩的再度出现使她的诗情复燃。
白落梅说:这样的感情,一生只有一次,也只要一次。林徽因为徐志摩美丽地绽放过,所以她此生无论以何种方式行走,以何种姿态生存,都将无悔。而徐志摩亦是如此,在他的生命里,那样清澈地爱过,真的足矣。他们的青春被装订成一本唯美的诗集,让每个读过的人都爱不释手,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