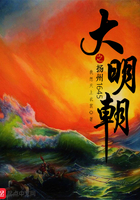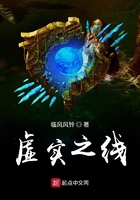青州,是《禹贡》“九州”之一,于太古,老祖宗唤这为东夷,自大禹治水后,便有了大名青州。
青州水道多,太平年间据说来往商船络绎不绝,无数商贩纤夫皆依何而生,只是这天道乱,莫要说商船了,河畔间连帆影也没有,唯有入了北海,进了孔文举治下的北海,商船商贩才多了起来。
话说青州也是个灾祸颇多的倒霉地方,黄巾未平时这里便聚集了黄巾军几十万数,没法子,这青州隔年差月便有几次蝗灾,旱灾,似乎连上天也不怜惜这里的百姓。
待张老道死了,黄巾各个渠帅也被官军平了,只是青州仍聚有不少黄巾余孽,特别是大寇管亥,光和年黄巾起义,此人乃是青州渠帅卜已的麾下大帅,青州人自古凶悍,在黄巾爆发时更是聚有贼军几十万数,可以说这青州军便是黄巾军当时的主力兼后盾,后来黄巾被官军击溃,卜已身亡,管亥带着残部逃到崂山,占山为王,做起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买卖,时不时就侵袭北海东莱来往的商贩,那时的兖州刺史刘岱便被这群手执粪叉木棍的贫民捅死了。
有了兵源,加上本身管亥脑袋也不错,一见着官军来讨便躲进深山,一时间官军也奈他不何。
若逢着天灾或者官府不体恤,合计着与其饿死或被苛政购税害死,倒不如夹着脑袋,投奔管大王去,倒保得两顿餐饭。
暖阳当空,河水似那歌女的薄衫长袖,蜿蜒盘旋,连绵不绝,岸边青山霭霭,白雾寥寥,鸟儿不时从深山中飞出,拖着长尾儿,点过碧波。浅滩上有大片大片的鹅卵石,流淌的溪流拐过弯,掠过浅滩,叮咚一片。
明明是个人迹寥寥的地方,却有马蹄踢踏人语声不断,四处亦有鼓鼓的帐篷设着,似是有商旅在此下脚呢。
河水清澈,冰冷入骨,浅滩尖石水草萋萋,鳞鳞的波光闪耀着,倒映出水下弯弯曲曲的黑色小影。
有一年轻男子赤足于浅滩,凝神注目,手上长枪举着,眼神平静。
溪流转过了弯道,流淌得更欢快了,有波浪击中岩壁,溅起了纷飞的水珠,就在这时,那人单手提枪,喝道:“起!”
红缨抖动,枪头如闪电般刺出,明明是个尖长的枪头,落到河中却猛然发出“嘭”的一声巨响,若奔雷,无数水花飞溅,河底也被奔腾的水流搅起了浑浊了黄沙,受惊的鱼儿一溜烟就消失了。
“子谦,你又失败了!”有大笑声从岸边传来,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脸上还带着些许稚气,唇上蓄着胡须,露出了几分男子汉的气概,他赤着上身,露出了一身小麦色的腱子肉。
说笑间,青年挽起了裤脚,几步便奔到了浅滩,与提枪人一同伫足。
“这个时候若在徐州,灌碗冰镇的乌梅汤那就痛快了。”那年轻男人说着,望了眼一片狼藉的河岸,不由得大笑:“子谦倒是巨力,用木头的枪杆也能弄出如此声响,真真如夏雨倾盆啊!”
那年轻男子却没搭他话,嘴唇抿着,皱眉苦思。
“子谦,莫要想太多了。”蓄须的汉子举起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想我初入师门的时候,可没你这么厉害,师父说你是练武奇才果然没错,我当初学时也是学了三年才练到举重若轻,枪落水而不惊鱼,那是师父才能做到的。”
“啧啧。”那青年望着被水流弄晕浮水的鱼,不由得感叹出声:“暗劲凝于枪,子谦你的进步也太快了,可能没过多少时间,我这个当师兄的就要被你超过了。”
这两人,是由徐州出发来到青州附近的刘瑜和糜芳。至于为什么要到这里,那还得从拜师说起,糜芳的师父乃是一隐士,于糜芳幼时被请到糜家,亲自教授糜芳枪术,只是他师父却是闲云野鹤般的性格,一生醉于武道,没过多久,把要交的写了下来,自己提枪便走,闲暇时也会回糜家暂住一段时间,最长不过两个月便离开。
古人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糜芳这公子哥的性格对他师父也是尊敬的很。
“姚师说我只是记名弟子,你却是内门的,怎么比啊。”刘瑜有些沮丧,糜芳出去大概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回来那天就带着刘瑜见了那个神秘的师父。
“这是个像乡下闲汉般的老人。”
在见这便宜“师父”前,刘瑜一直在脑海描绘着他的形象,想着他是不是气度不凡,或者面生异相之类的,但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闻名。
这个高坐在大堂,与糜贞老父同座,一身破麻布衣裳,兼之吃饭样子如猛虎下山,却深受糜家上下尊敬的猥琐老头,就是糜芳师父?除了手掌上颇厚的老茧,还有那双不似老人浑浊的闪着精光的眼睛,他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颐养天年的老汉而已。
以貌取人是人类的通病,刘瑜也避免不过,当下就对这便宜师父心凉了几分。
只是当这农民样子的老汉拿起了手里的枪,刘瑜便对他瞬间改变看法了。
那根梨花木制成的长枪哪是一根枪啦,在老汉手里,这根长枪仿佛有了生命般,如同触动了逆鳞,怒不可遏的白龙,撕咬咆哮,一挥一击之间,糜芳与他那训练有素的家兵便如同触电般反弹后退。几息之间,糜芳连同十数个家兵个个倒地
而且老汉用的不是枪头,而是枪尾。
等收起了木枪,老汉恢复原样,依旧让人感觉是一个乡下的老汉。
但刘瑜再也没有怀疑他了,只是当糜芳提出拜师的时候,姚师父却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也很令刘瑜郁闷,说是无缘。刘瑜只能当了个记名弟子,随后与糜芳一同游历青州,而那姚公依旧留在了糜家。
“子谦,你说这话就不对了。”糜芳表情严肃:“师父虽然只让你做记名弟子,只是身上的所学却一点也没有藏私,全部教授与你,其实是师父他老人家怕教不好你,所以才不肯收你为弟子的,师父说过,你天生就是练武的,身架子是他在世见过最好的,虽然根骨已定,但未来的成就有多少,连师父也不敢说。”
“好吧,是我不对。”刘瑜有些闷闷不乐。
“子谦你就不要介意了。”糜芳也举起了自己的长枪,轻抖红缨,一声轻微的“噗通”声后,一条大鱼被长枪穿过身体,张着鱼嘴扑腾不已。
“好男儿当执三尺剑锋,于战场厮杀,马革裹尸亦无悔。”糜芳把插着鱼身的枪头举起,鱼鳞在阳光下闪着白光,而糜芳的眼睛里,也流露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光。
慷慨了一会儿,糜芳又苦笑道:“若贞丫头听到我说这种话时,定会告与老父,又说我看低女性了。”
说这话时,他流露出既宠溺又惧怕妹妹的神情。
有家兵把被巨浪震晕的鱼拾起,自有随行的下人拿去烹煮。
鱼汤白皙浓稠,鱼肉亦是鲜美,有家兵把捕到的野味架着树枝一烤,顿时油香四溢,喷香扑鼻。这野外的食物就是不一样,虽有种腥味,却因是自然生养的,不仅肉质肥嫩,脂肪厚实,更有种很特别的鲜香味,一口咬下去,当真是满嘴是油啊。
又或者说是因为这四周春意盎然的两堤垂柳,渔歌悠扬的湖光水色,一群汉子生着火,时不时的说些荤腥臊话,哈哈大笑。
吃着手里的美味佳肴,刘瑜的心情却没有那些满身肌肉的家兵那么happy,出了徐州约半个月了,也不知季兰和宝儿过得怎么样了。
穿越这么久第一次出远门,他就像一个离家的游子,心里无时无刻都在想着那朐县的每一块土地,季兰临行前的叮嘱和嘱咐还萦绕耳边,而每当夜晚仰望着点缀着碎钻的夜空时,他就会从这黑羽绒般的天空看见了前世许多的事情。
从徐州出发游历半个月之后,刘瑜变了很多,他黑瘦了,精壮了,粗俗了,脸色虽然依旧白如瓷玉,却没有了当初那种白脸书生的柔弱,他也不会像以前那种瞧着看不起的人就冷着脸面对人家,他嘴里也能像糜芳身边的汉子一样,不时的说些粗俗的话语,而且更丰富。
他的眼眸依旧明亮,却没有初到汉末时的迷茫,浮躁从他身上褪去,留下了一种内敛的沉稳。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是半个多月的日子,就让这个还对着命运迷茫的后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于文,他的毛笔字不再像鬼画符那样了,对繁体字,也能勉强的认了个通透了,于武,很值得高兴的是,连糜芳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力气太大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而如果力量达到了一种极致也会像他那样,依靠蛮力生生把人欧死,虽然技巧还欠火候,生疏不稳,但他靠着蛮力,每次都会把糜贞郁闷得半死。
所以每次比完武后,糜芳总会很难过很不甘心的要去检查他,明明看起来不是很壮,连一丝肌肉的弧线也没有,却不知为何力气大得吓人。
接下来,糜芳和刘瑜一行人会到北海郡,见见孔融,沿途顺便买些手信给糜贞与宝儿,这次的旅途便宣告结束了,孔融是糜芳兄长的好友,糜竺常受邀与孔文举的宴会,而且糜芳说,到了北海,要让刘瑜结识一个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