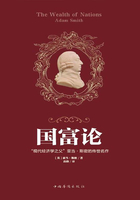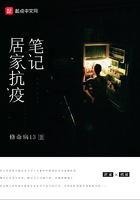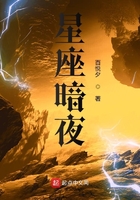沙旺斯说,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大批研究人员从事有关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但见解明显不同。
在社会学家A·埃茨奥尼的影响下,斯金纳和温克勒(1970年)在他们的乡村政策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不尽真实的周期模式。他们从目标周期、权力周期以及分配周期的相互影响出发,将周期划分为六个阶段:(1)正常期;(2)动员期;(3)高涨期;(4)恶化期;(5)收缩期;(6)恢复期。在1949年到1977年之间,出现过11次这种周期,每次2~3年。在斯金纳看来,限制农村市场的政策与有限制的宽容态度交替出现,表现为“走两步、退一步”。
D·珀金斯认为,应该在计划的实施中观察经济周期。首先,中国的经济周期受固有的统一计划矛盾的影响,即时而强调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时而又强调投入资源的有效利用;其次,周期又受国家社会目标与技术需要之间冲突的影响,这一影响表现为时而信任技术,时而又不信任它们,也就是在所谓“红”与“专”之间走钢丝。珀金斯说,中国的经济似乎有一种机制,它不需要形式上的五年计划和市场,便可以纠正发展大方向的错误。经济方向的变换,常常与上层领导的政治冲突相关联,这些冲突往往又是以各个时期的发展战略的变化为依托的。
有多位学者谈到了农业波动对经济的影响。Kuan唱I·陈(1972年)对1952—1965年的中国谷物生产、工业生产、纯投资和前一年的国内净产值等四个变量关系做了分析,认定谷物生产和工业生产与国内净产值有本质的关系。他说,中国既属于不发达的世界,又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类型的世界,即两类世界的混合体。于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既具有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不发达世界经济波动的特征,又具有中央统一计划体制的那种不稳定的特征。
中国的投资周期引起了日本经济学家的注意。S·艾西凯渥专门研究了周期波动这一术语。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周期首先应该是一种“政治交易周期”。这种周期是与计划工作者及政治家权力的突然更迭以及典型中国式的“群众性探索”过程分不开的。他鉴明了两个设备周期:第一个设备周期从1952年到1962年,以大规模引进20世纪40、50年代的前苏联技术为特征;第二个设备周期从1962年到1978年,这时以仿制技术为重,引进较少。然而,两个设备周期分别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艾西凯渥指出,有四种限制———食物、就业、外汇、消费等决定了“可运行的空间”,一旦越出这一空间,将会发展大动荡。他认为,有四种因素可能导致大动荡,它们是(1)结构性失衡;(2)体制因素;(3)落后的计划水平;(4)盲目性。他对中国投资周期的分析是建立在 J·科尔内的“软预算约束”基础上的,他认定中央计划的过度投资是周期的根源。这方面,他的分析与T·鲍尔(1978年)关于东欧和J·萨宾(1985)关于前苏联的投资周期分析是很类似的。艾西凯渥还认为,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投资膨胀则是来自于权力的分散化及信贷膨胀。
N·马鲁雅马(1982年)指出,在中国,高积累率、低资本产出率和高资本系数并存。他引用了中国有关方面自己的估计。1953—1978年中国的资本边际系数为3 。18;而1956—1976年,美国的资本边际系数为3.12;日本的为3.1;前西德为3.0;英国为2.8;法国为2.9;前苏联1960—1976年为6 。6.马鲁雅马还指出,中国的投资规模与资本系数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过高的增长目标—过度投资—原材料供应紧张及工业部门的失衡—产出价格上涨—建设周期拉长—产出率下降—资本系数上升。这与中国学者的见解相同。马鲁雅马还指出,地方分权和部门分权也是投资失控的原因。地方和部门为受权投资与中央争论不休,导致重复进口、重复建设。他还引证了戈德曼和库巴的“准周期”分析以及鲍尔的学说。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投资狂热”仍在不同层次的经济实体中存在着。因而,他对中国将来是否能消除投资失控持悲观态度。
另一位日本经济学家T·希马库拉(1982年)认定中国的机器、设备进口周期与投资周期及政治周期是紧密相关的,至少,从日本向中国出口变动来看是如此。中国总进口量中机器、设备进口所占比重,大体五年出现一次高增长(1951—1952年、1956—1957年、1964—1965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五年出现一次削减进口(1954—1955年、1959—1960年、1967—1968年、1972年),这与总投资的膨胀和收缩相一致,而这一切,又与地方、部门的冲突和政治变动直接关联。希马库拉认为中国五年计划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总的看来,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并不重要的角色,而重大的政治变化往往发生在五年计划的头一年(1958年、1966年、1971年、1976年)。T·鲍尔也提出过投资者计谋的见解,与希马库拉相近。鲍尔说,投资者往往故意压低投资成本,使之被纳入计划,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今后会得到附加的财政保证的,这就是所谓的“紧扣计划”概念。希马库拉进一步阐述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周期”。他认为,在中国,权力分散与权力再集中交替出现,使工业计划、原材料分配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游移。集权导致僵硬,于是分权;分权又产生混乱,于是又重新集中。这种天平制造商的游戏反复无穷。先是1957—1958年的分权,1959—1963年重新集权;1964 年分权,1968 年集权;1970—1973 年再次分权,1974—1978年再度集权。希马库拉用中国决策体系的矛盾来解释进口周期和改革周期。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决策权力中心,有“保守者”,也有“激进者”,两者都试图争取最高“决策者”的支持。这样,“保守者”、“激进者”和“决策者”构成一种“三角游戏”,而这种三角关系形成了一种隐蔽的总周期波动的调控器。
1982年,陈储元在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专著中,专设一章“国民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其中主要依据美国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基本上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一致。他认为 1950—1976年间有三次大周期(1950—1961 年、1961—1967 年、1967—1976年),每次大周期之后又有短周期。
关于“政治周期”,陈储元和沙旺斯各自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储元强调了政治因素对经济变动的作用,他提出了“农村政治周期”和“人口政治周期”两个概念。他认为,在农业集体化、公社化运动中,有一种“充公”运动。尽管私有财产“充公”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是国家高积累的重要补充力量。例如,1958年前一年虽没有创纪录的好收成,但还是实行了大跃进,导致大涨大落。至于人口周期,他说,在最初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后,第一个控制人口出生的计划出台(1956—1957年),但大跃进很快使之夭折,马寅初受到批判,并被撤销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62年又旧话重提,但是1963年,尤其是“文革”期间,人口计划又再次偃旗息鼓。1979年又重新推出宏大的计划生育计划……马老先生90岁高龄方得昭雪。如此人为地反复胀缩,中国人口压力愈加严重。
沙旺斯认为,一方面应看到政治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应看到经济本身的作用。他承认,“政治周期”在波兰等国也可以见到,但在中国尤为突出并长期存在。毛泽东曾将其理论化:一是强调“波浪式的发展”或“螺旋式上升”的哲学;二是在文革期间认定“两条路线斗争”若干年还会再来一次。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占统治地位的财产公有制相结合,似乎构成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模式,它促成了“唯意志论”和“政治周期”。无论是为了快速工业化,还是出于国际事务的考虑,政治权力都发挥了至高无上的作用。但是,沙旺斯认为,应该更多地看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任何政治冲突都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紧密关联的;单单强调政治冲突的影响,是一种逃避态度,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应更多地注意到消费者、农民和工人在经济震荡中的影响。他指出,在中国,许多“政治周期”既是“经济周期”的结果又是后者的原因。因为激进派常常是在好的经济形式下展开攻势,而务实派或温和派则在困难成堆的时候走到前台来。
美国学者邹致庄1984年出版枟中国经济枠一书,其中专门有一节讨论中国经济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模型。书中邹致庄虽然没有直接从概念上定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波动,以及做出划分,仅就乘数—加速模型的政府投资引致的波动进行模型讨论,但是,毕竟是作为境外学者对中国的经济波动进行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