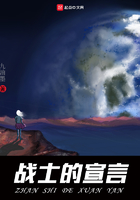要写母亲是件很难的事,总是感觉无从下笔,因为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母亲的慈祥,母亲的细致,母亲的恭俭勤良,母亲的温柔,丝丝缕缕地泛上我的心头,不知从何说起。
前天晚上回娘家,事先,给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们一家要回去。意思是要母亲准备好饭菜。每次回去之前都要这样,因为如果不提前告诉她,回到家里,即便是他们已经吃过饭了,母亲也要张罗着重新给我们做过,每次都很隆重地做至少六个菜,要父亲与老公一起喝酒。
在家,父亲是不做饭,不洗衣服的。没有刻意地分工却已是多年不变的惯例。母亲负责家务,父亲负责在外赚钱养家。父亲一人赚钱养活了我们一家五口人,使母亲与我们兄妹三人一生都衣食无忧。父亲是个称职的父亲,非常的称职。母亲是个贤惠的妻子,她的贤惠使我们一家人日子过的和和乐乐,温温暖暖的。我们都深爱并感激着我们的父母。
我与老公很多次都表示不要母亲做饭,因为在我们家不远处就有好多饭店,靠近海边,海鲜品种很多,价格也不是很贵。可是母亲总是不同意我们出去吃,她总说不喜欢饭店冰冷的氛围。她喜欢看着我们坐在她烧的暖暖的炕头,暖暖地说着家长里短,暖暖地喝着酒,品尝着她暖暖的手艺,脸上露出暖暖的笑容。
母亲做饭很好吃,这是我们家所有亲戚都公认的。我做饭也很好吃,我承袭了她的手艺,并使之发扬光大,比她做的还要可口。可是母亲总不要我插手,她总是说我工作很辛苦,每次回家总要把我按在她烧的暖暖的炕头上,老老实实地坐着与父亲唠嗑,与孩子嬉闹。我们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自己一人在里外地忙碌着转悠着,如果我非要去帮她,总会引起她很大的不安。时间长了,我只好提前几个小时告诉她我们要回家,以使她不致因时间紧显得那么匆忙。
母亲个子不高,因为年龄的关系,就胖了许多。也因为从嫁给了父亲,父亲非常疼爱漂亮而娇小的母亲,从来不要母亲下地干粗活,她的模样就没有农村妇女那样粗糙,母亲脸相细嫩白净,60多岁的人了显得比同龄人要年轻许多。而母亲也不娇惯自己,不下地干粗活,她就把家整理得有条不紊。家里的房子室内面积近200平米,爱干净的母亲自己一个人把偌大的一个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母亲对生活很细致,包括在对待外出吃饭这件事上,一来她觉得外面没有家里气氛好,二来就是觉得外面的饭菜不卫生。母亲很会调理生活,我们家里吃的小菜都是母亲亲手腌制的,口味非常的好,以至于我们家好多亲戚都吃着母亲腌制的咸菜,没了就打电话给母亲,她就会赶紧地去赶集买各种调料,腌制好,一坛坛地分送给亲戚及我们姊妹。
母亲蒸大饽饽也是一绝。每个重量我没称过,估计也有一两斤重吧。她先用酵母发一盆稀稀面引子,等引子开了再往里和面,重新将面发酵。面发酵好了后,她将发酵好的面倒在面板上,加入白糖,猪大油,并不断地往面里掺干面粉,直到面变得很硬,掐成适当的大小,挨个揉面团,柔软了后,放边上,用干净的棉布罩上。母亲在揉面团的时候总是跪在炕上,以使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面团上,是一项重的体力活。她蒸大饽饽,多数时候有父亲帮忙。等这些面团再次发酵长大后,再挨个用力地揉使它们再次变小,直到再一次发酵长大,就可以团成大饽饽了。这些团好的大饽饽再一次发酵长大,就可以将它们放入烧着开水的大锅里急火蒸。
母亲蒸的大饽饽白白亮亮,暄腾腾的,顶端挂着大红枣的香甜扑鼻的大饽饽就出笼了。
母亲蒸大饽饽一锅只能蒸四个。而每个大饽饽都足够我们全家吃几顿。
母亲在这些大饽饽上花的工夫每个都不会少于一个小时,如果说我们平时吃馒头只吃二两的话,对这饽饽,我们至少能吃四两,甚至连菜都不想吃,那实在是一种极致的味觉享受!
母亲蒸饽饽都是垫以玉米叶。
我们家地很少,种很少一点农作物,种玉米都是在很嫩的时候就掰下来,吃新鲜的玉米棒子,那样的叶子根本不能用。平时用的那些玉米叶都是母亲去帮种地大户剥玉米,只为了获取玉米叶。母亲在剥玉米的时候,很细致地把里层白而软的叶子剥下来,回家后再一张张地叠好,穿成串,挂起来晾干。每年收玉米的季节她都以这种方式弄很多串玉米叶,干了后用大而干净的塑料袋套上封扎好,分送给我们家城里的亲戚。
我在自己家做包子、蒸馒头都是用母亲给的玉米叶,从来不用纱布垫底,这样蒸出来的面点比用纱布垫底要清香很多,且不塌底。
每年的冬春季节,母亲都喜欢到山里挖荠菜,那时的荠菜叶子很少,根部肥壮,吃起来有嚼头,很嫩很香。挖回家后,她要费很多的时间,把荠菜挨个摘去死叶碎根,然后在冰冷的水里洗干净,用开水烫好,放冰柜冻好。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她就可以包饺子吃给我们吃,剩下的就装起来给我们带回家。
母亲头上有了白发了,丝丝缕缕的白发间杂在她的头上。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母亲在一盏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衣服的情景。那时候,她头发黑黑的,浓密而柔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她中指套着顶针,大拇指与食指紧紧地捏着细细的绣花针,不时地在她的发上摩擦几下。问她,她说这样针在穿布的时候就不会发涩。记得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母亲自己裁剪,自己缝制的。母亲的针线功夫很好,街坊邻居很多不会做针线功夫的女人都来找母亲帮忙,也因此,母亲在村里的人缘与口碑就很好。她的手纤细而灵巧,小时候我们穿着她缝制的红条绒布鞋走在街上,能吸引很多羡慕的目光。每当穿上新鞋子,我们都是那么的骄傲。
每年的大年三十,我们兄妹三人在放完鞭炮,吃完饺子后,就睡下了,父亲母亲还在忙活着过年的一干事务。到了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我们会被挨个地叫醒,闻着满屋子的香气,我们就知道可以吃猪头肉了,那个时刻肯定是母亲刚将猪头肉煮好,刚掀开锅盖的时候。当我们清醒过来,从被窝里坐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三碗肥肥的、香香的猪头肉放在我们面前,开始几口我们会吃得很香,不要多久我们就会吃不下去了,再躺下接着睡觉。
我自小就体质弱,冬天里手脚常常冻得冰凉。白天与母亲一起,她就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手里。那时的棉裤都是左边开口的,有时候她就把我冰凉的小手从左边开口处放进她棉裤里边,贴着她的肉取暖。晚上睡觉,我都是与母亲一个被窝,与她倒头睡,她总是把我冰凉的小脚紧紧地抱在她的怀里,在她暖暖的怀里,我很快地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到如今,她拉到我的手,还是会疼爱地试图把我抱在怀里取暖,只是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不好意思再这样与她亲近了。
虽然父亲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家庭条件,母亲也总是勤俭持家。她精打细算地为父亲,为儿女操持这个家。小的时候,母亲做饭总是两样的,一样是我与父亲的,一样是她与弟弟妹妹的。因为父亲是家里的劳动力,又因为我体质弱,所以吃饭时,好的东西总是紧着我与父亲,然后是弟弟妹妹,然后才是母亲。在我们家,吃饭是不允许浪费的,碗里绝对不允许有剩余的米粒浪费,包括我的女儿,自小跟着姥姥,即使平时浪费很多的东西,在吃饭的时候也养成了碗里不能剩米的习惯。
到现在,我们回家,只想到父亲爱吃什么,偶尔想起给母亲带点东西,也只是想给母亲买什么漂亮的衣服,在下意识里,似乎从来没有想到母亲爱吃什么。仔细想想,还真的不知道母亲究竟爱吃什么东西。想来,家里的剩菜剩饭似乎都是母亲吃了。
母亲家庭条件很好,虽不是大家闺秀,也能算上是小家碧玉。外公的阶级成分是上中农,母亲是她的小女儿,深得外公喜爱。在家里没有受过什么苦,外公不舍得嫁女儿,于是父亲倒插门进入了外公家。父亲家里兄弟姊妹多,家庭条件很不好,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给母亲,只带给了母亲深深的疼爱,带给母亲一辈子的幸福与满足。母亲没有因为父亲穷而与外公一起欺负父亲,在外公面前她处处护着我的父亲,护着他一点可怜的自尊。到后来,母亲与父亲从外公家里搬回了奶奶村,没带一砖一瓦,与奶奶一起住在三间破房子里。在三年的时间里,父亲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去石头窝打石头,硬是靠着自己的双手为我们娘四个盖起了能够挡风遮雨的四间大瓦房。
后来父亲做村支书,母亲仍是平和的,她一如既往地帮助乡邻。后来父亲自己经商做生意,钱多了,母亲仍然吃着我们的剩饭剩菜,仍然不舍得丢掉一粒米。
收拾起零碎的记忆,具体的还是不知道怎么表述母亲,母亲对于我,只是疼爱,只是慈爱,只是温柔的代名词,她是和风细雨,她就是冬天里那床厚实的棉被,她就是一个家。哦,我知道怎么形容母亲了,母亲就是我的家,就是我们兄妹与父亲的家,无论我们走多远,能够使我们栖身的,能够给我们温暖的永远都是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