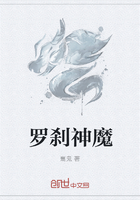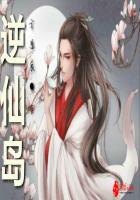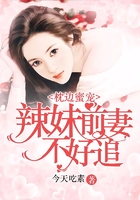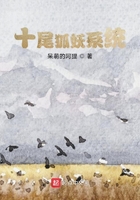有一天,似乎因为翻找什么东西,在一本书里发现了自己插队时的一张照片:我穿着一件破烂的棉袄,腰里系一根柴草绳,站在一棵盛开着红色花朵的桃树前,更远的背景是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前方,则是烟笼雾绕的峡谷,我就在这里插队落户。那时我刚刚20出头,却显得瘦弱苍老,黑黑的脸上胡子拉渣,头发蓬乱得必须用手压住才略显驯顺。
我问女儿认识不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她摇头。
我觉得挺好玩,于是把自己插队时的影集翻出来给她看,告诉她,那个形如叫花子的人,就是她的爸爸。她笑起来:“您过去是这样啊!瞧你们穿的,都是什么呀!”
女儿这一代,已经非常讲究穿戴。服饰讲究品牌、精美、时尚,瞧不上“过景”的衣裤,更别提穿打补丁的服装了。
想想这一切是挺有意思的。谁不喜欢穿戴得整整齐齐呢?但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环境制约着你:布票是有限的,吃“大锅饭”的人们收入是低微的。何况那个时代把讲究穿戴看成追求“资产阶级享乐”的腐朽观念。“文革”中,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不是把上街剪又细又紧的包腿裤作为“破四旧”的内容之一吗?所以当年人们大多穿得越破越好,似乎这样就更像无产阶级。而在“文革”中,什么服装也不如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更美。因为它已是阶级成分、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等一系列荣耀的标志。
我并没渴求过一身绿军装。我家庭的“海外关系”跟革命军人沾不上边,但是我却凭空得到过一件军装。说来挺逗,那是1967年的盛夏,校舍变成狼烟四起的战场。我校老红卫兵和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发生了长达数月的武斗,老红卫兵据守北边的教学楼,我们则占据南边的宿舍楼。一天晚上,我们这一派发动突袭,经过激战,老红卫兵们被打得龟缩在教学楼里。第二天,看看教学楼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便戴着柳条帽,手执钢筋打就的长矛壮着胆子进入教学楼,却不见一个人影。堵住楼梯的课桌狼藉地遍布楼道,碎砖头烂瓦片和自制长矛、棍棒、皮鞭等扔得到处都是。在一间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做饭用的电炉子、煮挂面用的铝锅和“红宝书”以及大字报底稿、“文革”小报等资料都胡乱扔着,在一个堆放着肮脏被褥的两屉架子床上,我发现一件退了色的绿军装皱巴巴地扔在那里,自然,它成了我的战利品。这是件咔叽斜纹布料的绿军装,估计还不是小兵穿的,虽然已经洗得发了白,但一块补丁也没有。从此一有“外交”活动,我就穿着它招摇。
我那时在北京中学界挺活跃却不甚起眼。可这件军装一穿,尽管有些肥大,但它依然为我罩上了一层光环,那些不清楚我底细的中学生们以为我有过硬的家庭背景。有个被称为中学生“4·3”派领袖的人物,一有活动,就必然拉上我。这种活动人员的流动是很大的,一批批地不断换来新的面孔,而每次活动,常有聪明漂亮的女同学凑过来表现出愿意和我接触、深谈的意向。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颐和园的活动中,在微波荡漾着秋月的昆明湖堤岸上,一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用感慨的语调对我说:“我终于找到啦……”想想吧,我这个一向“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人,一向有些自卑的人,突然受到这样的“礼遇”,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对此,我真是既惭愧又窃笑不已,以至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再穿这件军装满处“风光”了,毕竟我并没那样令人羡慕的家庭背景。
然后是去农村插队。尽管下大田时我很少穿它干活,但毕竟它无法历久弥新,所以先是被洗得发白,然后又开始糟朽—哪怕被酸枣刺、树枝一类的东西轻轻一挑就扯个口子。被我粗针大线地缝补了几次,后来实在缝不胜缝了,就破破烂烂地穿着它劳动。一直穿得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时已经是70年代初了,军装热已消退下去。一天,我在赶集时碰见了一个同学,他穿着一件“的确凉”半透明汗衫,一些老乡跟在他后面一个劲地打量那件汗衫。“呀,玻璃汗衫呢!”一个村姑叫起来。同去赶集的女同学、男同学也都在碰见他时,不是摸摸它的质地就是问问价钱,于是他很风光,不由得我想起我最初穿那破军装时的情景。我知道,这位同学的风光,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政治内涵,我从心底不由得笑了起来。
在中国出现服饰革命以来,我的确也穿过新的衣服,甚至十分规矩的中山装,三接头皮鞋,后来又是西装领带等。但是最让我风光的就是这件我捡来的褪色军装。它让我领会的东西,胜过书本。
服装和人类比,永远在数量上占多数,多出许多倍。它们被制作,被吹嘘,被喜爱,被遗弃,被花样翻新,又被无情地淘汰。人类的文明史有多长,服装的河流就有多长。毫无疑问,服装是时代的镜子。透过人类缤纷庞杂的服饰,你能看到、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