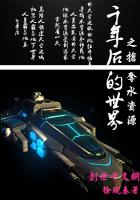顺帝至正七年,,秋,北疆。
一阵秋风吹过额尔齐斯河的水面,荡起层层涟漪。河边的草丛里,翠娥手里甩着一根小木棍,一边用木棍拨开一人高的牧草一边寻觅着甚么,还不时的张嘴大声喊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像一个神秘的天外来客一样伴在草原的浩瀚的天空上回荡着。
“桃符,桃符……”
牧女翠娥的声音传向远方,渐渐消散在地平线。而名字的主人他听到了,他睁开了眼睛。
……
……
赵养卒睁眼,怔怔的望着天上的白云,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很可悲的已经习惯了孤独。来到了这个世界已经快满十二年了,不知何时他如一只野兽一样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一个人仰躺在无垠的草原上,让高高的牧草把自己彻底掩埋,然后傻傻的看一整天的白云变幻消散。每当这个时候,世界总是会显得特别安静,感染似得,赵养卒的心也安静下来,也许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去想起记忆深处盘桓着的那些人那些事,回想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有一个叫徐牧云的人,他也许平凡,但无可否认的是真实无比的,而现在,赵养卒却只感到一切像一个虚幻的梦,只有那个女人的爱让他觉得温暖。
想着想着,赵养卒不自主的笑了起来,那笑声颇让人笑声的主人无奈,清脆的分明便是一个孩子。那偶露鳞牙的一道闪电过后,一个和谐社会下不那么优秀的青年,已是一个小名桃符的十二岁孩子了。
正在此时,一根手指带着女人的嗔怒狠狠的按在赵养卒的眉心上。赵养卒睁大了眼睛,牧女翠娥映入了自己的眼帘,代替了眼里的蓝天和白云。
翠娥蹲在赵养卒身边,呆呆的凝视着那张小脸,还有那双漆黑如墨的眼睛,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里透着说不出来的迷茫和惫懒,犹豫了很久,翠娥用长年干活磨练出的粗粗手指狠狠的戳了一下赵养卒的额头,和预料一样,桃符只是睁大眼瞅了自己一眼,没有一点惊讶。
“都不像一个孩子……”翠娥也老大不小了,却还孩子气的嘟囔着,一屁股坐在地上,颇为不满。蓝天和白云重新映入了眼帘,赵养卒却没了回忆的心境,耸了耸肩,坐了起来,他没说甚么,事实上,他能说甚么呢。想了想,赵养卒把头搭在膝盖上,“吃晚饭了吗?”
牧女翠娥突然兴奋过来,她一下子上前抱住身子小小的赵养卒,在他头上轻轻敲了一下,笑道:“今晚上家主会过来哦,夫人会做烤全羊,一想到夫人的烤全羊,翠娥姑姑这口水就要填满整个额尔齐斯河,忍不住了啊。”
像大海里蕴藏珍珠的贝壳,赵养卒随波逐浪的任由翠娥抱着摇晃着,没有一点反抗。打小,赵养卒的母亲就在赵养卒耳边重复,“桃符,日后需事翠娥姑姑如吾。”
“咳咳……”
一阵剧烈的咳嗽让牧女翠娥的手顿住了,她用力的扳过赵养卒身子,一下子脸色紧张了起来。刚才还面色如常的赵养卒此刻脸红的如同醉汉,一丝丝不正常的酡红填满了那张孩子的脸,他不停的咳嗽,在傍晚寂静的草原之上刺耳的让翠娥心肝一阵乱跳,她起身很是有一把力气的把赵养卒拉了起来,然后背在背上,手里的棍子也扔掉了,“桃符,你坚持一会儿,我去找张自在先生……”
“翠娥姑姑,放下我吧,老毛病了,没事。”在女人背上的赵养卒拍了拍女人的背,摇摇头说:“你看,现在不咳了吧,刚才姑姑不是说今晚父亲会来吗,快一个多月没见到父亲了,再不去见见,都快忘记他是男是女了。”
翠娥一个憋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她放下赵养卒,转过来亲昵的像一个没有孩子的母亲痛惜的搂紧了赵养卒:“永远不要忘了,夫人和翠娥会一直惦记您的。”
草原的落日下,一个牧女牵着一个孩子的手走出高高的牧草中,两个背影渐渐走向远方,日落之处。
……
……
二夫人杨氏也和他的儿子一样喜欢看落日,只不过赵养卒的眼睛总是望着天空,杨氏的眼睛则喜欢遥望着江南的方向,那里是她的家乡。
此刻她正在忙碌着,将一层层细密的胡椒粉和孜然撒在铁架子上那只全羊身上,微黄的羊腿上顿时微微泛红,一阵香味油然而生。刺鼻的胡椒粉还是让七夫人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喷嚏的声音很轻很低,一如女人的优雅,低调却难以掩饰的住,仿佛藏在深闺的佳人,世人不知也会有明月来亲的。
两个细碎的脚步声在帐篷外响起,听着脚步声,二夫人矜持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帐篷被掀开了,最先进帐篷的是牧女翠娥,“夫人。”翠娥乖巧的跪坐到二夫人身边,不容分说的接过她手里的盘子,接替了女人的工作。
“桃符怎么还不进来?”二夫人如一个名门闺秀一样正襟危坐,对着帐篷外问道,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似风,却透着一股威严,那是母亲特有的威严,隐隐间有着斥责的味道。帐篷外先是一阵安静,然后才传来一个孩子文静的声音,文静的也不像一个生长在风吹雨打草原上的孩子,而恍如江南烟雨巷里的少年书生,“桃符怕母亲责骂。”
二夫人面色如常,她静静的吐出两个字,“进来。”
帐篷外手足无措的赵养卒心中唉声叹气的摇摇头,掀开帐篷帘子。
入目的是一个跪坐的女人,女人很美,像一朵妖艳在北疆的紫兰花,微颦的眉头柔柔软软的,白皙娇嫩的皮肤哪怕已经过了十二年也没有一丝粗糙,似乎塞外干燥寒凉的风特地放过了这个江南娇娇女,只是那双仰视赵养卒的眼神却早已经冷了下来,那冷意中赵养卒看不透是甚么。
“又一个人待着去了?”七夫人冷冷的瞪了儿子一眼,却发现后者虽然面色恭谨,却还是没说话,估摸着等自己说完后,还是我行我素,私下里更是对翠娥说这叫不走寻常路,面对这个儿子,杨氏真是不知该怎么教了,“你应该多几个小伙伴,别老是一个人待着,娘说了那么多次,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
“等他们再大点,和他们在一起没意思,还不如一个人待着能想些事情。”赵养卒低着头辩解。
“桃符,”二夫人很认真的说,“你还是一个孩子。”
“哦。”赵养卒依然低着头,不以为然的应承着。
看着对面跪坐的儿子,七夫人无可奈何的一笑。对于这个儿子,她实在不知该怎么说了,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可以说话了,但是却很少说,自打能睁开眼能看人的时候,是坚决不喝自己这个娘亲的奶,不仅不喝自己的也不喝别人的,后来没办法只能用牛羊的奶去喂他。后来稍稍长大一点,也不像别的孩子一样和着尿玩泥巴,总是一个人骑着他那头小黑马跑到帐篷对面高高的草坡上,抱着膝盖仰望星空。你说他孤僻呢,每每与人聊天,又总是语出妙语,逗得自己这个为娘的也甚是开心,可就是不爱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仅仅有的两个伴当,也是受人轻视的庶子。这样下去总是一个人游离在外,成天与其他庶子混在一起,二夫人不知道,他这个“少爷”还会当多久。
“今晚你父亲会过来!”二夫人从牙关里恨恨的挤出这两个字,捏紧了两只拳头瞪着儿子。这小家伙就怕他父亲,只可惜,那个可恶的男人一个月只来一次。
恍若未闻,赵养卒岿然不动,充分表达了对那个一月只来一次如同大姨妈的父亲的不屑和本身超乎寻常的成熟。
二夫人看着神色漠漠的儿子,突然笑了起来,像在风中摇曳一样,笑的花枝乱颤起来,赵养卒依然八风不动,他知道自己这个母亲可不能看表面,表面上活脱脱的一个大家闺秀,内心里却像是一个藏着恶魔尾巴的少女,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少再能看见那象征着充满灵气、捉弄、古怪的恶魔尾巴了,多的是一个母亲的坚强。但总有那么比较少有的情况,母亲会心性大变,每当这个时候,赵养卒总是额外的小心。
“你父亲过来是为了和我商量给你娶亲的事。”
赵养卒一身蒙古袍子,身上还有几根枯萎的牧草,他百无聊赖的像捉虱子一样剃掉牧草,粗声粗气的“哦”了一声就没甚么反应了,信你才怪。
“不信?”
二夫人突然兴趣大加,草原太寂寞了,除了自己想方设法弄来的几本书她实在太无聊了,偶尔逗逗自己这个古怪的儿子也是一件乐趣,特别是七夫人想知道当自己儿子知道自己不是逗他时,那表情的一定有趣的紧。
二夫人毕竟年才二十八啊,在后世,多少白领御姐在这个年纪,还在满不在乎高傲的打着光棍。
“母亲的话总是正确的,母亲的话总是不容置疑,母亲叫桃符做的事桃符一定会做。”赵养卒重复着每天早晨母亲叫他必须背诵的三句话,不知为何每次背诵这三句话时,他总会想起传销组织的女头目,自己则是那可怜的被传销人物。
二夫人一阵无语,她回头看了看在旁边对此视若无睹安静烤羊的翠娥,”想笑就笑?“
“嗬嗬嗬……“翠娥终于憋不住了,歪倒在一旁没什个形象的大笑,难怪这么大了,还嫁不出去呢。二夫人再看赵养卒,发现儿子正对着烤全羊发呆,一阵龇牙咧嘴的,不时的还吞一下吐沫,那种想扑上去大嚼一顿的样子,让二夫人一阵好笑后,心头泛起淡淡的心酸。
“想吃就吃吧。”
撕下不大不小金黄色的一块羊腿肉,二夫人一脸好笑的递过去,赵养卒本想豪言壮语然后很谦虚的说等父亲来了大家一起吃,让他也体会一下自己这个小妾生的儿子也是有孝心的,不过嗅着金黄色羊腿不断散发的肉香味,就只是象征性的冲母亲矜持的笑笑,很优雅的抢过羊腿肉,嗷呜一下,大嚼一通。一边吃还不忘拍拍母亲的马屁,竖起大拇指。
女人是个情感动物,母亲也不例外。
二夫人很欣慰,也就很自然把这种在她眼里很失礼的事悄然忘却,看着儿子吃的额头、鼻梁、嘴唇都是汗水,映着毡包里的灯火,晶莹透亮,不由露出一阵会心的温柔。用干净的白色棉布,轻柔的擦拭,“慢点,没人和你抢。”
“都怪娘亲做的太好吃了。”
赵养卒一边吃一边夸,二夫人的笑意越发的浓了。正说着,突然一阵咳嗽在帐篷外响起,赵养卒一惊,本能的放下了爱不释手的羊肉,七夫人温柔的笑意也僵在脸上。歪倒在一边的牧女翠娥下意识的撑起身子挪到了角落,帐篷里的气氛猛地凝固起来。
然后,帐篷倏然被掀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