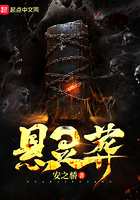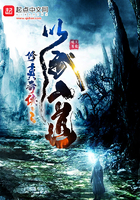有人在千华苑拿此事调侃。那天是十一月初五,安常大人穿过大厅上厢房去,厅子里故作知情的人炫耀道:“你们可知道这一位最近做了什么,天大的事,想将一个女人送到陛下身边,可不是,亲自调教的,迷人是很迷人的,哪成得了啊……”
这件不知真虚的新闻立即沸沸扬扬地传遍千华苑。世上的人都有一颗无聊的心,以诽谤高高在上的人为消遣,这是真理,记述丰功伟绩的事情是不需要他们干的。安常大人身陷舆论中心,再也没有往日的隐忍肚量,走出千华苑大门的档口突然回头,问住那个尚在说话的人,“你说什么?”
那人突遭谪问,一时不知应对,红着脸吱唔道:“我说什么……关你何事?”
安常大人逼前一步,气势好似严酷的弑杀者,将他手上的酒盏打到了地上,“你说什么?”他重复问道,看上去是不会罢休的。在场的人都紧张而兴奋地观望着,想安常大人向来不屑理会此类流言蜚语,今日较真不知道是因为他酒醉得厉害还是真有其事,只是这个倒霉的人也太可怜,非撞在刀尖上。
“这个倒霉的人”乃当今文正大人之子林子商,也是初出茅庐不谙人事的少年才俊。他现下正处在上不去下不来的境地——硬着脖子与安常大人争执,那无异于自取灭亡,立即软下来求饶,也太有失脸面与尊严。他家世代为官,为世人敬重,敞开来讲,何惧安常大人,闹臭了也不至于危及生命,权衡之下,颜面最重。
于是林子商眉毛一挑,装疯卖傻道:“我哪有讲什么,不就是戏文里唱的,吕不韦官拜丞相一出么……”
林子商话没说尽,人们就爆发出一声惊呼,因为安常大人出手揍了林子商一拳,两人扭打在地上。一时没人拉架,围着看好戏,百年一遇的好戏,这比台上唱的戏可好看一万倍。
奇善从外头冲进来,拨开人群,死死地拉住林子商,把他推出人群,随后四五个侍卫闯进来,牢牢护住安常大人。
千华苑主事口里嚷着死罪奔现,他见安常大人衣衫不整地坐在地上,脚下发软即跪倒了,“大人,您没事儿吧,这可怎么说,如何闹到这地步?”
奇善去扶主子,安常大人自顾站了起来,冷戾地说:“这个破园子能经营下去?哼,该换老板了。”说完即离去。几个侍卫冷眼逡巡一圈,挥刀将大厅里摆设一概敲碎了。千华苑主事噤声不敢反抗,直掉眼泪,难料今日遭此横祸。
苏信春入宫,详细情形在此难做赘述。这个女子心性慧黠,即便现在年纪轻,满眼满心皆是旧情旧爱,能一剑斩断就可以看出她的强势性子。
甫进宫时她心如死灰,勉强应付帝恩,在宫苑里深居简出,各妃处也是推病无心交际,一心认为此生已走到尽头。唯一觉得心思活着即是午夜梦回,望见安常府小公子的时候。
这一日用过晚膳,苏信春知道元统帝在储庆宫歇下,便更衣,在**花苑内散心。明月初上,皎洁如玉,苏信春长时望着它,也不知哪来的风,浸得满身冰凉。
“娘娘,披上褂子可好?”亲身侍女明晓轻声轻语地站在苏信春身后,见苏信春无声无息的,便轻轻给她罩上。
苏信春倚着梨树长站,宫闱外起了更。明晓想浸着露水要生病,就劝了一句,苏信春回转身体,踏着鹅卵石向内殿走去。主仆二人转过假山,忽看见前面两个太监缓缓行来,在前的一个手里提着琉璃瓦宫灯。两人竟毫无避让之意,直直行来,明晓快走几步叫道:“娘娘贵驾,怎么不知礼节,这样横冲直撞着来?”
两位侍人停下脚步,在后一个走至前来,苏信春一望,差点失声叫出来。明晓伶俐,立即打量四处,把内殿的人都支出去。苏信春这才领着那个人进来。
安常大人站在门边上,看苏信春一如从前那样斟下茶。“您……请喝茶。”苏信春端着茶盏,递在胸前。安常大人走过去,静静望了一会儿苏信春,便接了茶,送到唇边。唇齿碰到瓷盏,他的双眼下阖,眼泪便漱然流下。他的双手在颤抖,却细细地捧着茶盏,将茶慢慢饮尽,这样,放下杯子,用袖子拭了拭嘴巴。
“弥宣可好?”“已牙牙学语。”苏信春再也无语,沉默地站着。她哪里知道与他分别并不摧肝断肠,现如今相对而立,四目相望才是生不如死。
安常大人垂下头,右手捏着茶杯,叹了口气,然后局促不安地打量手中的杯子,好像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把它搁下了。
----------------------------------------------------------------------------
安常大人无可奈何地抬脚离去,苏信春紧跟了两步,顿在原地,看着他走向门口。启开门,他站了一会儿,复关上,转过身来。
“你到底是为什么要进宫来,要做帝王妃?你给我一句话,你说什么,我都信。”
苏信春一下子软下来,跌坐在椅子上,泪如泉涌。她咬着牙,不发一语。
安常大人走上前,托起她的面庞,对着她的眼睛,字字泣血,“世上再难找你这样狠心的女人了!”
苏信春嘤嘤哭泣,抚摸安常大人的额、眉、鼻梁、唇、下颚。安常大人倏然将她拥进怀里,拼尽全力抱住她,“信春,跟我走吧,就现在,天涯海角,任你想去哪里,我都跟你去。”
苏信春脸色惨白,喃喃道:“大人,我多想回到为您跳舞的时候,我永世难忘您折下一株梨花戴在我的发间。那时候,只有您和我,您和我。我们就停在那里,大人……”
“我们能回去的,信春。我知道你厌烦我的无趣才委屈自己进宫来,现下,我就带你回去,你喜欢跳舞我就给你伴乐……我说到做到……”
苏信春在他怀中,听到这里,心念如千军万马过境一样,翻覆到安常大人这边,想就此丢开一切,和他远走高飞。她把嘴唇也咬破了,推开安常大人,对他说:“若在三年前您这样说,我无怨无悔和您同生共死。但如今,我是册封的娘娘,女人一辈子不过如此,您拿什么让我心甘情愿再跟着您?”
安常大人不可置信地僵立住,盯视苏信春,盯视着她的花容月貌,久久才身形一晃,垂下眼睑,黯淡地坐了下去。
“你何必说这样的话伤我的心伤你的心呢,你对我怎样我哪里不清楚。今夜我也是孤注一掷,让你明白我的心。我告诉你,我可以与你共生死,却难独活。”他绝望地流下眼泪,声音像夏末无知的鸟儿一样飘渺不定。这个人是漂洋过海来的,有不顾一切的勇气,有蔑视生死的深情,有让苏信春心动的爱情。他抓住她的手,绝然道:“信春,我们从这儿离开,你,我,弥宣,天下无论去哪儿,只要我们在一起,行不行?你点头,我们就走。”
苏信春心内一软,跪到地上去与他面面相对,犹如当初为他跳第一场舞那样眉目情深,且笑且悲,竟鬼使神差地说:“大人,信春愿意和您走,您带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