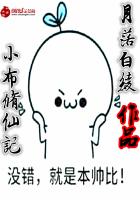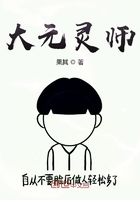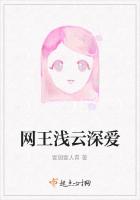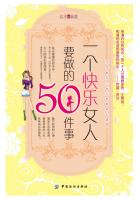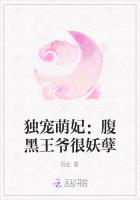就在夏宫接近竣工的时候,路过一位外来的天竺僧人。
天竺佛教在中兴时期便已经传入中土大陆,只不过那个时候依旧是儒家的天下,到了近兴初期时期,才是佛教在中土大陆的兴盛时期。
佛寺在中原大量出现,中土大陆信佛之人不断增加,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甚至一些儒生,都开始信佛。僧尼十余万,甚至到了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程度。足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信佛人数之庞大。
当时的各朝君主,更加支持佛教发展。
因为十六国中很多统治者是西域少数民族,本身就是蛮夷之人,以打猎为生,没有什么自己的文化,他们入主中原后,跟拥有上千年儒家文化的汉人相比,内心存在一种自卑感。
因此对同为外传而来的佛教产生了一种亲切感,而且恰巧佛教的主张有利于他们用来糅化人心,他们就大力支持佛教发展,广建佛寺,使佛教发展到了极高的高度。
佛教,自然是发源于天竺。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经常会有从天竺而来的得道高僧,受君王的盛情邀请,来中土弘扬佛法,普度众生。
从天竺到中土大陆,吐谷浑便是必经之地,只不过伏俟城的位置没有在官道上,又因为被山包环绕,也很少有僧人从这里经过。
但那位天竺高僧似乎是迷了路,无意间来到了这里,站在一座小山包上,看到正在赶工修建的王城,驻足良久,然后他深不可测的眼睛朝向天空,在渺渺茫茫之中,他似乎见到了什么,不肯离去。
天竺高僧衣着破烂,骨瘦如柴,可以看出,一路上,吃了不少的苦,但这僧人却神情清逸,丝毫没有半点的不情愿,反而有一种超然于世外的神秘感,
能够在荒漠中孑然独行,这个天竺僧人,绝不简单。
好久,天竺高僧才回过神来,急匆匆,一路小跑,直接进入王城,到达夏宫的跟前,拦住那些正在施工的工匠们,嘴里叽里呱啦的不知道说着什么。
那些个工匠哪里见过什么得道高僧,以为又是一个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根本不理不睬,依旧做着自己的事。
但天竺高僧突然闯入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吐谷浑王的耳朵里。
虽然吐谷浑人信仰萨满,与佛教没有一丝关联,但宗教与宗教之间,并无什么矛盾,反而有一种无形的相互尊重,彼此坦诚。
视罴亲自来到夏宫处,迎接那位天竺高僧。
天竺高僧看出视罴的身份,连忙走到视罴的跟前,嘴里依旧不停地说着什么,边说边比划,一会儿指了指正在修建的夏宫,两只手合拢在一起,做一个圆球状,然后再突然分开,像是一个花骨朵,渐渐绽放。
吐谷浑王虽然听不懂那天竺高僧说了些什么,但是高僧比划的手势却看得明明白白,连连点头。
对对对,大师说的对,本王就是这样想的,这里四面环山,层层环绕,就像一朵花一般,这座城池正好被四周的花瓣包围,易守难攻,绝佳的地理位置。
但随即,天竺高僧竖起食指,环顾着四周的小山丘,绕了一圈,然后又将双手合拢起来,紧紧地扣在了一起,如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天竺高僧的双手往下压,一直压倒膝盖处,而此时天竺高僧也作出痛苦的表情,似乎是承受不住双手被下压的力量。
吐谷浑王原本自豪骄傲的表情顿时间化为乌有,嘴角绷着,已经有汗从头皮析出来,大气也不敢喘,浑身的肉都紧紧的硬硬的。
天竺高僧的手势,再明显不过。
此处虽然四面环山,河流经过,地势险要,按理说应该是修建城池的绝佳选择,然而事实却并非想象的那般简单。
四面环山不假,但由于入口处过于狭窄,造成了与外界的隔绝,外来的空气无法流通,进入不了城内,只得在空中集结,以摧枯拉朽之势由上而下压向整座王城,就算是城池建的再怎么坚固,也抵不过常年的风化。
虽然是河流环绕,可作为护城河,但是这里地处偏僻,周围又无村庄辅佐,纵使是建成,这王城也会成为一座孤城,从建成之日起,就走向灭亡。
更让吐谷浑王害怕的是,天竺高僧说的话,句句在理,每一句话都有根有据,并非无稽之谈。
但天竺高僧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让吐谷浑王茫然不解。
只见天竺高僧原本压在膝盖下面扣在一起的双手,缓缓上升,升至腰间,突然之间分开,挨在一起的十根手指张开,不断地颤抖,紧接着身体也跟着发抖,嘴里呜呜地低声发出不知道什么声音,让人听了一阵发麻。
接着天竺高僧用手指着即将建成的夏宫的地下,在吐谷浑王面前画一个庞然大物,朝吐谷浑王做了一个不的手势,重复地说着相同的几个字。
比划完之后,天竺高僧瞪大了双眼,做了个恐怖的表情,不管吐谷浑王有没有看懂,是否理解,就直接离开了,虽然吐谷浑王一再的挽留,但天竺高僧似乎对整座王城有所忌惮,不敢多待一刻钟。
吐谷浑王预感到了情况的不妙,虽然看不懂天竺高僧后面的动作什么意思,但那天竺高僧那眩晕的声音,以及颤抖的身体,让人惶惶不安。
这是个难以抉择的时刻。
该怎么办?
吐谷浑王从未有过的为难。
一边是自己信奉的至高无上的神,一边是外来高僧的真诚劝告,到底哪一个说的是对的。
直到此刻,才有些后悔当初作出修建王城的那个决定是有多么的鲁莽,一座王城,说得严重一些,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自己怎么就那么冒然下决定呢?
吐谷浑先祖开国至今,从未有过修建王城的打算,自然不是没有原因。
可是事到如今,该怎么继续走下去?
难道要把这即将竣工的王城弃之不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