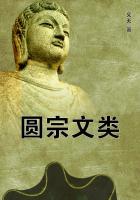二少奶说:“这个你不晓得的,他们怎肯吃一餐饭就算数呢,自然还有旁的阴谋,你怎能知道,我一定不让他们两个当面交接,你也千万不可替他们传话。少停回头她,只说君如玉不肯答应就是。这二千块和我那四千头一并拿便了。”金阿姐三言两语,又哄得二千元到手,心中不胜欢喜。这种买卖,着实大可干得。比之做洋行买办的更容易进账,无怪她数年以来,挣起十多万家私,都是从这上头来的。闲言休絮,再说次日君如玉在戏台上,留心望包厢中,果见金阿姐同着她女儿,和二少奶,以及另一年轻使女,四个人占着一间花楼。那边杨三太太同着他丈夫,和一个螟蛉儿子,三人也是一间花楼。过去几排,便是康府中一班奶奶小姐们,也是来看他戏的。花楼中鼎足三分,电光四射,煞是可观。如玉眼光回到二少奶这一边,二少奶对他觚犀微露,盈盈一笑,分明有无限情绪,都在不言中流露出来。如玉恐被旁边人瞧出痕迹,慌忙回眸他顾,及至他的戏完场,所有女客,十成中倒散其六七。如玉卸妆之后,掩到戏房门口,偷看花楼中二少奶同金阿姐母女,早已不知去向,知道他们一定先往新马路候他去了,于是自己也即出戏馆,登包车直到新马路二少奶那间小房子的门口,果见金阿姐倚闾而待。见他来了,说:“等杀我咧!你怎来得这般之慢?”
如玉说:“我并没耽搁工夫呢。”金阿姐道:“别多说闲话了,楼上还有比我等得更心焦的人呢。”于是金阿姐当先引路,如玉随在背后,登登上了楼,如玉看房间内的布置,果然华而不俗,富丽堂皇,十分考究,不觉暗暗称赞,真可谓名下无虚。因二少奶这所小房子布置华丽,外间大有名望。如玉久已听得金阿姐说起,今日始身临其地。二少奶正同金阿姐的女儿小妹,面对面横在烟榻上。他们本听得如玉上楼的声音,所以不即刻起身迎接者,无非要表示她少奶奶的身份矜贵缘故。然而自己备着小房子,请不相干的男人来家相会,身份在那里,她倒忘怀了,这都是假搭架子,拆穿不得。金阿姐见她们还横着不动,忙说:“客人来了,你们还不起来?”
二少奶闻言,始带笑坐起。小妹也随着起身。如玉对二少奶微笑点头,她二人本来没一夜不在一处,所以今天也用不着客气了,不过她们在外面的时候,有说有笑,很有话讲,此刻竟没一句话头可开谈判。金阿姐晓得这种谈判,不是人多所开得来的,惟有一男一女,两对手方才济事,自己一生靠着这上头吃饭,岂有不明白个中秘诀之理,故也不肯再做讨厌人了,叫声:“小妹,我们走罢,三太太还约着到我家里叉麻雀呢,再不回去,要给他们起疑心了。”
二少奶还叫她慢慢的走,吃了半夜点心再去不迟。金阿姐笑说:“半夜餐改日再来吃罢,今夜可有人等得不耐烦咧。”二少奶问她什么话?金阿姐答道:“我说家里有人等我呢?”其实她这句话,带着双关,二少奶也听得出,所以笑着,让她母女先走。金阿姐临行时,向如玉说:“你的包车还在外面,我教小妹顺便坐回去罢,免得停在门口,给认得的人见了触目。”如玉回言使得。她们走后,二少奶便叫如玉烟榻上坐,如玉依言,二少奶笑问:“你适才可曾听得老太婆的话么?他说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如玉笑道:“她素来就是这种脾气,喜欢说笑话的。”
二少奶看如玉说话之间,还有几分嫩气,自己却九练成钢,比他老练得多,况心爱其人已久,平时只能在戏台上看看,赌场中望望,格外的心热无比,此时孤男寡女,空房对伴,并无第三人在旁边看着,叫她如何再装腔作势得来,慌忙凑到如玉旁边,执住他的双手,假意问他吴奶奶一番事迹,然而耳鬓厮磨肌香触鼻,如玉可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早已语不成句,颠倒万千。说到后来,如玉不能讲了,二少奶奶也不愿意听了,但既不说话,究竟作何勾当,做书的明白,看书的明白。若有不明白的人,也只可让他存疑一辈子,在下不能奉告。
当夜二少奶因恐少爷回家,故而不敢整夜的宿在外面,然而也挨到东方发白,方订了后会之期而别。好在他两个都是吸烟的,肚中抽饱了福寿膏,出来也不怕风吹。二少奶本有汽车,到此不能乘坐,只可坐着黄包车回去。幸亏今儿她带着个使女来此服侍,回去也合坐一部车,两个人偎着,不致于着冷。如玉也乘坐黄包车回家。这一宵他们此地虽畅叙幽情,尽欢而散,然而金阿姐家中一班客人,已议论纷纷,疑端百出。皆因二少奶近两月来,风雨无阻,逢场必到,今天忽然不来,众人好似少了什么似的,全体为之不欢。加以他们那唯一目的君如玉,也刚在这夜不来。他平时虽也有不到之日,但今番却拣在二少奶一天上,常言说,会做贼的会防贼,彼此都觉得事有可疑,然而却没人疑心到金阿姐的身上,因她同女儿小妹二人,都在家内陪着她们,并没出去之故。内中有个陈三小姐先开口说:“奇怪了!为何花家老二,今天这时候还不来呢?”
旁边李七太太冷笑一声道:“你小姐家懂得什么,她不来自然有好地方适意去了。”说得众人都笑将起来。惟有杨三太太不声不响,一个人在旁边转了半天的念头,忽然问金阿姐说:“适才你不是同她在一间花楼内看戏么?后来她往那里去的。”金阿姐说:“她出来坐的汽车,我同小妹坐包车往别处打了岔,又往大马路买两块钱水果回来,委实不知她往那里去的,仿佛听她说到一个小姊妹家里去望病呢。”三太太点点头,又问:“你可晓得还有一个人,为什么也不来呢?”金阿姐道:“这却不知。”
三太太听说,微微一笑。这一笑金阿姐虽然老奸巨滑,也被她笑得面红耳赤起来。三太太岂有瞧不出颜色之理,当其时众人正七张八嘴,在那里说,这件事若教痴子知道,只恐更要痴得利害些呢。又有人说:“可惜不晓得他们现在哪里,不然给痴子通个风,令他打门上去闹一场,倒也有趣得很。”三太太听他们讲得,都是空头话,自己不愿意岔嘴,却假解溲为名,把金阿姐唤到小房间内,问她你究竟可晓得花老二,今夜往哪里去的?如玉又在哪里?金阿姐焉肯供认,说:“我实在不知。不过他两个奇不奇巧不巧,不先不后,偏在今夜一同不来,这桩事莫说杨三太太生疑,便是我也觉得格外的奇怪,行迹上大有可疑呢。只是他们预先在我跟前,并没露过一点口风,叫我怎能知道。当着你三太太面前,我可以赌咒的。倘使他们两个有什么事情,我知道了,罚我天火烧何如?”她的意思,来天火烧了,有保险银子赔着,又可以大获其利呢。太太却信以为真,说:“你既不知道,也是没法可施的事,何用赌这般咒呢。但这件事必须设法替我打听出来,方是道理。”金阿姐道:“这个自然。”
三太太又许她:“你若能探听出他们怎样的相叙,何时入港,约会在什么地方,一一无遗,我必定重重谢你。”这几句话又是金阿姐的进账来了,她自从招着君如玉来家之后,仿佛接到了活财神一般,烧香许愿者有人,便是天天这班女施主来叉麻雀玩意,头钱也常有百十元收入,她母女两个,好不受用。这一回三太太虽又许下愿心,金阿姐倒不放在心上,她正主却注重在二少奶的六千元谢仪。所以第二天趁早就赶到花公馆内。那时二少奶刚回家未久,通好了头,梳着条辫子,靠在沙发上,旁边放着张炕儿,上置烟盘伙,打烟的娘姨坐在小凳上,装一筒让二少奶吸一筒,看她好不忙碌。二少奶手中还夹着根纸烟,抽鸦片烟的时候停吸,放下烟枪,又接上去呼香烟了,看见金阿姐进来,对她笑笑说:“你可是来拿钱的么?来得太早咧。你不看看少爷睡在床上,还没醒么?连我吸烟都不敢床上吸,恐怕惊醒了他。少停醒来,我叫他打银行划条给你,你到上火时候来拿不迟。”金阿姐晓得二少奶在外间贴汉滥用的钱,都要向少爷那里拿。至于自己敲来瘟孙的竹杠,却要自己入袋。两方面界限划分颇严,所以也不多言,连声诺诺,回家挨到了晚饭时候再去。二少奶的划条,早已端整,六千元并没少她半个。金阿姐好不欢喜。正是:一片春情缘色动,无端笑口为钱开。欲知后事,请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