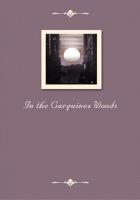次日旧学维持会开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济济一堂,人才鼎盛。就中汪晰子、钱守愚、杨九如、黄万卷等几个主脑人物,自然都晓得今天开会的宗旨,而且各存着一个希望。晰子欲做省长。万卷学部尚书。守愚的心计最工,开口并不甚奢,只求代晰子为旧学维持会会长,因他听晰子谈及欲将旧学维持会改组政党,他想目下做了会长,日后便是政党领袖,派出党费百十万任意揩油,岂不比做官更适意。还有九如,他很喜欢拿现的,故欲得一捐局差使。其余各会友的希望,都和往常开会一般,预备来扰些茶点而已。当其时晰子将签名簿翻了一翻,对守愚说:“卫运同怎还不来?他告诉我今天赶早到此的。现在会友差不多已来十分之八,只等运同一到,我们就可摇铃开会了。”守愚也说:“他不来果然奇怪,他是干事员,理该比众早到的,为甚来得独后,难道你昨天没同他接过头么?”晰子道:“岂止接头,他早已晓得咧。”
原来晰子昨儿告诉万卷说,北京有个朋友,写信给他等情,都是假的。其实却是卫运同在侦探部得来的消息,教晰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必能得北京政府的欢心,功名不难立致。因此晰子必欲等运同到场之后,方能开会。此时见他不来,会友已到不少,恐他们时候等长久了,不待开会就此散步,岂非白忙一常万卷却因昨儿会长给了他这个难题目,翻了许多书本,都没总统弃行,改做皇帝相类的文字,可以仿做。皆因万卷的笔墨,虽有名望,然而出于獭祭者为多,所以自朝至晚,埋头时习书屋,钻研故纸,他的文章,也层出不穷,现在无书可抄,不免大受其窘。足想了一天一夜,还未能完卷。此时在事务室踱来踱去,口中还哼哼哈哈,心思注在文字上,外间开会不开会,他倒并未顾着。九如巴不得早一刻开会,好早定他的终身大计,所以时时催会长摇铃开会,晰子好不着急。正在这个时候,运同来了,晰子看见他,如获异宝,正欲命守愚摇铃,运同对他连连摇手说:“会长且慢。”
晰子怔了一怔,他晓得运同来迟,必有缘故。一面运同挽着晰子进了事务室,不意万卷正在里面,大踱方步,负手长哦,见晰子进去,只当会长催他稿子来了,心中十分着急,慌忙拉一张凳在书案旁边坐了,心想字虽写不出,拿枝笔装装幌子,也是好的,免得会长怪我文思太钝,教守愚起草,自己岂不失却一个学部堂书的机会。这一面运同因有秘密话同晰子讲,见万卷坐着不动,赶又不能赶他出去,心中顿生一计,对晰子道:“会长,今天我们会中,难道不备茶点么?”晰子道:“这个焉能不备,现在还未到时候呢。”运同道:“会友们来此已久,腹中岂不饥饿,应该先用茶点,再开会才是道理。”说时指指万卷,使了一个眼色。晰子会意,即唤茶房外间摆茶点。万卷一闻此言,果然丢却纸笔,到会场上抢茶点去了。里面剩下晰子、运同二人,正好秘密谈论,运同对晰子道:“会长,我日前教你的手续,可惜已迟一步,被捷足的先得去了。”
晰子惊问此话怎讲?运同道:“你可曾看见报上,某处有个商会会长,特任道尹么?”晰子道见过的,那原是常有之理,何足为奇,本地不是也有个商会长做官的吗。大概做了商会长,已去官不远,犹之鱼化龙,雀变蛤,物理变化,一般作用,可惜我只做一个学会长,不是商会长,若做商会长,休说区区一个道尹,便国务总理,也容易得很。运同笑道:“你休夸口。老实告诉你,所说那个商会长的道尹,本来是你的,现在被他抢去了。”晰子大惊道:“怎样抢去的?”运同道:“便是那天我对你说的,北京留着一个省长,一个道尹的缺份,预备各省有名人物,打电报去赞成帝制。将此作为奖励品,好引起世人升官发财的念头,不敢反对帝制。这消息大约也被那商会长得了去,所以先我们一脚,打了封劝进电报,北京政府便把这道尹赏了他。你想倘使这封电报,是你先打,那道尹岂非也是你的么!现在可被他夺去了。”
晰子道:“那有何妨,你不是说有一个道尹缺,一个省长缺吗?目下道尹缺,虽已被他得去,但那省长缺,还未有受主。况道尹同省长比,也是省长强,自然我们宁弃道尹,而得省长了。”运同笑道:“你倒说得好一厢情愿,不怕你动气的话,你旧学维持会会长身份,怎及得商会长贵高,他以商会长之尊,所得亦不过一个道尹,你一介书生,反欲跳出他头上,猎取省长,劝君休想。倘使他先入的得了省长,也许你还有道尹的希望。现在我看你虽打电报,也是枉然的,还不如省这几块钱,待日后有别的机会,我再通知你罢。”
晰子听说,宛如当顶门浇下一桶冷水,四肢都凉透了,说:“运同,你不能这样寻我开心,我为这件事,赔了脚步,费了口舌不算,还丢掉好些零用使费,方能今天召集全体会员,开这个特别大会。现在照你说话,教我打消这件事。你开口闭口,只任着两片嘴唇皮翻上翻下,原甚容易,但不想想教我怎生下台?而且今日召集的是全体会员,非同小可,我身为会长,岂能无缘无故招呼他们来了,又不明不白打发他们走。犹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般,日后本会的通告,还有什么信用!你这个烂污可把我撒大了。”运同十分抱歉,说:“会长,你也不能怪我。这件事一半也是你自误的。你若在我告诉你那话儿的时候,就打电报,可就赶在别人之前了,都为你要顾全什么手续,必须全体会员通过,以致耽搁下来。依我心思,会长便有借用全体名义的权力,何须会友过问。所说那商会长,大约也未必得他们会友的同意,一定是盗用名义出的电报,现在做了道尹,众会友还愁拍马屁拍他不上,哪个敢再同他理论前头的手续呢!”
晰子闻言,低头无语。运同安慰他道:“会长休得灰心,我看北方这件事,也未必一定干得下,因南边反对的很多,所以他们至今还不敢实行。此时运动各方面赞成,把官爵当萝卜青菜一般,任意送人,也为这个缘故。倘使运动无效,反对的仍占多数,说不定依旧要取消的,那时这班劝进所得的官儿,还有甚面目见人。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中也有点儿出入,会长以为何如?”晰子闻言,猛道:“有了!这件事既与我等没有利益,我们何不索兴破坏他,也打一个反对帝制的电报,一则社会上可以出出风头,二则对于这许多会友也有一个交待。老卫你看好不好?”运同道:“随你会长大裁罢。”晰子主意决定,出了事务室,见几盆茶点早已抢空,守愚手中还剩半块鸡蛋糕,因他牙齿已有大半脱落,吃什么也比别人烦难下咽几分,深恐受着损失,取蛋糕的时候,手指上头明白,多拿了两个,故而别人的吃完了,他还独有盈余,此时一个人受用,好不适意。晰子见了他,忙说:“老钱,快摇铃罢,我们开会咧。”
守愚闻言,也不答应,因他口中塞满着蛋糕。要答应也不能开口,却急急跑过去,取铃在手,一阵乱摇,众会友纷纷入座。晰子上了演说台,他今天本来是预备演说赞成帝制的,此刻临时改变,幸亏他是大演说家,没几天前头也曾在别处会场上演说过帝制问题,极口反对,现在只须抄一抄老文章,已说得天花乱坠。众会友掌声不绝,却把黄万卷、钱守愚、杨九如等几位弄得如坠五里雾中,莫明其妙。听晰子在演说台上,倡议发电进京,反对帝制,诸位赞成的请举手,不消说得,众会友吃了他的茶点,那举手的义务,自然也只得尽他一荆手续既毕,晰子下了演台。本来九如、守愚等也预备演说帝制为立国之本,此时被晰子平空竖起反对的大旗,倒弄得他们没人再敢上台,跟了晰子进了事务室,纷纷向他责问,会长因何前言不对后语?晰子不慌不忙对他们一阵冷笑道:“这是我试试你们的。我晓你们几个人头脑很旧,虽做了共和国民,还未能忘怀君主,所以我特地设一个反面文章,试验你们的心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们都是利禄薰心,一闻有高官厚禄,竟不顾世界大势,倒转去附从他们一班毫无心肝的官僚,岂不可羞,实在可叹。”
众人听了,都红涨满面。万卷却窃喜幸亏文章不曾完篇,不然岂非白用心思么。守愚、九如都自觉无颜,溜出事务室。万卷也想滑脚,晰子止住道:“老黄且慢,现在请你草一张反对帝制的电报,大约比那个容易了。”万卷因昨儿受了晰子的戏弄,心中颇不情愿,无如自己有把柄在他手内,不敢不依,好在反对电天天报上登的很多,也用不着套什么陈情表、出师表,寥寥数语,一挥而就。晰子原不过借此下台之意,看了也没甚扳谈,摸出几块钱,打发茶房往电报局去。此时会场上一班会友,因茶点业已吃过,晓得没甚别的指望,会长落台,他们也一哄而散。万卷问过晰子无甚别事,也自回家去,晰子却因茶房打电报还有几角找头,恐被他揩油,故而必欲等他回来,算清账再走。一个人闷坐之下,想起数日欢心,尽成泡影,不免暗恨运同。又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大约我命中不该做官,所以已有好几次,功败垂成,可知天定确可胜人,强求无益。想到这里,未免怨命。又恨祖宗不曾积德,所以子孙无福作官,不能够光宗耀祖,也许是坟上风水不佳,明天还得请教堪舆先生择一块佳壤,将父母的棺木迁一迁方好。不一时茶房回来,晰子收了找头,回转家中,却值他女儿如玉在家请客,一班女同学都聚在他客堂上,莺声燕语,热闹异常。见晰子进来,有几个陌生的,纷向厢房中躲避。还有几个见过晰子的,使上前招呼。晰子见了这班人,心中老大不赞成。因他想起黄老夫子那件事,觉女学堂中有点儿不堪设想。况自己女儿,又是个未婚守节的节妇,带有数万金遗产关系,在此横流滚滚之中,倘有差池,不但名誉坠地,还恐财产上发生交涉,这岂是儿戏之事。古人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儿何必十二分通文达理,一念及此,便欲令如玉脱离学堂,不必再读书了。进去同老妻裘氏商量,裘氏也是古派人,听了亦颇赞成。等客人散后,老夫妻两个,对女儿说:“你读书已好多年了,我们原不是预备将来靠教书吃饭的。你今年读了半年,往后也不必再读书咧。”
如玉惊问爹娘为何教我不必读书,我学堂中再过一年,便可毕业,我们辛辛苦苦的读这几年书,也无非为想一张毕业文凭,怎的只一年工夫,差不多文凭就好到手了,你们忽教我不必再读,这是为何呢?裘氏没回答,晰子便细细将黄老夫子在女学堂中闹的这件事,讲给他女儿听。如玉听了,怫然不悦道:“爹爹这句话是你错了。常言人有几种人,物有几等物,你怎好因一个人抹煞全体。古云:知子莫若父。女儿的脾气,难道爹爹还不知道。当初志敏死的时候,女儿情甘守志不嫁,说句不堪话,女儿又没过梁家的门,要嫁人尽管改嫁,望门寡能有几个肯守节的?我既已守了节,自然始终如一,难道还肯缩转去干什么没廉耻的勾当么!爹爹你不该错疑女儿。”说话时候眼圈红了,眼泪似乎要淌出来模样。裘氏见了,疼得了不得,就此不敢附从丈夫劝女儿废学,却帮着女儿抱怨晰子道:“对啊!女儿说话是不错的,她既肯守节不嫁,难道还愁有甚别的差池不成!这是你老糊涂,空口白嚼,惹女儿生气,俗语说坐得正立得稳,哪怕和尚道士合板凳。学堂中读书,更不相干了。女儿休听他的话,自己尽去读书,等到毕业之后,你若爱进别的学堂,不妨念一辈子,有娘替你做主,不关老头子之事。本来子从父教,女从母教,是他多管闲事的,女儿休得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