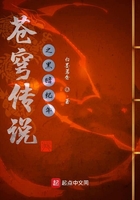“况且这呼……侍卫,玉体胎境的侍卫,嘿嘿……”
驽部一声嘲笑,那面上鄙夷之色,话语虽未尽,内中之意却已是不言而喻。他懒得再看那呆傻憨直的黑熊呼,反而皱眉扫视在场这二十二位近身护卫,那暴吼的语气近乎叱责。
“各位近身侍卫,均是身境的高手,莫非也愿雌伏在这玉体胎境的呼侍卫手下么?这等耻辱,你等便真的甘愿忍受?”
这驽部倒真是个狠角色,此番被罴招惹起来,竟是将场中无论身份,上至罴这等得势少主,甚或呼这原近身侍卫,还是余下二十二位近身护卫,一个不落皆尽骂了个遍。
如此嚣张横行,便连呼延自觉已是胆大妄为之辈,此时亦是看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比较罴或近身侍卫,这驽部说起呼延时,倒是寡言少语,听着倒似他不愿太过招惹呼延,其实却是看之不起,不屑在呼延这等小角色身上耗费口舌而已。
往日无事,这驽部张扬些也就罢了,顾忌到他那身后背景,诸位近身侍卫能忍便也就忍了。但今日呼侍卫归来,大喜之时却来只苍蝇呱噪,饶是众熊脾性算好,也被惹得大怒,皆尽朝驽部怒目而视。
人界俗话说得好,即便是泥菩萨也有三分火气,更何况是以脾性暴烈著称的战熊。那本是先锋军中一军主的黑熊,原本统御万熊,是何等的大权在握意气风发,随后惨遇大败,唯有投靠先锋军的统领罴少主,这大起大落的滋味,实在是百味陈杂。幸遇明主,这罴少主重情重义善待他们,让他们做了近身护卫,又得见呼延这值得结交的战熊,这才让他心情渐佳。
奈何随后情势突变,大军再次覆灭,掩护罴少主侥幸逃脱,呼延却不见了踪迹,其后这四年之事……不提也罢,只可谓命途多舛,一言难尽。
本就压抑怒气,待听得驽部如此不堪的漫骂,一众近身侍卫哪能容得他这般挑衅,内中资历最高的原先锋军军主,名为沽巨的战熊最先按耐不住,昂然跨到驽部面前,四目瞪视之间,冷笑低吼道:“呼侍卫虽说修为尚弱,但总好过那些坏到骨子里的熊货,每日里只顾得挑拨离间,即便是身识身境的修为,我等也是看不不起!
“这修为境界总能提升,脾性却是难改喽!”有沽巨军主率先开了骂口,其余近身侍卫自然响应,接着话头继续往下暗讽。
“哈!沽巨军主,粟奕千主说的是!我等还真是喜欢呼侍卫,他那脾性正对我夫袭的口味!”
“夫袭千主,照你这么说,若呼侍卫是头母熊,你便要将他带回家去了吧?”
不知是谁说的俏皮话,引得众熊哄然大笑,那千主夫袭更是捂肚爆笑,重重拍打着呼延肩头,尚有兴致促狭道:“若呼侍卫真是头母熊,讨回家去那是我夫袭的福气,哈哈!若家里真能有一头如此对脾气的母熊,我这日子便舒坦啦!”
呼延此时倒也是好脾气,满脸笑吟吟,任由他们调笑、打趣。
这却只是开始,当然接下去那些个冷嘲热讽,却与呼延再无干系,均是朝那“驽部侍卫”而去,听得呼延咧嘴大笑,对这群骂得有趣的黑熊更增赞赏。
“呼侍卫那是无需多说!我等兄弟皆尽认他号令,听得他的絮叨或帮些小忙,起码闲暇时,能够讨口酒吃!不像是某些他娘的熊货,他娘的只懂得用指头比划,便吩咐兄弟们做这做那,劳苦不说,更没半点实惠好处,即便是他娘的身识身境修为,顶个屁用!哎,沽巨军主,罴统领,我老秃噜可不是说你们,你们两位咱可是没半句怨言!”
说这话的,便是那眼识身境的千主秃噜,虽是说得粗俗到不堪入耳,但这话里的意思,却挑不出丝毫含糊来,除了未曾指名道姓,已是分外赤、裸的唾骂。
眼见这千夫所指的趋势愈演愈烈,驽部那熊脸铁黑,已是气得止不住的微微战栗。罴却是好整以暇,非但未曾出言制止,更是饶有兴致的在旁看戏,险些想要就地而坐,拿出几块鲜美肉食与一坛老酒,慢慢吃喝着看戏,这气氛才最是舒畅。
驽部被骂得忍无可忍,终是扬臂直指众熊鼻头,怒吼咆哮道:“恬不知耻!自甘堕落!竟敢辱骂上司,莫非你等想吃军法不成?还不快给我住嘴!自掴一百巴掌以示惩戒!”
此言凶煞乖张,听得呼延震惊失声,周遭众熊却是怒目瞪裂,像是那目光能化作锋锐利刃,将驽部顷刻切成万千肉片拿来下酒一般。
便在此时,那正立在驽部身前的沽巨军中,已然怒而出手,悍然捏住驽部那指指点点的熊腕,如若铁箍般牢实。驽部虽与沽巨境界相若,但沽巨这修为乃是厮杀苦炼而出,而驽部则不提也罢,哪里会是沽巨的对手,被沽巨攥紧自家熊腕,却是任由他如何极力挣扎,也是全无用处。
“哪里来的狗,满口不干不净的屁话!”
“你放开!沽巨,你要造反不成?”见得沽巨较真,驽部登时慌乱起来,却也不敢率先动手,惹怒了这沽巨更有他的苦头吃,于是只得任由沽巨擒住他一只熊腕,用言语低吼威胁道:“得罪了我驽部,没你沽巨的好肉吃!你知道我是谁么……”
他的话未能说完,已被沽巨狞笑骇得没法继续,便在他惊愕的当口,沽巨捶胸高吼道:“驽部侍卫莫要忘了,这是在军中,并非那彰显家事的家族圣地!”
这便是现世报,顷刻前驽部嘲讽罴的言语,如今被沽巨略作改动,便扔回给了驽部。这报应来得实在太快,堵得驽部近乎窒息,气得呼吸不畅,瞪了沽巨半响,那唇口哆哆嗦嗦,却怎也没能吼出半个字来。
“驽部侍卫,”沽巨嘲讽地低吼出声,那鄙夷神色与驽部先前一般无二,“依据这军中的规矩,想要做上司,还得靠自家的拳头!因此,我郑重向你邀战,用战熊军士的方式,来决定谁是统帅!”
这一声低吼隐有杀伐之气,令这驽部侍卫倏然呆滞,继而显出极度仓惶惊怒的神色。他可是心知肚明,自家虽与沽巨相若,均是身识身境的修为,但他一直在圣境潜修,境界提升全靠那强者血肉。若是与沽巨真打起来,他与沽巨便是天差地别,比不得沽巨那生死厮杀出的武力强悍,无非是自取其辱罢了。
见得沽巨同他较真,驽部底气顿泄,犹自色厉内荏地强撑怒容,咬牙切齿,怨毒死盯住沽巨,“沽巨军主!你要想清楚,得罪我的后果……”
威胁之意,已是不言而喻,但此刻沽巨已是忍无可忍,那些个忌讳早已抛之脑后,嘲讽低吼道:“驽部侍卫,我沽巨行得正坐得直,哪怕日后圣地不容我,我却无所谓,你又能拿我如何?若是不想让出统帅之位,说不得你尚要受些皮肉之苦,恐怕日后这面子便不大好看了!若是驽部侍卫足够识趣,不若顺水推舟,卖个情面给罴少主,亦是两全其美!”
谁说战熊直蛮,只是习惯了听受号令,只管宣泄嗜杀之情,懒得动弹心念罢了。待到要用到这心念算计,便是沽巨这等粗坯,在盛怒之下犹有心机,未曾将驽部逼入死角,低吼这一番言语,连消带打步步逼近,到头来又送了驽部一个台阶,实在想得周全无漏。
见得那驽部眼中已有踟蹰,沽巨索性大方放开驽部熊腕,若有深意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却仍旧候在驽部近前,只待驽部做出决定,却是进退自如。
“沽巨军主!和他啰嗦作甚,你便抢了他的军权,让他滚蛋便是!”
斜侧一头千主忽而怒吼,顿时便惊得驽部浑身一颤。骤然惊醒之后,他才想起沽巨那粗坯脾性,若是惹得这粗坯怒从胆边生,那时才叫驽部真是丢尽了脸面,还要受得一顿皮肉苦,尤为不值当。
如此做想,即便驽部将牙咬得嘎嘣作响,恨不得将这与他对峙的沽巨生吞活剥,切肉下酒,亦不得不退下一步,指着沽巨的鼻头,怒吼道:“好!好!好!你当真是勇士!我懒得与你多做计较,这群粗蛮熊货,送我使唤我也不要了,谁要谁拿去吧!”
撂下一句圆场面的狠话,驽部那脸色难堪,骂骂咧咧扭头离去,那临去前的阴毒目光,应是将在场所有战熊都怨恨上了,其中自然也包括一话未说的呼延。
可怜呼延看戏看得津津有味,没曾想他这毫无份量的小角色,也有被殃及池鱼的这一天。
眼见驽部远去,众熊面面相觑,终是轰然大笑,均觉着能见到驽部难堪,实在是间解气的事,怎不叫他们喜笑颜开,分外欢喜,亦是大松一口气。
毕竟这驽部来头甚大,连罴这得势少主的身份都吃不开,若是闹得太僵,最终吃亏的还是他们这群毫无靠山的战熊军士们。如此逼退驽部,在众熊想来,已经是最好的局面了。
看了这一出戏,罴那笑脸平淡如故,像是什么事都未曾发生一般。只是以呼延对罴的认知,罴那嘴角勾起的一丝飞扬,才说明了罴的真实情绪。
“就这样吧,你们四年未见,多些时间聊聊也好。”
留下一句话,罴便带着那隐露惬意的笑脸,悠然转身跨步离去,便连脚步都像是轻盈了好几分。
“哈哈!这样好!呼侍卫,你这四年的逍遥,总该给兄弟们好好絮叨一番才是。”站在呼延身侧的正是夫袭,将熊臂亲昵搭在呼延肩头,朝众熊隆隆大笑。
呼延目送罴远去的背影,忽而又生懊恼,苦脸叹吼道:“我还真是愚钝,方才主上尚在之时,怎忘了讨要几坛子老酒?如若无酒,岂不扫兴?”
“咦?这地上不正是十坛老酒么?”
沽巨忽而轻咦,引得众熊循声望去,但见他正站在罴原先所站的地方,堆落着整整十个酒坛。沽巨俯身抱起三坛老酒来,便满心欢喜地紧紧抱住不放,就像在抱一头身段妖娆的母熊,姿势尽显轻柔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