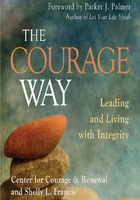弗恃难得一次卯时能起来的,桌上已经备好早点了,他抓过一个馒头,想着估计是因为要去听早课,长生提前起来热的,免得一会儿卦燎起来找不到他们又找不到吃食大发雷霆,哭鼻子把他这屋子淹了。
司马鹿鸣从房里出来,“师父。”他行过礼数,入座时下意识就是要解剑的动作,可摸了空才意识到佩剑已经被弗恃拿走了。自他父亲将剑交到他手上,便是剑不离身……
弗恃知道他是一时不习惯,“早课完了后,你随我去你众妙师伯那,先挑件兵器暂时先用着吧。”
司马鹿鸣道,“是。”
长生端着一大盘肉包子进来,这是给卦燎准备的。
这几日长生脸上一直粘着黑乎乎的锅灰,用清水怎么洗都洗不去,弗恃知道等时间过了,锅灰自然就掉了,反正长生也不在乎容貌,他也就没管。而到了今日她终于又变回了原来面目,也不知这锅灰是否有调理美颜的效用,她本就白皙的皮肤此时更是雪白到反光了。
“师父。”长生把包子放好后,她抱起桌上的一桶米饭,这是昨晚她多煮的,她现在的食量,若早上只吃包子清粥撑不到午时肚子就会叫,所以早上除了包子豆浆还得再加一桶饭。
弗恃觉得有些难办的抓了抓额头,他原先是打算低调的,现在看来估计有些难了。
弗恃悠闲的用完早点,领着两个徒儿御剑去了主峰。
徐清已经开讲了,数千弟子聚在其尘观内,盘腿坐于蒲团上认真听讲,按辈分规矩,弗恃应该到最前边和非恒众妙他们坐一处,可他素来不守规矩也懒得挤上前,干脆在最后头,坐没坐相,侧着身撑着头躺到地上了。
长生和司马鹿鸣盘腿坐下,听徐清讲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内容有些深奥,长生听得似懂非懂。
这数千弟子之中也不知是哪一个先开了小差,听讲听得累了,想偷偷回头瞅一眼殿外的白云悠悠,没想到却瞅见了长生。
前边的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的定住,后边的瞧见了自然起了好奇心,这好奇心往往是能杀死猫的,一个接着一个,这泛滥成了一片,也就顾不得慎灵正拿着一把长长的戒尺,来回的走动,要惩戒那些不专心的。
长生察觉到了无数道视线,想着是不是脸没洗干净,低头用袖子擦脸。
弗恃闭着眼呢,却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认真听,哪怕听不懂,至少态度得端正。别人分心是别人的事,你们两专心就好。”他说着摸出几颗藏在身上的炒花生吃。
慎灵往最后边看去,皱起了眉头。杀鸡儆猴的挑了两名弟子用戒尺狠狠的抽了他们的背,杀猪一般的惨叫,长生心里发毛,感觉戒尺像是打在她身上一般。
她转头看了一眼司马鹿鸣,见他心无旁骛,心下惭愧她不止悟性修为不及师弟,连定力和刻苦都不及万一,便收起心思专心致志了。
直到早课结束,弟子散去。
姜曲走时朝长生比了个手势,掌门他们都在,他可不似长生他们命好,有个不守规矩的师父带着徒弟也可跟着不守规矩,这玉虚上除了弗恃师叔,不论是哪一位门下都是管束得严的,听了早课要立马回去修习道法不可耽误。
所以姜曲不敢与长生他们多说,钱如月看向司马鹿鸣,奈何惧怕慎灵手中的戒尺,也不敢过去,她当初是因为司马鹿鸣要上玉虚拜师这才跟来的,谁料想,却是拜了不同的师父。弗恃又是三天两头的往外跑,她都多久没有见过表哥了,钱如月看着司马鹿鸣身边的长生,怔了怔,随即觉得格外的碍眼。
怜玉冲着长生笑,长生也回了个笑,怜玉随即便两脚发飘被门槛绊了一下跌了个四脚朝天。怜玉不是唯一一个跌得难看的,他身后不少弟子边目不转睛的盯着长生边走路,皆是被门槛绊了脚。
慎灵走到弗恃跟前,“什么时候回来的?”
弗恃吊儿郎当的答,“昨日回的。”
司马鹿鸣和长生行了礼。慎灵看着司马鹿鸣,方才他听讲时心领神会,心领气气随心,可见是有所悟,慎灵颇为遗憾,当初她想收司马鹿鸣入门下却被弗恃捡了便宜,他既收了徒,就该好好教导才不辜负了这好胚子,可是呢……当初若是归在她门下,修为何至于只到这般境界。
慎灵又看向长生,严厉的训斥,“你该知道自己天资不好,既入了玉虚,后天更应该比常人用功十倍才是,你自己不专心也就罢了,还要扰到其他人,叫他们也跟你一样不专心。”
弗恃道,“师姐,你要讲讲道理,这关我们家长生什么事。我徒儿是傻,可也不是什么锅都背的,归根究底是那些孩子定力不够,你不也狠狠打了么,再多教几次多甩几回戒尺就会学乖了,师姐你门下的那些徒儿不就个个全神贯注目不斜视。”
慎灵皱眉,她执掌玉虚的戒律惩处,看到有弟子做的不对,训斥几句不可么?“这世上凡事过犹不及,就像你们师父吃的花生炒得过咸了就不好了。相貌也是如此,到底专心的修行才是你们该做的,不要学你师父把心思用在旁处。”
长生低头听训。
弗恃想着长生若是有一日会顶嘴,那他就要给祖师爷烧香了,该让慎灵管教别人徒弟时先回去管束好自己徒儿,她门下弟子哪一个不是涂脂抹粉爱惜容貌,这不是用在旁处么。
反观长生,有时他都觉得她不像个姑娘家了,衣物首饰全然不热衷,只喜欢吃饭。
弗恃正要反驳,听到慎灵问,“我训斥你的,你可听明白是什么意思?”
长生想了想,略微有些高深,“师伯是说我长得咸?”
司马鹿鸣嘴角微微提起了些,不似弗恃看到慎灵听到这般训话心得气得脸发红哈哈大笑,他竟能看到慎灵的脸被气出了好几道褶子。弗恃道,“你师伯的意思是让你不可仗着你的容貌能下饭,能让你师弟每顿多吃几碗饭便不把心思用在修行正途上,你明白了么?”
长生又想了想,“师伯的意思是说我能健胃消食?”是这个意思么?
慎灵扔下一句“朽木不可雕。”走了。弗恃想着他这笨徒儿偶尔也是能把人气得内伤不治的,再稍稍点拨点拨,或许哪一日能开窍又多出一项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非恒走过来道,“你明知她就是这个脾气,偏还要与她争执,说过多少回了,让一让让一让,怎就是不听。”
弗恃挖了挖耳朵,他这些师兄上了年纪也越来越啰嗦了,都明知他不听了,还不厌其烦每回都要念叨一回,弗恃瞧了一眼指甲缝里的污泥,手往衣服上擦,“从来只有大让小,哪来小让大的,我那声师姐可不是白叫的,叫得师姐就得受师弟的气。只是她一大把年纪了,还这般心浮气躁,估计她这修为也难有突破了。”
非恒心想还真是被弗恃说中了,慎灵修行境界停滞不前,脾气才会较之前更急躁。
徐清走了过来,长生和司马鹿鸣恭敬的作揖,徐清对众妙道,“你带他们去吧。”
众妙斜了弗恃一眼,他倒是有脸面说慎灵,他自己何尝不是以小欺大,“明知道若直接和我开口,我肯定不答应,你就绕了一个弯,先求到师兄那,再由师兄跟我开口。你是打算当一辈子无赖是么。”
弗恃笑道,“师兄这说的是什么话,有借有还。”
众妙心想他还不知道他德性,有借有还倒是说得好听,他看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才对,“我是看在掌门的份上,可不是因为你这无赖。”
弗恃拍了拍司马鹿鸣和长生的头,“还不多谢师伯。”
长生不解弗恃为何也叫她道谢,不是该问安么,但她还是听话的和司马鹿鸣异口同声,“多谢师伯。”
众妙领着他们去,长生记得上次来好像还是为了偷酒。她记得众妙师伯的道馆墙的后边养了狗,那时弗恃还吓唬他们,说这些狗会挑身上干净的人来咬。
长生盯着墙。
想着弗恃这个憨傻的徒儿心里想什么还真是一目了然,妙众道,“我养的狗只会咬那些不请自来的,有我在,它们不会出来。”
自上一回遭了“贼”,众妙就把他观内按后天八卦布下的法术给改了,出口入口的方向被调换了,众妙穿墙而过,长生跟在后,进到一间密室。
弗恃道,“看来师兄这几年又得了不少好东西。”
他这胖师兄若不修仙问道,定能当个极成功的商人,和刻骨本事相当。他们玉虚这么多弟子,尤其长生,在吃方面是以一抵十。加上他和卦燎,这米缸里的米消减速度更是惊人。
虽似鹿鸣姜曲这些根骨好的年轻一辈修习得辟谷之术,又不似他贪口腹之欲,可以好几日不进水米,但终究还没成仙,还是得吃饭。
玉虚上上下下,有多少个人就是有多少张嘴,这每一粒米都得花银子。至今还没把玉虚吃垮,多得妙众经营有道。
密室之中放了八个大柜子,类似药材铺里装药材的百子柜,这些年妙众经营所得的宝贝皆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摆放在抽屉里,每个抽屉上贴着宝贝的名字。
妙众拉开两个抽屉,对司马鹿鸣道,“这两把剑一把名曰天御,一把名素尺,皆出自薛家。别看外观平平无奇,实则是削铁如泥的宝剑,死于这两把剑下的妖魔不计其数,因缘际会到了我的手上,原本是要传我座下的弟子的,只是这剑与市井之中铁匠铺里那些死物不同,自有灵性,他们皆与之无缘。你可挑选一把试一试。若是拔得出,你便带走,若是无缘,就别说我小气吝啬不给。”
长生想着又是拔剑么?怎么天下有灵性的宝剑脾性都这般相近,都喜欢用同一种方法来测试有缘人,只是这拼的真不是蛮力么?
弗恃就知道从妙众这取东西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上回盗酒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所谓的无缘估计是他座下的弟子无一能拔得出剑,他这师兄好颜面,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罢了。
弗恃玩笑道,“师兄可不会是在里面抹了什么,塞了什么让它拔不出来吧。”
妙众笑道,“我可不是你这等无赖,不会做那样没脸没皮的事。”
司马鹿鸣想起宋容赠姜曲纯钧时便说名剑与烈马一般不容易驾驭,结果长生一下就把剑拔出了鞘,他忍俊不禁,不由看了长生一眼。
妙众道,“怎么?你是觉得我似你师父说的那般是动了手脚,还是认为我说这两把剑是有灵性的宝物,你觉得言过其实。”
司马鹿鸣作揖,“师伯,弟子无此意。”
妙众确实不太想割爱,又不想落个小气的名声,为了证实他确实是大方的拿了两把会挑主人,拔不出只能归咎天意的宝剑出来,他把剑柄皆对着长生,“你试试。”
长生怔了怔。
司马鹿鸣道,“师伯,剑是弟子要借用还是弟子试吧。这场试炼是弟子的,最终得与不得弟子都会坦然的接受,不愿借助于师姐。”
妙众心想着司马鹿鸣这话倒说得好似长生必能拔得出剑一般,是他年纪轻太过于轻狂内心真是觉得这两把剑没什么了不得谁都能驾驭,还是这顾长生除了能使她那根笛子还有其他本事?
妙众又仔细的看了看长生,倒是好奇了。弗恃这个女徒弟除了样貌变化最大,其他的好似没什么改变了,也正因如此慎灵才这般气恼,一直当当初让长生拜入师门就是个会给玉虚抹黑的错误。
妙众对司马鹿鸣道,“你选吧。”
弗恃道,“你不必细想,只拿自己顺眼的就得。这世间事要说章法,其实也没什么章法,左右的就是一个缘字,你师伯也说了,你们师兄与之无缘,它等的就是有缘人。”
司马鹿鸣看了看,凭着感觉拿了天御。
这剑握于手中,竟有刺骨的寒凉渗进掌心里,冰凉得司马鹿鸣几乎握不住,他稳住心神开始运气,体内的真气与宝剑的寒气开始抗衡。
妙众知道他是开始尝试驾驭手里的名剑了,他将素尺对着长生,“你试试。”
弗恃笑道,“我这笨徒弟若是也拔出来了,师兄今日损失可是惨重了。”
妙众抬脚要踢一脚这个尽占众人便宜的,为人师表他却其身不正,好在他两个弟子秉性好没学坏,弗恃转了个圈躲开,妙众道,“她若是能拔出来,一并拿走。”
长生想着司马鹿鸣是因为没了佩剑才来借剑,可是她不是。
弗恃道,“你师伯让你试,你就试一试。”
弗恃这般说了,长生便握住剑柄,就跟拉柜子上的抽屉那般一下就把剑拔出来了,全然不似司马鹿鸣额上沁出豆大的冷汗,显然,他可不似她这般轻松。妙众微讶,因为长生拔剑时无半分阻力,该说这把剑是到了她手中才听话得似绵羊一丝抗拒也无么。
“可有感觉到什么。”妙众问。
长生“感觉”了一下,“大概六斤。”她不懂怎么看剑,但手中这把叫尺素的剑,剑身打得极薄,好像轻轻一掰就能弯曲,她想若是用来片鱼肉,或许能片出如宣纸那般薄得透光的鱼片来。
弗恃好笑,问的是重量么,“你师伯是问你可有感觉到不舒服。”
长生摇头。
司马鹿鸣平复体内的真气,剑出鞘一抹寒光似惊鸿掠过眼睛,剑气冷冽迅猛不可阻挡将密室中踏脚的矮凳削去了一角。
妙众看着司马鹿鸣手中如醒来般锋芒尽现的天御,弗恃说得对,他今日是损失惨重了,“拿走吧。”说是借,妙众心里明白得很,这是送了,他心微微的刺疼。
弗恃道,“师兄,我想把丹炉拿走。”
妙众道,“师父留给你的丹炉?”弗恃不是定得住的人,要他守着丹炉好几个时辰甚至好几日寸步不离只为看着炉火,炼丹,他没这个耐性,所以当年他下山游历时,就把丹炉扔到他这,“你不是说炉子带着不方便,不要了么?”
弗恃道,“这个师父不好当,得因材施教。长生虽说道法精进得慢,但在炼丹这方面似有些天赋,总不能抹杀了。”
妙众道,“算你有些做师父的样子了。”那丹炉是师父留下的,他一直小心保管着,舍不得炉子蒙尘,隔三四日就要擦拭一遍,“就放在那边……”观外檐下的铜铃响了,妙众听到铃声,知是弟子寻他,“你们先等着,我出去看看。”
妙众离开密室,原来是有弟子打扫观内时不小心,打翻了香烛把他道袍烧出了两个窟窿,妙众罚了那弟子抄写道经五遍,等他再回到密室,弗恃师徒已经不在了,炉子不在了,还有他准备用来炼丹的药草也不在了。
又被顺手牵羊了去。
这何止是无赖,还是个贼。
……
弗恃让长生添柴,点火,烧炉,“加二钱五味子。”弗恃边吃花生边翘着二郎腿教司马鹿鸣和长生炼丹。
长生道,“师父,我们没问过师伯就拿了他的东西是不是不太好。”卦燎和桃子刚才还围着丹炉跑,长生点了火后,他们觉得屋里热,就不愿意待了。事实上也确实很热,长生蹲下看,确定自己确实是往炉下添了两根细柴,可火烧得格外的旺盛。
她想师公传下来的炉子,应该也不会是一般的丹炉。炉子外表刻了许多她看不懂的符文,这比起在欧阳靖那看到的炼丹炉要更小巧些。
弗恃道,“等你炼好了丹,给他送几颗去也不算是白拿了。我教你炼的丹是要给薏米服用的,炼成了,让他服下或许就能化回人形了。”
“车前子……山茱萸……”
弗恃说一味药材,长生就添一味。一只鸽子落到窗台,弗恃看到那只鸽子脚上绑着的竹筒,猜想估计是欧阳靖飞鸽传书,那日寻到司马鹿鸣后他便传信给欧阳靖告知情况,商量办法。弗恃懒洋洋道,“鹿鸣,你去看看。”
司马鹿鸣走到窗台抓住那只鸽子,取下纸条阅读,他脸上布满忧色,“欧阳叔叔说我娘在赶来昆仑山的途中染疾,如今正于客栈落脚,我爹正照顾着,怕是要耽搁几日才能到。”若不是他出了事,爹娘也不必为此而奔波劳碌,身为人子不能尽孝,反让爹娘担忧,司马鹿鸣愧疚道,“师父,我能不能下山几日。”
弗恃知道他是要下山去探望,百善孝为先,他爹娘膝下只有他一子,想来自小关爱,他听到母亲生病,如何还坐得住等得了,“去吧。你爹可能会和你提起你们司马家的家事,外人听了怕是不太方便的。我和长生就不一同去了,至于你的剑我贴了道符在上边,你别撕,也别再使。你带回去让你爹看看,毕竟是你司马家家传的宝物,他知来历根源,或许知道该如何处理。”
弗恃去取了剑让司马鹿鸣带走,并叮嘱若是有事就传信。
司马鹿鸣御剑离去,长生这才想起司马家的信物还在她手上,她这脑子记性,或许真该吃点猪脑以形补形补一补了,只好等师弟回来再还他了。
长生炼好了丹药,问起这丹药的名字,弗恃却是忘了,他不喜读书,药理炼丹方面也并非强项,并非自谦就真的只是领长生入门,教些粗浅的,把他会的都教完了,随后精进只能她靠自己去书楼查阅。这么多年他还能记住方子已是不错了,至于名字,他随口就安了一个,“驻形丹吧,反正若是炼成功的,服下应该就不受你师伯设的法界的影响。”
长生看着手里褐色的圆圆的药丸子,“师父,若是没炼成功,怎么看?是不是从颜色或是从外观上分辨成与不成?”
弗恃撑着头,哟,还懂得思考和发问了,平日里教她道法是如何教,她便如何死记硬背,从未提过问,弗恃略感欣慰,“这丹药可跟你平日辨别那些饭菜馊与不馊不一样,光从这气味颜色来看,难看得出。”
“那怎么看?”
弗恃道,“跟开方子治病一个道理,方子开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开错了便治不好。丹药炼成了,这丹药是什么功效,服用了就有什么功效,若没炼成,妖怪的肠胃比人强健,大不了拉肚子吧。”
长生抓了抓头,琢磨着弗恃这番长篇大论,浓缩成一句是不是指让薏米做试丹药的狐狸?“师父,真的没什么问题么?”
弗恃道,“长生,这些方子能流传至今,自然是有前人验证过的。只要药材分量拿捏的准,炼丹的火候、时辰,这些你也能做到分毫不差,也就真的不差了。有师父在你担心什么。”
长生想了想,先去备了些泻药,再去抱薏米来喂它丹药。
过了一会儿,就见薏米身上的白毛退去,四条腿渐渐变化成人的四肢,弗恃饮了口茶,提醒道,“记得顺便把衣服变了。”
这可还有个姑娘。
薏米感觉身体轻盈,终于不似刚上山的时候,疲累沉重步子都迈不开,终又化回翩翩公子的模样,“多谢道长。”
司马鹿鸣一走就走了四日。
长生拿了张小凳坐在屋前摘菜,薏米坐到她身旁,卷起衣袖道,“我帮小恩公吧,也总不好意思一直吃白食。”
长生道,“你本来是送了亲就回去了,结果因为我们在外耽误了时间,现在又跟着我们回了昆仑山,你要不要写信去和馒头说一声,免得她挂念。”
薏米学着她把竹篮里的菜摘了,只留叶子,“我已经写信去和老祖宗说了,老祖宗允我在外头多留些时日,只叮嘱我不要给道长和小恩公添麻烦就得。”
长生真心的道,“你帮了我好多回了,哪里有添麻烦,我该好好的谢谢你,要不是你或许我都不能从魔都活着回来了,可我又不知该怎么谢你的好。”
薏米笑了笑,看着眼前蓝天白云,当初在狐狸洞时他还和长生说若是哪一日有机会见一见这昆仑山的美景就好了,没想到这么快便实现了,“在魔都时我见到小恩公为了你两个师弟连生死都可以不顾,好生的羡慕,不知若是哪一日,我也遇到同样的事,小恩公愿不愿意也为我这般奋不顾身。”
他们是朋友,共过患难共过生死的朋友,“你为了我们三番两次的涉险,哪一日你也身处险境,我也愿意为你两肋插刀的。”
薏米笑得开心,“凡人多有背信弃义的,但我知小恩公是言出必行,小恩公可要一直记得你今日和我说的。”
长生点头,她会记着的,得人恩果千年记,义父和师父都教过,“薏米,你笑起来和馒头好像。”
薏米侧着头托着腮,眸里流光溢彩,就像万丈光辉洒在翻涌的云海上一般,涂山氏的狐狸崽子打娘胎生出来就是美艳懂魅人的,“小恩公这话我能不能理解成你觉得我和老祖宗长得一样好看?那是我好看些,还是小恩公两个师弟好看些。”
长生心想原来薏米和姜曲一般那样的在意容貌,“都好看。”长生一下就把篮里的菜摘好了,她干活一直很速度,因为一会儿还得腌肉,她拿过薏米手里的菜叶,道了谢。
薏米看着长生进厨房里忙了,也不知是长生太过于不解风情,还是他这副皮囊还不够美得叫人失魂落魄。
弗恃躺在树干上,他原还想着是不是该写信让司马鹿鸣回来。可薏米和长生的对话他一字不差的听完后又觉得没必要了,他家长生若是这么容易就被勾引了去,那鹿鸣也不会近水楼台处了几年,还是这个样了。
卦燎嚷嚷着由远处跑近,他跑到窗台那,从窗户跳进厨房里,“媳妇,媳妇,山下来了好多好多人。”他方才跑到主峰去玩了,然后听到有弟子说九宫山光天坛还有……反正好多好多门派,他也记不得了那些名字了,就是好多好多人来了,他就带着桃子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