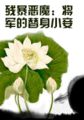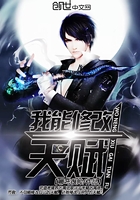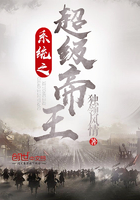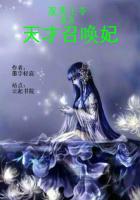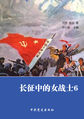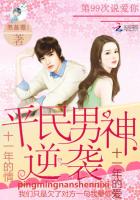司房门外有颗碗口粗细的秋子白梨,七月绿肥红瘦,树下是一片残花碎雪。我透过一眼窄小的格楞向外张望,及目所见皆是葱茏的碧绿。只有老树枝丫间散落着几片凋谢的苍白,那样消瘦而憔悴。梨花落尽,春天也快要过去了吧。
古有司同四音。司房顾名思义,就是妓府后院的一行四尺见方的矮舍。专供奴隶官妓居住,每四人一房。屋舍面北,终年不见阳光。房屋的一半埋于地下,无窗,只在面西的角落开了一方三尺四格的方洞。
我在这座囚笼般的陋室里蜗居了整整两年,严冬的阴冷苦寒,酷夏的暑湿潮热。曾经无数次,我长久的凝视着那些伏生壁角的苔痕。房屋已老旧了,经过不知多少人来去。居住在这里的妓女们早已没有心思收整,房屋的角落里遍布着茂盛的苔草。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羡慕那些苔草,他们年年月月;一岁一枯荣,贫贱的身躯早已适应了苦陋的环境,不惧寒暑亦不知这人间的沧桑。
直到许多年以后,每当我病卧深宫,看着玉手纤纤的婢女奉上的一碗汤药;我却总会情不自禁的想起韩箐。
第一次见到韩箐是在哪里呢?思绪不知不觉间径自飘远。我又想起那个屈辱的初夏,灼人的艳阳下一叠整齐的黄笺奴籍。宦官尖细的嗓音响起,一张纸页掀去。离去前的刹那,我习惯了余光一瞥,就见那揭开的扉页下赫然书写二字-----韩箐。
韩箐,韩氏。
说起韩氏,开京城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高丽荣盛三朝的世家名门,世代入仕为官,却不巧与德妃明氏一族结姻。如果没有卯巳士祸,韩箐或许早已嫁作明氏妇。这些自是后来相熟时韩箐说予我。而彼时的我与她既无一面之缘,也还不知道,韩氏这辈嫡出长女闺名单一个箐字。
或许从那一时开始,我们的命运就奇异的纠缠在一起。就像两个原本迥异的个体,莫名其妙的相遇却再也无法分离。韩箐,这个如此烈性的女子,爱与恨都过分强烈到令人动容。她陪伴我渡过了半个残败的青春。而我亦用自己最后的年华鉴证她那轰轰烈烈的爱情。她最终横死在朝阳殿的偏房里,可是或许连她自己也无法说清同我的关系。我们之间是爱是恨,是朋友还是敌人,一切在她死后早已无法辨拾。空余下的,只有一腔哀伤,浓的却化不开…。
记忆里,我与韩箐的初识就始于妓府后院那间小小的司房。高丽有制,凡入贱籍者不得居内城。于是开京大大小小的妓馆几乎都散落在护城以南的青石桥下。然而,真正上得档次的行院却分布于桥北。
清溪北岸,别牧巷宛如一条绵长而华美的绶带束于桥畔。那些稍有姿色的妓女,凡能识文断字或粗通音律者几乎都聚居于此。甚至天家营绎的娼馆亦坐落此地。
在这严于礼义的国度,高居上位的统治者却如此奇妙的矛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