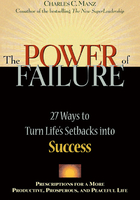先锋大将、兵部尚书韩岱禀报曰:“出城迎战的是史可法手下总兵刘肇基。此人乃史可法左膀右臂,甚是忠勇。不过扬州城中守将并非铁板一块,目前已有数位将军暗遣使者来我军中,商谈归降一事。”
多铎点头道:“本王怜史可法之才,若能为我所用,江南不足忧矣。本王当尽一切所能,招降史可法。倘若事成,江南战事可不战而定。”
韩岱道:“史可法师从于左光斗,也是个愚忠之辈。我料史可法必不投降,定要与我大军玉碎于扬州城下。”
多铎冷笑道:“此战,将为我大清征服江南的最后一役!若史可法率部降我,则可保城中数十万军民之性命。倘若不然,我将屠城十日,杀尽胆敢抗我大清军威的所有人等,不留一鸡一犬!”
韩岱吃了一惊,禀道:“大帅莫非要效仿霸王项羽,立威于江东?”
多铎冷笑道:“不错!宣我将令,以后若有见我多铎军旗不降者,便如扬州一般,杀尽满城军民,鸡犬不存!韩大人,你率先锋部队,出营列阵与史军对弈!倘若军中有临阵观望着、畏惧不战者、临阵退缩者、战之不利者,阵前立斩。此战,当尽挫史军锐气!”
清营内击鼓三通,营门内奔出数名大将,率军一万,列阵在营寨之前。军中一名千夫长持刀奔出,叫阵道:“你等南蛮士兵,见我大清军威如此,还不赶快归降?昨日那个伤我斥候、叫盖问天的蛮子,速速出来受死!”
盖问天哈哈大笑,从军中策马而出,也不搭话,六尺长剑挥舞,与那名千夫长战在一处。
刘三带马,站在盖夫人一侧,为盖问天掠阵。盖夫人望了望刘三,微微一笑,随即将目光投向战团中的盖问天。
刘三昨日问了盖问天长剑一事。盖问天说到了扬州,便找铁匠用上好铁料打造了一把。铁匠怕此剑太过沉重,寻常马匹驮不动,因此长剑虽打造得十分锋利,但重量却减轻了十来斤,盖问天用起来不是很趁手。
数招过后,那千夫长不敌盖问天神勇,渐渐露出下风,只是主帅将令难违,不敢败回本阵,只得勉力支撑。清军队中另三名千夫长见势不好,各持兵器出阵增援,四名敌将围住盖问天。刘三见状,也奔出阵来,挥舞两柄倭刀,杀入战团,六个人六匹马搅在了一处。
盖问天得刘三相助,压力一解,奋起神威,一剑将一名敌将连头带肩劈成两半!刘三双手挥舞着倭刀,双手刀势相同,便如是心意相通的两人一般,共同对敌。所持倭刀虽是较轻,但招式精湛,如庖丁解牛一般,游刃有余,片刻后也斩杀一员清将。剩下两将见势不妙,虚晃一招,便想逃走,盖问天和刘三岂能容他们退去?抓住战机,两人也瞬间被斩。
刘肇基见敌将已灭,我方士气正高涨,令旗挥动,率部冲击,与清军杀在了一处!
清军虽然折了几员大将,但士兵皆舍死奋战,阵脚未见丝毫凌乱。史可法见敌寨中旌旗招展,料定敌军正在集合部队,准备出战,急忙鸣金收兵。
经此一役,双方都已经了解对方的战力。史可法见敌兵势大,严令各部不得出城迎战,只在城墙各处加强巡逻警戒。多铎也是奇怪,虽然南下的清兵越来越多,对扬州已是合围之势,却并不急着下令攻城,只是遣人给史可法送来劝降书信,却被史可法严辞喝退,连书信也不曾打开。刘三、盖问天等则带领史可法的亲兵,在扬州城内四处巡查,因此虽城内有军民二十余万,但也次序井然,趁乱偷盗、打劫者甚少。
刘肇基前来西城,找史可法禀报北城情况,上了城楼,便大吃一惊,指着城外小山岗上的树木道:“大人,这片山岗,高出城中地势,城中部队调动,从这座山岗上可一览无余。更兼山岗之上这么多树木,便于隐蔽。若清兵将大炮埋伏于此处,对着城内轰击,如何是好?末将原带本部人马,守住这片山头,绝不能让清兵占据此处。”
史可法叹道:“我如何不知此处险要?只是该处是我扬州百姓的祖坟墓葬之地,若将它夷平,于城防当然要好,可是如此一来,百姓势必会有怨言。扬州民心一乱,守城可就难了!”
刘肇基道:“既然如此,末将愿将山上树木悉数砍伐,免得清兵炮队藏匿其中。”
史可法摇头道:“妄动百姓祖坟上的草木,与掘百姓祖坟无异,还是罢了吧!我已令陈于阶将城中大炮半数移到西城,扬州只需坚守十余日,待江东援军一来,清兵便会知难而退。”
刘肇基道:“大人,我观这扬州城,城内地高,而城外地低,若掘开北面的邵伯湖之水,定能将城下之敌陷入灭顶之灾。”
史可法摇头道:“刘将军,若掘开邵伯湖之水,恐怕是杀敌三千,自损一万,扬州城外数百里之内必定是一片汪洋,百姓定然遭殃!此计万万不可。倘若时运不济,你我就算殉城而死,也不能落下个千古骂名。”
刘肇基也摇了摇头,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望着西门外那片高地上的树林发呆。
刘三在城中巡查完毕,也上了西城,见刘肇基也在,朝他微笑点头,然后对史可法道:“阁部大人,扬州新旧两城,共有城门十三处,皆需分兵据守,不能合兵一处。在下以为,如今清军兵临城下,东、南、西、北四向,各留一处城门,其余各门,皆用土石从内封死,大人以为如何?”
史可法点头道:“很好,如此有劳了!”
刘三领命,与盖问天夫妇两人率城中居民担土垒石,堵住了九处偏门,只留下四处正门出入。
江东沿岸,日日都有冒险从江北偷渡过江的百姓前来避难,因此南京城中百姓都已知道清兵兵临扬州城下,人心惶惶。
弘光帝正在后宫看着史可法派人呈来的乞兵书,心中开始不安,便唤卢九德请马士英、阮大铖入宫。
马士英看完史可法的乞兵书后,再递给阮大铖,道:“皇上,江北四镇之兵如今虽然只剩下两镇,但刘泽清和高杰旧部加起来尚有兵力十五万,清兵不过十万,其势足可与清兵决战,如何会少兵?”
弘光帝道:“史可法说刘泽清与东路清军固山额真准塔暗中勾结,不发一兵一卒到扬州,只怕有变。而高杰旧部缺少领军大将,各部如同一盘散沙,李本深、胡茂顺等人已经降清,李成栋下落不明,该镇之兵已名存实亡。”
阮大铖怒道:“臣不知这史可法是如何督军的,怎么竟然使得江北各镇弥乱至此?!”
马士英道:“皇上,万万不可偏听史可法一面之词!刘泽清前些日还有书信寄来,说目前江北各文臣武将,或降清、或过江、或渡海,独有他一人孤军当道,绝会不退却一步。刘泽清忠勇如此,他岂会降清?我瞧定是史可法惧敌,谎报军情,骗粮骗饷而已。”
阮大铖也道:“若听史可法之言,抽调黄得功、或是刘良佐大军北渡,若左梦庚率部偷袭南京,仅以一部兵力,如何抵挡?莫非史可法的扬州比皇上的南京还更重要不成?”
弘光帝道:“扬州一丢,则南京北面再无屏障,如此南京危矣!两位爱卿速速拿出方案,切切勿要让扬州陷入敌手!”
阮大铖道:“皇上放心,臣等立即抽调江东可用之兵北上,不过如今江东可用之兵恐怕无多。只是史可法监军失职,令江北一片混乱,大片国土陷于敌手,皇上应治其监军不力之罪!”
弘光帝点头道:“如此你等快去调兵北上!史可法之罪,待扬州之围一解,再去追究不迟!”
马士英、阮大铖出宫后,马士英道:“阮公,你看这江北之势,史可法能胜清兵么?”
阮大铖低声道:“马公,史可法此人,死活都要面子。若不是形势危急,绝不会如此低声下气,连连催兵。我瞧扬州旦夕且下,就连南京也守不了!公早为之计,勿要陷于危城之中,不得脱身。”
马士英道:“那么也就无需再派兵北上了!不过这样一来,岂不是陷史可法于死地?”
阮大铖道:“此人数度与你我二人为敌,如今钟鸣漏尽,当及时报复,否则哪里还会有这等机会?”
弘光帝待两人走后,在皇宫之中乱扔东西。卢九德站在旁边,颤颤巍巍,不敢做声。
弘光帝怒道:“马、阮二贼误我!早知如此,便不该将史可法逐出南京!如今这二人独揽朝政,连朕的旨意他们都敢不听!”
卢九德跪下道:“皇上圣明!马、阮二人实在是太过放肆了!”
弘光帝心中委屈,忍不住大哭道:“他们以为朕糊涂,其实朕心中如何不明白?无奈只好装糊涂而已!扬州若失,南京也是守不住的。早知如此,朕就不该听他们撺掇,去当什么皇上!朕当福王要好得多,不会如同皇兄一般,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
卢九德也垂泪道:“如今江东满朝文武之中,能信耐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黄得功,一个是刘孔昭。若南京城陷,老奴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护送皇上逃离此处!”
弘光帝心中悲痛,与卢九德抱头痛哭。
四月二十一日,刘三训练亲兵回来,走入大帐,只见史可法怀中抱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士兵,眼中蓄泪。
那士兵被医官救醒,见躺在史可法怀中,便要挣扎起身,却给史可法止住,道:“无妨。你且休息片刻,再说不迟。”
那士兵气息奄奄,声音微弱,道:“阁部大人,洪盛师傅令小人前来禀报,东平伯刘泽清不战而退,将大军撤退至海上,淮安已经落入敌手。瓜洲高杰旧部张天禄、张天福、李成栋也相继投敌,如今扬州城外围已全部陷落。清兵东路军固山额真准塔领带着各路降兵一路南下,加入了多铎的攻城大军。小人仗着地形熟悉,深夜闯阵入城,一路上只见清兵把扬州围上了数层,兵力至少有二十万。洪盛师傅正率领数千汉留勇士在扬州外围,冲击敌阵数次,皆被清军击退,不得入城,只得在城外四处袭扰清军。”。
史可法掉了几滴泪,望着那士兵浑身的伤口,哽咽道:“这重重关卡,也不知道你是如何闯过来的!我大明将士若个个都如你这般忠勇,时局何至于此?医官,不惜任何代价,你都要救活他。”
医官探了探士兵的脉搏,摇头道:“大人,此人伤势太重,只怕是在下回天乏术,无可奈何。”
史可法急道:“这可如何是好?”
紫儿道:“大人,家父有一朋友,叫钱应式,他是神医傅青主的弟子,如今也在城中,听说他医术高超,何不找他一试?”
医官喜道:“在下也听说过此人,妙手回春,救人无数!若能有他相助,那真是再好不过。”
史可法急急挥手,道:“如此便有劳少侠和紫儿姑娘,快快送他去找钱先生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