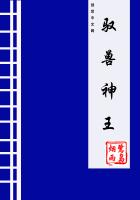江湖分为六大门派,皆是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之辈。百姓本应安宁平静度日。可近些日子出来一个从未有人听说过的虚元宫。一时之间无人不惧怕。所到之处,便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虽说不是对着百姓下手,而是几大门派撞上了虚元宫,话未说一句,便先动起了手。可谁能受得了这般惊吓。要说也怪不得几大门派不依不饶,虚元宫宫主自个儿放出来话,三月之内必将天岭教灭门。
天岭教是江湖上最有名望的正派,其他门派无一不臣服。听到这等辱没的话,怎能忍得下去。说来奇怪,其他门派打得热闹,天岭教却从未有机会与虚元宫交手。
天岭教的弟子心里都憋着口气。
可巧,天岭教上山的一条路有十来个人抱剑在那儿站着,应说是特意等着。他们的衣服都是白色的袍子,胳膊处绣着青竹,正是虚元宫的打扮。
两个门派对视一眼,纷纷冷笑,拔出剑刺向对方。功夫不相上下,一时打得难解难分。这可就苦了想走这条路的行人,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生怕刀剑无眼伤了自个儿。
全仰仗运气的事儿,自然有那运气不好的。
秦书宜缩着脖子,抖着肩膀,仔细瞧着刀剑的走势。看见有一点儿冲这边过来的苗头,就赶紧换地方。结果躲得人多,她身材又偏瘦,被别人挤了出去。还有人趁乱推了她一把,一下就摔倒在正打得火热的两派之间。
秦书宜吓得直哭,脸都白了。方才提到名门正派,皆是行侠仗义之辈,遇到此事,哪还打的下去。对方却纠缠不清,这边早已无心恋战,瞬间落了下风。
天岭教一位弟子急得不行,招数变得散乱,渐渐不敌对手。一边正在哭的秦书宜,突然抱住他的腿,抖个不停。弟子连忙低头看她,却没瞧见她的表情,对面又挥过来一剑,他无法闪身躲避,只得拿剑去抗。
对方却收回了长剑,又吹了个口哨,一脸看好戏似的神情。虚元宫的人渐渐都停下手,刀剑声停下,耳朵不适应的嗡嗡几声。
虚元宫的人道:“这姑娘倒也真会扑人,一下儿就扑了个最俊俏的。”
说完一阵大笑,弄得被秦书宜抱住的弟子一阵脸红,被笑得恼怒了,又拔起剑来朝对面的人:“莫要胡说,若不是你们生事,岂会殃及无辜之人!”
那边毫不在意,听他说一句,他们便笑一声。气得那弟子去推秦书宜,要上前拼杀。但秦书宜抱得紧,他又怕伤着她,推搡之时竟像小两口闹脾气。尤其是秦书宜脸上还挂着泪珠。
嗤笑声更明显了,弟子弯着腰用力去掰开她的手指,秦书宜死拽着他的裤子不放,他又狠了心要把她推开,拉扯了一阵,差点把裤子弄下来。弟子羞臊得很,看着秦书宜脸上泪珠不断,他也想哭了。
还是与这弟子同行的人看不过眼,斥道:“承治,这般拉拉扯扯如何要得。”又对虚元宫的人道,“你们若是想交手,让你们宫主过来,私下打斗有什么意思。”
虚元宫的人笑着摇了摇脑袋,领头的一摆手,都下山去了。
天岭教弟子哗啦全围住承治,瞧他急得快要哭了,才赶紧帮着把秦书宜弄走。秦书宜也不再默默掉眼泪,哭出了声音,听上去惨得很。
承治瞧她哭,他心里的委屈更大了,郁闷地一屁股坐到地上,生气地不看人。
路过的行人见他们那儿正说的热闹,赶紧走过去,生怕再有波折。天岭教弟子伸手把承治拉起来,不让他闹脾气,天眼看就要黑了,赶紧回去才是。
一干人等准备浩浩荡荡的上山。
忽听一声带着哭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们就不管我了。”
承治回头怒瞪她:“你还想赖上我?”他正一手提着裤腰带,方才硬是被秦书宜给拽松了。
秦书宜被他凶得一缩肩膀,然后抬着下巴,硬撑着说:“就是赖上了怎么样。我走的好好的,你们偏要打架,如今把我吓着了,你还想不管我?”
承治一向在天岭教受宠,又懂事,没人与他吵过架,嘴巴自然不厉害,一时说不过她,只好气得身子发抖。
方才替承治说话的是厉师兄,此刻开口道:“姑娘还是快回家去吧,我们一群男人实在不宜与姑娘多做纠缠,怕会坏了姑娘的名声。”
秦书宜用袖子一抹脸,眼睛红红的,瞪着厉师兄道:“我都不怕坏名声。你个大男人胆儿怎么这般小。实不相瞒,我前些日子失去双亲,本是想去投奔叔父家,结果却被你们挡在半道上,写着地址的信和散碎银子全被人偷了去,如今我已是无处可去。”
众弟子摸着下巴,不太相信。
别说他们不信,就是薛娘听到系统告诉她用这个冒牌身份的时候,也是不信的。到处都是疑点。可时间紧急,系统又说这个是真事儿,而且寻亲的人早已被抢了银子饿死了。
薛娘真正的身份是虚元宫宫主。一心想称霸武林,灭了六大门派的宫主。那些流言都是她依着人设放出去的,以现在的身份去刷天岭教弟子承治的好感度,怕是话没说上一句,剑就朝胸口戳来了。
所以就生了这个法子。那些堵在路上的人,自然也是她派的。
不管天岭教如何心存疑惑,也不能看着天黑了把一个女子单独丢下不管。薛娘跟在他们后面上山,怕她掉队,还派了承治看着她。
也不知天岭教的人是不是故意的。
承治每走两步就瞪薛娘一眼,薛娘看过来,他就往别处瞧。如此反复几次,承治一个疏忽没察觉脚下的石子,被绊了一下。两手死死抓住裤腰带,生怕出丑。低头停住都收拾好了,再继续瞪薛娘。
薛娘都替他累得慌,复杂地看了承治一眼,他连忙扭过脸不想看她。薛娘默默地伸手帮他把露出来的腰带塞回去。刚碰到边儿,就被承治满脸通红的狠狠朝她手上打了一下。
声音尤为突兀,众弟子回头看,承治闷头走着,满脸羞臊。薛娘正跟在后面,似是没什么事儿。众人叹口气不再去看,到天岭教的路程没几步了,抓紧时间上去。
薛娘手背在身后,默默揉着。她怎么觉得自个儿跟个登徒子似的。
天岭教,大门前老早就有人守着,盼他们回来。天岭教教主的女儿顾溪琳,瞧见他们连忙蹦起来挥手。待他们走近点儿,她一连串问了许多,脸上洋溢着笑,然后探头探脑的,厉师兄笑她:“别找了,承治在队伍后面。”
顾溪琳羞着低下头:“谁找他了,我爹说让你们回来后赶紧去见他。”然后就赶紧跑了。
承治还在两手提裤子,一双眼睛瞪薛娘。
薛娘头疼的厉害。
他们先去见了教主,留薛娘在门外等着。门外还有四五个守门的,薛娘站在那儿不自在的很。只好装作仰头瞧屋檐上的花样。
过了会儿,薛娘低下头揉揉发酸的脖子。终于听见里面有了动静,出来一个人,朝外面看了两眼,找到薛娘对她道:“教主让你进去。”
薛娘颔首,提了裙摆款款而行。
教主高坐在椅子上,下面站着一众弟子。薛娘低着头站到前面,对着教主行礼。教主说话和蔼,只问了她一遍身世来历。
薛娘又照着说了一遍。他笑着摇头,也不知信了没有,竟就让她住下了。承治皱着眉头,想说话,就被教主给打发走了。又让众人散去,不再多说。
薛娘单独有一间屋子,一张木床,一席书桌。一摸上去满手的灰。她叹口气,寄人篱下有个住处就不错了。朝人问了水井在哪儿,打了些水来,将屋里擦干净。
正待她扫着地,就见承治朝她这儿来。薛娘眉毛一挑,他看她跟仇人似的,怎么这会儿自个儿过来了。
薛娘没主动说话,当没看见,仍打扫着房屋。
承治走到她跟前,用力地清嗓子。薛娘这才抬头看他,他一脸别扭,俩人瞧了半天,他才道:“不管你有什么心思,到了这儿都会有人看着你,不要妄想会得逞。”
薛娘心下一惊,她被发现了?
后又听他道:“望你今后莫要再缠着我,女子怎能不顾羞耻的来抱男子大腿,实在是不成体统。我今后也会躲你远远的。”
哦,原来指的是这个。
薛娘冲他一笑,温婉可人,听话地点头:“我都知道了。”
承治已经准备好与她斗嘴了,默默在心里念了好几遍词,没听见她说的是什么,就开口道:“虽说我有不对的地方,可你……”
后知后觉,尴尬地挠了挠脑袋,清嗓子道:“你知道就好。”
他转身准备走,许是心里太紧张,竟没发现薛娘用来涮抹布的水盆,看着就要踩进去。薛娘连忙叫住他,然后跑过去。
承治以为她又要动手,连忙抓好裤腰带,结果踩进了水盆摔倒在地上,裤腰带也被他自个儿扯断了。薛娘站在一边儿不忍心看。
他瞧着手里的半截腰带,表情要哭不哭的。
薛娘道:“要不,你脱下来我给你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