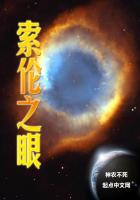被薛娘斥了几句后,卫司的气势开始减弱。皱着眉头,想张嘴说话,薛娘一瞪他,有咽了咽喉咙,在嗓子里嘟囔了几句。薛娘这会儿心里火气大得很,日子过得好好的,非得弄些事儿出来。
她脸色难看,冲着卫司道:“赶紧说,因为什么闹脾气。”
卫司瞪着俩眼,一副被气着了的模样儿,想发火儿,又强忍住:“没事儿。”
薛娘点了点头,走过去拽住卫司衣领。没他长得高,踮着脚尖把卫司拖到炕边儿,从矮柜上拿了蓝布枕头压在他脸上。
卫司没挣扎,随着往炕上倒。觉得憋得慌,侧过脸:“你说不过我就动手,你不讲理。”
薛娘没好气地说道:“我现在是鬼,用不着跟你讲理。”
枕头压得越来越紧,侧过脸也不管用了,卫司声音闷着,喘不上气:“你真打算把我给杀了?”
薛娘看了眼他两边儿的手,皆是轻松的放在炕上,连拳都没握。语气也平静得很,哪儿像是害怕的样儿。
反倒是把系统吓得不轻,一直喊:“你要是把他给捂死了,那可就全完了!”
薛娘下手是知道轻重的,本就是想治治他别扭的性子,系统在一边儿嚷嚷的她烦得很,皱着眉把枕头拿开。
卫司躺在炕上,脸憋得发红,大口的喘气,胸口起伏。看了眼薛娘,有气无力地说道:“怎么怂了,我当你真想把我给憋死。”
薛娘揉了揉额头,对他没招儿了。脱了鞋往炕上一歪,看着卫司,他也正盯着薛娘,二人对视了片刻,谁也没开口说话。
薛娘闭了闭眼睛,莫名觉得有些累:“我不想跟你斗心眼儿了。以前就这么猜来猜去的,生了不少事端。如今你我阴阳相隔,还有什么是不能直说的。”
屋里没有一丝光线,黑暗中,卫司躺在炕上看着薛娘的脸,神情带着薄怒,眼神透着疲惫,语气极为认真。
他忽然觉得心里的气瞬间散了,只剩下努力撑了这么些天的劳累。此时他连笑都没力气,抬了抬胳膊,想搂住薛娘,伸到半空,瘫软的垂下。
手一凉,薛娘握住了他的手。
卫司抬眼,弯了弯眼睛:“你手真凉。”
薛娘没吭声,盯着他看。卫司跟小娃子似的,皱着眉,语气不由带了丝委屈:“我也不是成心的,就是觉得你把我给耍了。”
薛娘没弄明白,表情疑惑。
卫司有些不好意思,用另一只手将眼睛捂住,闷闷地说:“好像自己跟个傻子似的。”
薛娘垂了眼,琢磨他说的话,轻声问道:“为什么说我耍你?”
卫司嘟囔着:“你自个儿知道。”
薛娘捏了捏他的手,卫司皱眉:“你又欺负我,本来就是你不占理儿。”
他说的话一句天上一句地下的,薛娘猜着他是不是知晓什么了,可又觉得不对劲儿。陆墨是因为看了镜子,知晓从前的过往。可卫司从哪儿看去。听他的语气,像是委屈得很。
薛娘试探着说:“我到你身边儿之后,就开始瞒了你,后来可有一句唬你的话?”
卫司抿了抿唇,瞪着她,像是在责怪她不老实。薛娘张嘴想开口,就看见他从炕上慢悠悠的起来,看了眼外面,厨房的烟筒正冒着气。
算了算时辰,也到时候了。整整衣裳,揉着肚子道:“想听我说话,就去厨房。今儿因着你,我都没吃好,这会儿肚子饿得直叫唤。”
然后迈着步子走了出去,薛娘被他的态度弄得一愣一愣的,连忙穿了鞋跟着他走。忽又慢下来,磨蹭了会儿,才过去。架子上点着煤油灯,光线昏暗。
卫司正在那儿烧火,柴火干燥一点就燃起来。拿了烧火棍吹了吹,烧得更旺。炒菜锅还没洗,锅底一层油。他腻歪的不行,一手掂着锅把,让薛娘去舀瓢水过来。
薛娘应了一声,从缸里舀了一瓢倒进过去,卫司拎着锅把涮了涮,往院里一泼。
案板上放着洗好的菜,切好后下锅,旁边儿的灶上炖着肉,应是有几个时辰了。方才薛娘闹别扭没注意,这会儿转过来弯儿。合着早就算好了她能跟着过来。
撇了撇嘴,怎么哪回都是他心眼儿多。
菜做好以后,卫司端到桌子上。这回没烧香。他也不动筷子,看着薛娘一句话不说。她清了清嗓子:“我也饿了。”
卫司这才跟往常一样,烧好香,让薛娘坐下吃饭。
味道是挺不错,她许久没吃饭,猛不丁吃一顿觉得比以往的还要好吃。过了半天,才想起来方才的事儿,这么一打岔,就过去了?
卫司瞥了她一眼,也没吭声。等都吃完了,他把碗筷洗干净。折腾的天快亮了,才往屋里。
薛娘打定了主意,今儿要把他的心结给解开。拽住他说话。卫司脸上不耐烦,嫌她啰嗦。背对着她倒了杯茶,弯了弯嘴角。
他说道:“之前我记得有一回,你说你饿得很,让我把碗里最后一块儿肉给你吃,那这些天一粒米都不沾,怎么不听你喊饿。这算不算唬我?”
薛娘把他的手放开,撇着嘴瞪了他一眼,作势转身往外走。卫司连忙凑过去,搂住她的腰:“你怎么又急了,不是你提的要好好说话么。”
薛娘在他背上打了几下,带着怒气:“我与你说正事儿,你偏要往别的上面扯,我还在这儿待着做什么。”
卫司闭了闭眼睛,搂住薛娘不放,轻声问:“好,我告诉你这些日子心里在想什么。”
叹了叹气,抿着唇没说出来。
薛娘又打了他一下。
卫司沉声:“我问你,即便当初没有陆墨把你绑去宫里,是不是也肯定要走的?”
薛娘身子一僵,没有再动作,感觉到卫司温热的体温,心口发烫,咽了咽喉咙,看了眼窗外,天要大亮,先前都是一团漆黑。语气带着丝慌乱:“是。”
卫司没有再说话。
薛娘僵直着身子,垂眼看着他的后背。屋门关着,把冷风隔在外面,二人却仍然感觉不到暖和。
在漆黑的屋子待久了,看东西也清了许多。卫司的表情尤为平静,薄唇抿了抿,语气和缓地说道:“那你可想过还能回来?”
薛娘眼神发怔,听见自己的声音:“没想过。”
她整个人有些飘忽,分明是踩在地上,却像站在棉花团上面走。心里一阵难受。忽听卫司说道:“你怎么不说话了,方才不是还理直气壮的么。”
薛娘垂下眼:“我没理。”
卫司轻轻笑了一声,屋子里静的很,听见他滚了滚喉头,半晌,又问道:“那你要是再也见不到我,难受么?”
薛娘盯着他:“难受。”
她跟下了学堂的小娃子一样,大人问什么,她就乖乖地答什么。卫司眯了眯眼睛,见到薛娘这副模样,着实稀罕的很。
又问道:“你……“
他故意拖着长音,没说全。薛娘神情认真,瞪着眼睛看他。其实卫司听见她说难受,心里就放下了。
之前一想到她能那么利落的将他抛下不管,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薛娘越是对他好,就越难受。
过了会儿,卫司搂着她呼出一口气,声音有些发闷,语气却轻快了不少:“你真想让我死?”
不同之前的谈笑,这句话说得尤为认真。
薛娘轻轻抚在他的后背上,没吭声。卫司感受着她冰凉的手,隔着衣裳一阵酥麻,勾着嘴角:“那我听你的。”
薛娘的手顿了顿,又听他道:“但是你得容我些日子。”
怎么说的她跟专门要人命的厉鬼似的。卫司听她不吭声,估摸着又想到别处去了,拽了拽衣袖,薛娘垂眼看他。
卫司说道:“你活着的时候,我曾说过要给你想要的。之前你不在身边儿,我也没心思去做。如今你回来了,不管以后走不走,我都要把答应过你的事儿给办了。”
薛娘明白了他的意思,弯了弯眼睛:“你真是闲得很了,多久的事儿还记得这么清楚。”
卫司皱着眉瞪她。薛娘唇边带着笑:“合着你这几天出去就是去办事儿了?”
卫司点头:“原先怕你知晓了,笑话我没出息,在意这些身外之物。”
又补充道:“现在也怕。”
他声调软的很,弄得薛娘心里直痒痒,伸手掐了他脸一把,下巴抬了抬,眼里透着笑意:“你这话把我想说的都给堵住了。成了,今儿也都说清了,走吧,睡觉去。”
卫司皱眉搂住她的腰不动弹。薛娘抿着唇作势要往外走,被他给拦住,有些恼怒:“都说清了,还走什么走。”
薛娘挑眉:“你这会儿心急了,之前可是连话都不主动说一句。”
卫司不作声,拽着她往炕边走。扯开被子盖在两人身上,拥着她带着凉意的身子,心里却暖和的很。天泛起鱼肚白,他的困意刚涌上来,下巴抵在薛娘的肩窝,沉沉睡去。
薛娘这些天一直在外面转悠,也困倦得很,挣了挣,反倒被他拍了一下,索性躺在他怀里把眼睛闭上。此时被他拥着,十分踏实。
事情说破,便无了隔阂。卫司做起事儿来也方便的很,不用再费心思瞒着薛娘。京里飞来的信鸽,他以往都是算着日子,一步不敢离开家里,就怕不在的时候,她看见信鸽腿上绑着的字条。
薛娘对这些头疼得很,直接跟卫司说,要不然施个法术让皇帝给他腾地方算了。卫司正拿着笔给封越回信,听见她的话,冲着额头弹了一下,还真想当祸害凡间的鬼了。
薛娘瘪瘪嘴,没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本就是想把卫司给忽悠到地府再说,等他们俩走了,这个世界恢复成原样。结果刚开了个头,他就说不行。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么讲规矩了。
封越传来张字条,让卫司去京里。事情有了转机,若是顺利,要不了多久,应是就成功了。
因着这个皇帝登基的时日不长,开始一两年还尤为勤政,过了段日子,许是用劲过猛,朝臣懒散,他也疲倦了许多,渐渐也成了昏君的模样。
百姓怨声载道,有许多大臣不服气,封越这些年一直在偷偷打点,就想着卫司哪天会回来。
所以这次,应当是能成的。
卫司立马收拾包袱,牵着马要走。薛娘挑明了说要跟着去。卫司不耐烦的很,嫌弃她碍事儿。被瞪了一眼,悻悻地低头,领着她走了。
路上的人瞧见,卫司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却撑着纸伞,抬头看了看天儿,日头好得很,哪儿有要下雪的意思。
用麻绳把纸伞绑在腰上,马背颠簸,纸伞一晃一晃的。看着尤为好笑。但凡是卫司经过的地方,皆能听见一片闷笑声。
薛娘的侧脸贴着他背后,弯着唇角,轻声说道:“出来转转,心里是舒服多了。”
卫司脸色难看的很,咬着牙隐忍。她不禁笑了几声,叫着他:“卫司,你不高兴么?这段日子,咱俩头一回一块儿出来。”
他低声斥道:“老实点儿!”
马以为在说它,疾驰的马蹄渐渐放缓速度,卫司气得嚷道:“谁让你老实了,快点儿!”
马蹄又变得快起来,薛娘在后面也应声。
卫司抿着薄唇,垂眼看了看她在胸口作怪的手,即使隔着衣裳,也仍然带起一阵酥麻。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你欠打是不是。”
薛娘眯了眯眼睛,手的动作停下,身子向前倾,拥着他。在耳边说道:“你这会儿可打不过我。”
卫司脸色阴沉,没吭声。
薛娘知晓他这是认怂了,低声笑了笑。他恼怒:“你笑什么?”
这回有薛娘作伴,卫司在路上没之前那么乏味。二人打闹一阵儿,就到了京里。没有再住上回的客栈,到了一处宅院。
早就有人在那儿等着,安排了房间,送了些膳食,又打来水,让卫司洗漱。为了掩人耳目,这院子里并无仆人,只有一个伺候的,还负责专门在封越跟卫司之间传话。
赶路好几日,满身尘土。卫司正在解衣裳的盘扣,薛娘瞧见了连忙背过身。他嗤笑:“有什么可避讳的,又不是没见过。”
薛娘:“就是没见过。”
卫司跳进浴桶,掬了把水洗脸,点着头:“对,没见过。应该是摸过。”
薛娘气得回头呸了一声,又连忙转过去。
在院子里待了一天,卫司跟薛娘正闹着,忽听门响。他神色一变,坐直了身子,整好衣襟,沉声问:“谁啊?”
门那边回话:“将军,是我。”
卫司起身把门打开,以防万一,他白天都是锁着门的。封越走进来后,压低声音与卫司说事儿,神情隐隐透着欣喜,想来事情进展的顺利。
卫司敛着眉头听了半天,这些朝臣倒是变得挺快,风向不对,马上就投了过来。与当年迥然不同,那个时候可是想尽了法子,也讨不到一声好。
封越见他神色不对,也知晓卫司在琢磨什么:“这些年皇帝昏庸,大臣早变成了墙头草,只要说舒坦话就能升官儿。”
卫司点了点头,又问:“刘迟那边……”
话没说完,封越连忙接上去:“您放心,他手里只有一部分兵权,想临时变了主意,那就是找死。咱们手里还握着他的把柄,不敢不听。”
“等事儿成了,该是他的东西,全都如数奉还。其他人我也都盯着,他们虽然掌握的兵权不多,可是把他们凑到一块儿肯定能成,还有原先您的手下,稍微一说,就投了过来,心里都念着将军。”
卫司“嗯”了一声。
事情商量的差不多了,天色也暗了下来。过了会儿,屋里端来了膳食,卫司看了封越一眼,他点点头:“今儿我没事儿,能留在这儿陪将军用膳。”
卫司垂眼看了看桌上的菜:“你家里怕是也做了这么一桌子菜,真不打算回去了?”
封越听他提到家里,脸上不由露出笑容,嘴上说道:“不碍的,就让她在家里等着。见天儿的回去,都吃腻了。”
卫司嗤了一声,摆着手,直接往外撵他:“赶紧走,少在我这儿显摆。这桌子菜刚够我吃的,你甭拿筷子,赶紧走。”
封越脸上带着笑应了一声。
门打开,又重新关上。躲在一边儿的薛娘伸了伸懒腰,坐到桌子前面,看着卫司烧香。她眯着眼睛闻了闻,香的很。
卫司见到她这副模样,说了句没出息:“平时在家里吃饭,我哪顿亏了你?”
薛娘撇撇嘴没说话,拿起筷子吃饭。
京城已经乱了,风声一天一变,传的都是有人要谋反。却弄不清是谁。皇帝只当是有人危言耸听,把一个冒死觐见的大臣给处死了。搂着怀里的妃子,笑的高兴。
刚得天下,谋反的势力已经都被除掉。谁能在这么短的时日,把他从龙椅上拉下去。
结果乐了刚两个月,晚上宫殿里载歌载舞,左拥右抱,忽听有人传,宫门失守,大批叛军进入。
那传话的侍卫身上带血,回了几句话,也咽了气。惊得宫殿里的妃子大喊,皇帝闹的心烦,又惊又怒,将怀里的人推开。拔出一把剑,将脸色煞白乱嚷的妃子给杀了。
顿时,宫殿里人人自危,拼命往外跑。
皇帝看着只剩下他自己的宫殿,还有地上的两具尸体,满脸不可置信。他像没头苍蝇似的,来回渡步。走到宫殿门口,拿着剑,忽又退回去,听着外面的刀剑碰撞的声音,惊惧的喘气。
门砰的一下被推开,皇帝脸色灰白。卫司领着人进来,神情严肃,抽出剑,抵着他的脖颈:“你昏庸无道,残害忠良,对待百姓如同畜生。落到今日的下场,你可还有什么要说的?”
皇帝也是会些拳脚功夫的,只是近些年,只顾着玩乐。身子虚的不行,稍一动弹就满头大汗,看着脖子上的剑,冷笑了一声,自个儿撞在上面,抹了脖子。
卫司看着淌血的剑,和皇帝未合眼的尸体,神情有了一丝恍惚。封越见势跪下,高声喊道:“将军有治国之才,深受百姓爱戴,请将军登基。”
卫司没应声,封越又喊了一遍,其他人也跟着喊。他这才说道:“此时只宜监国。其余事过些日子再说。”
封越一愣,虽说监国也是掌皇帝的权,可到底不是皇上。闹不清卫司怎么想的。
宫里经过四次到大变,人心不稳,卫司先后下达了许多命令,都是为了安抚人心。他搬进了宫殿,桌上摆着许多奏章,常常批改到深夜。薛娘在一边儿看着,也不知说什么。
她到了晚上都不敢出宫殿,生怕撞见鬼。只好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睡觉,可脑子清醒得很,全是愁事儿。
卫司要是变了主意怎么办。
他这段日子尤为上心,看着奏折神情严肃,若是跟他说一句话,就像是没听见,压根儿不理你。薛娘接连叹气,想开口问他,又不知道怎么说。
总不能上去问,你怎么还不自杀。
整天眼巴巴地瞧着卫司。过了几天,有人来求见,说了一大堆官话,才进入正题。想让卫司充实后宫,他如今一个女人也没有,应该多纳几位妃子。
薛娘在一边儿听得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卫司用余光看着薛娘,嘴角向上弯着。那大臣还以为自个儿说的正好对上卫司的心思,不由多说了几句。
等纳了妃子,就该选皇后,定要选一位贤良淑德的才好。絮絮叨叨了一大堆,听得薛娘耳根子烦,卫司反倒脸上带着笑,任由那人说下去。
薛娘走到卫司身边,伸手掐他胳膊。
卫司眉头都没皱,往椅子上一靠,抿着唇等大臣把话说完,中间时不时地点头。这么点事儿竟然说到了下午,薛娘也不看卫司了,直接背过身去,什么话也不说。
卫司瞟了她一眼,清清嗓子:“行了,你说的我都听见了。此事以后再议,我如今只是监国,哪儿就能纳妃。”
大臣还要再说,刚开口,就见卫司的神情不对,连忙噤了声退下。
门关上后,卫司拽拽薛娘的衣袖,凑过去:“还气着?我可是一口回绝了,对你我可是一条道走到黑。”
薛娘扭过头不忿:“谁让你走了!找别的路去。”
卫司连忙轻声哄着:“我这不是见到你为我吃醋高兴么,我错了成不成。平日里你都没这么在意我。”
薛娘要辩解,又听见外面有人喊,她冷了脸又背过身去。进来的是封越,卫司神情缓和:“事儿都办好了?”
封越应声,从身后背着的布包里拿出来一块空着的牌位。然后呈到卫司面前,再退下。
卫司垂眼看着,提起笔,忽然顿住:“名字。”
封越连忙道:“听以前的弟兄说,姑娘的名字是……”
卫司打断,声音温和:“名字是什么。”
薛娘歪了歪头,看了一眼,没转过身子,语气仍不好:“薛娘。”
凶巴巴的两个字灌进耳朵里,卫司弯着眼睛,在上面书写。
吾妻薛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