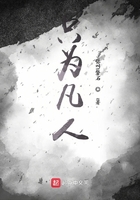她是医疗队防控组的成员,她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保证环境清洁。多年的职业养成,使她对职责和使命具有极强的捍卫意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看到生命受到威胁,第一时间就会冲上去抢救,这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本能。所以当她面对那样的情景,她怎么可能坐视不管,无动于衷?
那么,她做对了吗?她不知道。
这是38岁的秦玉玲平生第一次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确切的判断。她仿佛陷人了一个循环往复、永无终点的悖论,单独看起来每一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可是一旦相互叠加,彼此印证,所有的答案又都是错的……那一日,她少言寡语。
回到住地,她找到防控组组长贾红军。
她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贾红军说,你做什么了?
她说,我去处理病人呕的血了。
贾红军有点吃惊:你自己动手处理的?
她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要亲自去做?为什么不安排保洁人员做?如果养成了依赖习惯,以后这些事情他们可能都不去做了,那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
秦玉玲申辩道:我叫他们了,但是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进去。他们肯定是害怕,这是第一次出现病人呕血嘛……贾红军说,好吧,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秦玉玲就把她处理的过程仔细地说了一遍。80后的贾红军虽然在年龄上小她几岁,却是医院感染控制科技术实力很强的主治医师,是从事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和病例监测方面的专家,曾多次参加全军、全国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在2014年5月的首都联合防空演习中,还被任命为防疫组组长。在传染病防控和消毒方面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并因此受到多次嘉奖。这个时候,她需要得到贾红军的认可。
听完了她的叙述,贾红军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啊,应该没有问题。末了,又想起什么似的回头叮嘱了一句:哎姐,没事儿啊,放心!
秦玉玲嘴硬地说,我不担心,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一下这件事。
这时候,已经是10月5日的晚上。
此后的日子变得好慢好长。
那之后,贾红军没再提起过这件事,好像他已经忘了。可秦玉玲却始终无法摆脱掉那个关于对与错、是与非的悖论的纠缠。但是,每当自责和不安占上风时,一个声音就会从内心深处挣扎着升腾起来:我不会被感染的,我是专业的啊!我怎么会被感染呢!
我是专业的!一这是那段时间,她内心里最坚实可靠的精神支柱。
曰子就这样很慢很长地过着。
又是一个晚上的时光,在大家从食堂吃完晚饭各自返回宿舍的路上,贾红军追上了秦玉玲。
哎姐,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解除了!没事儿了啊!
秦玉玲愣了一下:啊?什么解除了?
但是没等贾红军答话,她已经明白过来,噢——
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是2—21天,通常情况下,接触过病毒感染者的人要被隔离21天,也叫21天隔离期。而这一天是25日,距离她贸然冲进病区亲手处理病人呕血已经整整20天啦,明天就是第21天!是埃博拉潜伏期的最后期限!
泪水瞬时间模糊了她的眼睛:哎呀,红军,你真是的!你还记着呢……是的,贾红军记着呢,他没有一天忘记过。他和秦玉玲一样每一天都在数日子,数着那个要么毁灭、要么重生的21天。
这21天真的是好长好长啊……随着疫情加重,病人的数量开始急剧增长。
这天下午,医疗队突然接到塞国埃博拉疫情指挥中心的紧急通知,一小时后,将有12名埃博拉疑似病人被转运过来,请他们做好接收准备。自留观中心开诊以来,还从没有一次接收过这么多病人,靠现有的值班人员肯定无法承受,李进闻讯后马上带领正在轮休的两名医生和3名护士急速赶往医院驰援。
护士陈素红手脚麻利地穿好防护服第一个冲进了病房,眼前赫然的一幕把她惊呆了:两名刚人院的重症患者瘫倒在病床上,掺杂着血液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喷溅得到处都是,散发着难闻的恶臭。这是埃博拉患者的典型体征!或许也就是一秒钟的犹豫,十几名医护人员马上兵分两路,各司其责,医疗组接诊、安置病人,防控组消毒清理现场。
接诊工作从下午5点开始,等到一切安置就绪,队员们筋疲力尽地走出病房,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随着重症病人越来越多,病房里种种触目惊心的场景,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而且,死神早早地降临了。
这一天是10月3日,留观中心开诊后的第三天。第一个去世的就是留观中心开诊第一天和妈妈一起入院的那个最小的8岁男孩卡比亚。
塞中友好医院没有太平间,卡比亚去世前一直和妈妈住在一起,这时候医护人员只能将他从妈妈身边带走安置在一个单独的病房里,等待政府的收尸队来将他带走。
在埃博拉之前,因为宗教原因,塞拉利昂一直实行土葬。其时,族人们要聚在一起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在一番载歌载舞和宗教仪典之后,亲人们要按照古老的习俗逐个地跟死者拥抱吻别。人们万万不会想到,恰恰就是这个古老而又温暖的习俗成了“非洲死神”埃博拉的帮凶,往往因为一个亲人的去世,进而招致更多亲人随之而去,有时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庄,就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被灭绝。
为此塞国政府刚刚制定了一套强制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此期间所有死亡的病人,民众不得擅自安葬,需由政府组建的专业收尸队统一处理,如果确定是埃博拉,将被拉到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焚烧;如果不是埃博拉才可由家人选择自愿带走自行安葬。
可是,在首都弗里敦总共只有六辆救护车,在医疗队开诊之前因为超负荷运转已经报废了两辆,剩下四辆车由塞国卫生部疫情指挥中心统一调度,不仅要运送病人还要收尸,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卡比亚去世的第一天,收尸队没有来。
第二天下午4点钟,收尸队来了,却因为门卫没有及时给他们开门,又走了。
门卫由政府派遣的军队负责,军人们在上岗之前普及过简单的防护知识,知道埃博拉的厉害,虽然不用直接接触病人,但每次开门的时候也是要穿防护服的。之所以没有及时开门,是因为值班的士兵刚刚为运送病人的车辆开过一次门,已经穿过一次防护服了,他要半小时以后再工作。就让收尸队在外面等。可收尸队5点钟就要下班了,他们不肯等,于是开着车就走了。
这一切,医疗队是在收尸队的车来了又走了之后才知道的。因为病区的大门和医护人员进出的门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二者之间相距几百米的距离。
这时候在安置小卡比亚的房间里,已经又多了一具尸体。
埃博拉病人的遗体本身就是最可怕的传染源,加上天气湿热,尸体很快会膨胀腐烂,长时间存放在病房里,无论对病人还是医护人员都是极大的威胁。
这下子不仅队长李进着急了,整个医疗队都着急了,连塞方的卡努院长也着急了,病人们也开始骚动不安起来。李进当即让后勤组工程师高磊在能看见大门的地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又给门卫配了一个对讲机,再三嘱咐门卫如果收尸队的车再来,一定要向院方及时通报。
当天晚上例会的时候,李进又做了两项安排:一是让医疗队教导员孙捷第二天一早就带着翻译王姝去塞国卫生部协调,请塞方务必及时安排人转运尸体;二是让医疗保障组组长郭桐生次日早上一上班就和卡努院长一起在医院里守候收尸队。
卡努院长是一位外科医生,在塞国医学界拥有很高的威望,大致相当于我国一个院士的地位,是塞国极少的著名外科医生之一。而卡努院长是在中国读的大学本科和硕士。换句话说,这个塞国医学界的重要人物卡努院长是我们中国培养的。所以卡努院长不但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还说得一口比较流利的中国话。
而保障组组长郭桐生是三〇二医院临床检验医学中心门诊检验室的主任,曾经到美国进修过一年,在医疗队里他的英语水平是数一数二的。跟收尸队打交道英语是必需的。
第三天早上一上班,又有两个病人去世了,这时候小卡比亚的房间里已经有四具尸体了。
这一天,李进也一直在医院里守候着。
四具埃博拉病人的尸体,停放在留观中心的病房里,最长的已经整整停留了三天,李进的心里仿佛压着一座大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山变得越来越沉重,几乎让人崩溃。其实这座山何止是压在李进一个人的心上,此时在留观中心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这座大山压得透不过气来。
就在李进和大家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下午临近下班时分,通过医院大门口的监控视频,他们看到有救护车正在驶近,一干人等赶紧向楼下跑去。
因为办公区和病区之间有隔离栅栏,他们只能远远地看到病区大门的地方。确实是收尸队来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看到他们又在跟门卫交涉,李进急了,一时顾不上斯文冲着门卫大喊起来:让他们进来!一定要让他们进来!
恨不得用手拉住他们不让他们走!事后李进这样说。
郭桐生也急了,说院长别着急,我去!他来不及穿防护服,只戴了个口罩就跑到大门口,把差点又要离开的收尸队给拦住了。
收尸队队长说:你们没有给我们死亡清单。
什么清单?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需要清单。郭桐生一头雾水。
自从医疗队抵达弗里敦以来,塞国政府只是不断地催促留观中心尽早开诊,却从未将有关的医疗政策和埃博拉时期相关规定和医疗队沟通过,因此医疗队一直以为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有人来把尸体收走。
队长说:就是病人的死亡证明,需要有一个清单,我们要有那个清单才能把尸体拉走。
队长说着就又要走了,下班的时间又快到了,毫无疑问,缺少手续,他们是不可能把尸体拉走的。郭桐生快要哭了,他知道他决不能让收尸队走掉。
郭桐生说:我们从中国不远万里来到你们国家,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需要你们来帮助我们。现在病人的尸体已经在病房里放了好几天了,如果你们不肯帮助我们,尽快把尸体拉走,那我们又怎么能更好地帮助你们呢?
收尸队长其实一直很友善,见郭桐生急成这样,就表示说他很理解,但是他也有他的难处,他只有拿到清单才能把尸体拉走。
郭桐生说:你们的这些程序没有人告诉我们,你说的清单什么样子我们都没有见过,你现在把清单给我,我马上去填,麻烦你们进去收尸体,我很快就把清单填好交给你。
这回收尸队长同意了。
郭桐生拿到清单,赶紧跑去找卡努院长把死亡清单填上。可是,有一个病人刚人院就去世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收尸队长说:那这个不能收。
―共四具尸体,再留下一具,那不是跟没收一样吗?然而收尸队长态度坚决。
郭桐生快要气馁了,他觉得他把好话都说到头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让收尸队长改变主意,这时候他脑子里突然跳出了两个字:小费!对,塞拉利昂是个小费之国,或许小费能帮上忙。可是医疗队到塞国以后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小费,郭桐生就跑去请示队长李进,李进想了想就同意了。
可是,当郭桐生拿着20美元去给收尸队长的时候,收尸队长却不肯收,当然也不肯带走那具无名尸体。郭桐生自然不肯罢休,想想或许卡努院长能说服他改变主意呢,他们毕竟是自己同胞,就说:那你跟我一块儿上去见见卡努院长吧,卡努院长很想见见你。
卡努院长毕竟是有威望的,收尸队长没有拒绝。结果是卡努院长跟收尸队长聊了一会儿,收尸队长收下了20美元小费,然后把四具尸体全都拉走了。
郭桐生终于松了一口气。事实上,这时候留观中心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郭桐生说:我印象特别深,尸体拉走之前我们队长脾气特别大,整天脸上紧绷绷的,特别严肃,等看到最后一具尸体拉走了,他脸上一下子就有笑容了。那是三天以来,第一次看到他笑。到塞国以后,因为大家天天在一起,界线也没有在医院时那么严格了,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李院长这三天第一次看到你笑了!
是的,三天来李进第一次笑了,压在他心头的那座山被收尸队长带走了,被收尸队那辆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因超负荷运转而报废的救护车带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弗里敦多日阴云密布的天空竟然也开始放晴了。
后来李进就跟郭桐生说,你把收尸的事情管起来吧,这个得专门有人管,看来收尸还是一件大事。
李进说的没错,收尸的事情果然是一件大事。
解放军医疗队第一批队员总共在塞国60天,开诊46天,接诊埃博拉疑似患者274人,死亡86例。这在正常医院根本是难以想象的。
埃博拉一一“非洲死神”真正是当之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