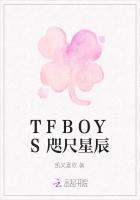挑剔和质疑,中国声音,示范作用,国家的底气
相比起王姝从记事本上划掉的日子,李进的每一天都要更沉重,更漫长。
作为医疗队主帅,总部首长在出发前夕亲自交付的四项任务时刻铭记在心。那么,如何才能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正像李进自己说的那样:当医疗队从首都机场一上飞机,全世界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呢。因此,他要求所有队员必须树立一个信念:在塞拉利昂,我们每一个人的形象,都代表我们国家!
此时的塞拉利昂,犹如一个偌大的国际竞技场,为了围剿“非洲死神”埃博拉,国际上各方医界精英不约而同地汇聚而来,仅在首都弗里敦,就有世卫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英国“救救孩子”慈善组织、世界儿童基金会、美国疾控中心,以及古巴、南非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以不同的形式抗击埃博拉。其中以英国的力量最为强大,除了英国政府卫生机构的派出人员,另有三个非政府医疗救助组织,同时在塞国工作。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同台竞技。
起初,国际上对于埃博拉的认识存在着很多误区。
由于对埃博拉所知甚少,一些欧美国家的医生在最早进入西非的时候高度自信,根本不把埃博拉当回事。正像我们的医疗队去各国的诊疗中心参观时,让秦恩强深感惊愕的那样,他们疏于防护,甚至在几乎无防护的状态下和埃博拉病人亲密接触,从心理上根本不把埃博拉当回事。
随着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他们又迅速地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盲目乐观一下子变成极度恐慌,转而制定出过于严苛的规则,甚至出于对医务人员的保护,禁止给埃博拉病人输液,致使大量病人因严重脱水迅速死亡。结果死亡人数的急骤增加,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对埃博拉的恐惧。
如此恶性循环不断叠加,恐怖的气氛逐步升级,再通过各种记者招待会、发布会,由各方媒体不断放大,埃博拉立刻就被妖魔化了。
美国一位著名疾病评估专家面对媒体镜头这样描述埃博拉:
埃博拉疫情大多从单一病例开始,村里有人生病了,把病传染给照顾他们的人,最后有人被送进医院。
然而非洲医院没有手套、手术衣或者口罩,正是散播病毒的绝佳环境,疾病会这样传下去,直到医院里的人死光离开为止。
在世人的眼里,塞拉利昂乃至整个西非无异于现实版的人间地狱。
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欧美援助,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座帐篷医院要建几个月,开诊半年的医院只接诊过几百人次。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医疗队的抵达,真正是万众瞩目。
一周时间改造出一座相当严谨规范的传染病院,不到两周时间,从零开始培训出87名合格的传染病护理人员,这是医疗队向国际社会交付的第一张考卷,这是一份成绩相当优秀的考卷。
但是,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对这支来自中国的专业队伍,起初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度的,有的甚至以专业考评的名义到塞中友好医院指指点点,提出各种质疑。
难道我们的专业水平真的存在差距吗?这是解放军医疗队第一次问鼎国际竞技场,不能不承认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的确有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中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竞技场亦如战场,李进决定带着我们的专家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他们先后去了英国、南非以及塞国当地的几家留观中心和治疗中心,参观之后,李进非常自信地对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和英国同行说道:你们在传染病基础研究方面,确实是走在世界前列,但是我认为近几十年,你们没有遭遇过大规模的烈性传染病,你们缺乏实战经验。而我们中国经历过“非典”,经历过禽流感,在这方面我们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当时一个以老大自居的外国机构,用红灯、绿灯、黄灯作为评判标准,在弗里敦给各留观中心和治疗中心挂灯打分,当他们要给塞中友好医院挂灯时,李进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李进说:在弗里敦任何人没有资格给我们挂灯,如果你们是来参观交流的,那么我们欢迎,但是按照国际准则你们要提前预约,否则恕不接待。
挑剔和质疑甚至会发生在具体的病例上。
10月8日,留观中心开诊刚过一周,从美国疾控中心传来消息,说一个从我们留观中心出院的确认为阴性的病人,到了另一家外国留观中心检查后,却被确认为阳性。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将是整个西非抗埃战场上的一个丑闻。李进带领医务人员立刻展开核查,结果发现,我们留观中心第一批出院的病人是10月6日,而对方10月8日就做出了新的确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埃博拉的最快的检测周期为三天。所以只能是对方搞错了,绝不可能是我们误诊。
国际竞技场,竞技,也竞智慧,竞谋略。
专业流程一在采访中,我听不只一个人说到这个词,秦恩强在改造病房楼的时候说过,秦玉玲在处理病人呕血的时候说过,李进队长在讲到零感染的时候也说过。这四个字在传染病防护中似乎显得格外重要,似乎只要严格执行专业流程,就可以将病毒拒之门外,就可以将传染链一斩两段。事实正是如此。
那么,对任何一个这样的流程的改变就显得非同小可。
塞国国家卫生部下辖七个小组,其中一个叫病案管理小组。这个小组实际上是塞国抗击埃博拉的指挥中枢。
病案小组的工作方式是以例会的形式展开的。
例会一周两次,参加例会的人员还包括所有在弗里敦参与抗击埃博拉的外国医疗机构和组织的代表。与会者在例会上研究讨论与埃博拉有关的各种问题,从埃博拉时期国家的宏观政策、机构设置,整个医疗体系的运转程序,各留观中心、治疗中心的职能范围、医疗责任、床位设置、标准工作流程、后勤保障,以及社区看护中心的设立、分工等,到一辆救护车如何使用,才能既保证病人的及时转送,又避免病人与病人之间、病人与司机之间的交叉感染……诸如此类,都是在这个小组里起草、讨论、制定,然后上报国家卫生部紧急医疗委员会审批,继而在全国推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病案小组是塞拉利昂在埃博拉时期点亮希望的一盏明灯。正是因为有了病案小组的努力,混乱无序、濒临崩溃的塞拉利昂才得以逐渐步出绝望的深渊,重拾信心。
解放军医疗队被派去参加病案小组例会的人,是医疗保障组组长郭桐生。
医疗队出征的时候,离郭桐生的不惑之年只差两个月。
前面说过,郭桐生是三〇二医院临床检验医学中心门诊检验室的主任,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身上的那种颇为显眼的军人姿态,专注、干练、身姿挺拔、相貌俊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加朝气、年轻,而且帅气。事实上,我觉得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胸有成竹的军事干部。
在医疗队,他负责过的工作遍及医疗保障的方方面面,比如培训、收尸、检验标本的釆集和配送等等,以及和医疗有关的对外联络。
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郭桐生喜欢用数据和百分比说话,而且极富条理。
对于病案小组的例会,他发现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不可忽视。
其一,医疗队在塞国所有的一切,从医疗活动到后勤保障都跟这个小组关系密切。通过这个例会可以非常及时地把医疗队的情况反馈给塞国有关部门,并及时得到解决。
例如医疗队刚到时,没水、没电。没电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发电,没水我们就自己建了储水罐,然后想办法从水务公司买水。后来,他把这些问题反映到病案小组的例会上,塞国政府就开始专门组织人员来解决后勤保障的问题,再后来,医疗队的用水就有了保障,水务公司每天按时把水送来,而且不用花钱买了。
其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国际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在例会上参与各种标准程序的制定,向世界发出我们中国的声音。
当时,关于各诊疗中心的标准操作程序正处在起草和酝酿阶段,在这个会上,郭桐生代表解放军医疗队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建议。
一个就是要向所有的医务人员特别强调“脱防护服比穿防护服更重要”,这是医疗队员们从亲身实践以及一个个血的教训中得到的宝贵经验。
当时,在整个弗里敦通用的是参照无国界医生组织经验,由世卫组织推行的埃博拉防治标准操作程序。其中对于脱防护服的程序,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时正值10月中旬,是埃博拉在塞国暴发的顶峰时候,也正是塞国医护人员感染的高峰期,平均每天有两名医护人员因为感染而死亡,一个星期就有14名医务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就包括杰出的协调官蒂莫西。这是塞国抗埃历史上最黑暗最危机的时期,甚至于超过了以往战争频乃的内战时期。这个关于脱衣流程新理念的提出,立刻受到许多外国同行的重视和赞许。
医疗队提出的另一条建议,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起初塞国政府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规定,埃博拉疑似病人必须经过两次检测确定为阴性,才能出院。一个标本的检测周期为三至五天,即使以最短的三天计算,病人也要留观六天才能出院。这无形中增加了病人之间交叉感染的几率,对于不守规矩不服管理的塞国病人就更是如此。
根据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发现,如果病人出现症状在三天之内,经埃博拉病毒检测为阴性,并不能确保棑除疑似,三天之后再检测还有可能为阳性;如果病人出现症状超过三天,检测为阴性,基本上就可排除疑似。鉴于这一规律,医疗队提出凡出现症状超过三天检测为阴性的病人,不需再做第二次检测,应立刻放其出院,以减少再感染的机会。
这个建议,得到了美国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的采纳,塞国病案小组也把这个新标准写进了“塞拉利昂卫生部留观中心标准操作程序”,在塞拉利昂全国施行。
遗憾的是,我方关于强调脱衣流程的建议只是得到了外国同行的广泛认可,最终却没有被写进留观中心标准操作程序。究其原因,似乎是因为塞国政府方面更愿意尊重世卫组织原有的程序。
不管怎样,对于国际抗埃同盟来说,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不然的话,它将会在非洲挽救许多医护人员的生命。它甚至可能在未来当人类遭遇更可怕的生物威胁的时候,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才真正是全人类的福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