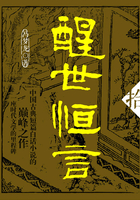假如我对大家说我父亲在不到二十岁时,就已经觉得“够本”而对死亡问题安之若素,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甚至还可能以为我满口胡诌或者是对我父亲的一种调侃,但我仍要一千个保证说:这是完全真实的。时间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我父亲是一个解放战争中的“红小鬼”,他出生在我的老家胶东半岛解放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和家庭都受尽了欺负。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花费笔墨来“忆苦思甜”,也不想全面地写父亲的经历,只想简括地说他最早嗅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气息”,而且在正式穿上军装之前就全身心地投入当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革命活动,并在十三周岁(按农村的虚岁是十四岁)上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是在连队当通讯员:随后不久,就被选送到机要训练大队学习密码电报业务。这里必须说明一下的是:许多人都将干密码电报的机要工作误以为是手指拍电报的“嘀嘀哒”,其实不是。至于究竟怎么弄,因是绝对机密,我父亲对谁也不说。他的嘴可严哩,说是叫做“守口如瓶”。
父亲在1950年秋天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就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了第一、二、三次战役。开始在兵团机要处,后来因为战线延长,部队分散出击歼敌,他又被派到师里任机要组长。你猜那时他多大?才十五周岁。信不信由你。但部队首长信任他。有一次来了加急电报,师长在前沿阵地指挥,政委派他由通讯员驾驶吉普车将电报送给师长。去时还算顺利,归途却遇上美机“油挑子”(即F84雷电式)疯狂扫射。他们乘坐的吉普车被打得起了火,通讯员当场牺牲。我父亲左腿负伤,幸而被“三八线”附近一个村庄里的“阿巴吉”姜大爷救了回来。姜大爷懂医道,又会汉文,能用笔交流。父亲在姜大爷家里疗养了一周,伤势好转时才与这位异国长辈洒泪告别。不仅如此,姜大爷为了给我父亲证明他没有落入敌手,还用汉文给他写了“字据”,由我父亲回来交给部队首长。只是成为终生憾事的是:停战后姜大爷那个村庄划在非军事区以南,注定再也无法与他相见。我父亲每当想到此,直到古稀之年还哭得泪人一般,而且常常边哭边说:“我这条命是好心人捡回来的。我后半生还有啥不能舍的?”
首长为了爱护他的身体,叫他到后方医院继续休养,这才保住两条腿基本无碍。
正在这时,华东沿海驻军的一位首长参加赴朝慰问团归来时经过东北,参观后方军医院,有缘与我父亲聊了一会儿。他很喜欢眼前这个“小孩”,就跟父亲所在部队的首长通了电话:“老战友,我分管的机要处缺译电能手,你就把小史借给我吧,行不?”对方沉吟了一下,说:“你喜欢就归你吧。不过,你可不能对他‘冷处理’呀!”“哪能呢?我要是慢待他,你回国见了面,还跟在沂蒙山那时候一样撴我的耳朵!”
这以后不久,我父亲就被转调至一个军区司令部的机要处,并被安排至很重要的台务组当组长(这个组的原组长提升至一个军分区任机要科长)。在随后的两年中,工作极其繁重,电报收发量成倍地增加,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的推推拉拉,再加上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还要在工作间隙中学习业务,提高工作效率。十几岁的他正在长身体阶段,却日夜处于“拼”的状态。今天的人们简直难以想象,他在一整年中几乎没睡一个囫囵觉。有时深夜时分刚刚处理完一拨电报,回宿舍躺下才合上眼,通讯员又从电台拿来新的电报,拍着他的脑袋喊:“起来,起来,特急的!”几乎连眼都来不及睁开,一骨碌翻身而起,毫不迟疑穿上衣服,急匆匆赶到办公室,又在灯下开始了工作。就这样不知不觉干到天亮,连早饭也顾不上吃,想回宿舍“迷糊”一会儿,可前脚刚迈出办公室门槛,后脚只好又收回来。因为,办报科的送报员彭大个儿又端着一寸厚的电报稿,都是“加急”的。那时的译电员有的也发点小牢骚:“彭大个儿是个催命判官。”不过,说归说,活儿该干还得干。于是,铅笔尖像蚕儿吃桑般地在电报稿纸上低吟浅唱起来:“喳喳……喳喳……”一唱又是一整日,直到西天太阳西斜。
星期日,没有星期日。偶尔有那么个把的星期天半天无电报,父亲必先抓紧记码子,他说他恨不能把新换的“本子”一口气都吃在脑子里,这样工作效率就会成倍地提高。有一天上午,他正在专注地记,没有听见詹副处长走近,拍着他的后脑勺说:“就这里头装着三千组码子呀!”领导的赞赏让他措手不及,反而像“有罪不敢抬头”似的只顾脸红不知该说什么。
就这样,工作效率真的成倍地提高,而病菌却悄然地向他的肌体无情地袭来……
忽有一天,译电科宋科长无意中发现我父亲办公桌内下角地上有一堆炉灰,好奇地拿煤铲扒开一看,呀,那是一口口的血痰,有的已经干涸,有的还是新吐的。原来,父亲早已累得吐血。为了“轻伤不下火线”,他怕叫同志们看见,也为了瞒着领导,就悄悄拿煤灰盖上……
宋科长平时非常和气,这时却一脸严肃:“小史,我要批评你,马上停止工作,到犀牛山军区医院去好好检查,明天就去!”
“台务组的工作……”父亲还在犹豫。
“叫小李顶上去,我给他打下手!”科长的话号令如山。
领导的命令是不能违拗的。第二天,一个叫史凌空的副连级干部由省城踏上奔赴犀牛山军区医院的行程。犀牛山,距省城西南二十华里。此时早春的凉风扑向他的面颊,如果有镜子的话,他会看到自己的双颊潮红。其实,他早就感觉自己具有明显的肺病症候:过午发烧,面颊潮红,咳嗽,吐血。这些都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他自己不说,同志们也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谁也顾不上注意这些。
此刻,他虽然身穿军大衣,可是仍觉得有点单薄,但他脚下生风,丝毫没有减慢几年行军练就的步履。一切结论都取决于两小时后X光的结果,他懂得,科学的验证是不容置疑的。
他挂过号,等待叫号,透视,并随拍片子。
在等待透视结果时,父亲说他当时的心里还是有点忐忑。虽然已有七八成的底数,还是心存一线希望——侥幸不是肺结核。
“史凌空!”随着护士的一声喊,尤其是递来的二寸长的一张单子,命运基本已经确定,“左肺二、三肋间浸润性肺结核。”虽然后面打了一个疑问号,但患者本人已不再心存侥幸。尽管他被告知一周后再来看拍片结果,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履行一下程序而已。
说来也怪,他平时本来还是有些紧张的,但当得知“逆耗”后,心情反而平静下来。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那一段的心理活动是他一生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他没有因为身患肺结核而悲伤和害怕。尽管在那时肺结核作为“痨病”几乎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也似乎没有“神仙一把抓”式的特效药;即使有雷米封、链霉素之类的外国药,也不知是否进入我国;即使有进口,恐怕也轮不到像他这样级别的小干部。但他仿佛并不在意这些,因为他想的是:
“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已经超过了十八岁。所谓‘三十而立’,那是‘孔圣人’说的,在我们老家,十八岁已算成年,作为一个男人,已经可以立门户。既然已经成年,那么来到这个世上,转了一圈也算值了。何况在这十九年当中,没有让生命白白流过——当通讯员时立过一次三等功;在朝鲜战场掩蔽部被打着了,还冒死译完特急电报,准时传达了志司的重要指令,立了一等功;回国后因两次打破全国机要译电新纪录,受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令嘉奖,立二等功一次。而且参加了全省团代会,与不少著名的劳动模范一起被授予全省模范团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既然这十九年没有白过,死了也算值了;更何况在三年之前已经尝到了死亡的滋味,也就是因为命不该绝,这条命才被好心人拽了回来。这次如果因为这场病而……也算够本了。”
没有人这样提示过他,但“够本”这个概念一直萦绕在父亲的心间。当得知自己确实患上了肺结核这么个难愈的病,反而轻松了。一般人听了很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父亲就是这么想的。因此他反而解除了似是而非的“嘀咕”,卸掉了精神负担,任体温升高,面颊潮红,归途上他甩开大步,更加强劲的风扑面而来,他索性解开棉大衣的扣子,就像张开翅膀的大鸟,迎风劲飞……
一周后,他又一次来到犀牛山军区医院。胸片确证,如透视无异,医嘱先全休三个月,“注意加强营养,发烧期间减少活动”。至于药品,没有开,更没有特别医嘱。回到处里,父亲将结果及医嘱的单子交给宋科长。细心周到的宋科长早就有所安排,他相中了处办公区对面的一所小荒园,原先曾是机关人员参加劳动的菜地。后来发现地有盐碱,蔬菜枯黄,就停止了使用。而在菜园旁边,有两间厢房,是原来放置农具的所在。宋科长叫公务员整理打扫了一番,里外两小间,恰好做史凌空和同期检查出结核病的另一位译电员张志忠的休养之所。
搬家那天,宋科长特地帮着他俩搬铺盖和书籍。他操着典型的晋中口音开导着两个年轻的病号:“既来之则安之,养病最主要的是心胸开阔,放下包袱,就像打仗一样,病魔就是敌人,要有压倒它的气势,还要有耐心,急躁不得。”他接着分头嘱咐,“小史要放下对工作的挂牵,台务组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说句好懂的话,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你就放心好了。小张嘛,主要是开阔心胸,养病嘛,就像在大海里游泳,千万不敢小心眼啊!”宋科长很擅长做思想工作,嘱咐完了,那颀长的身影才离开小厢房。从窗户向外望去,他习惯地将两只手背在身后并抄在一起的标志性动作,是永远留在我父亲心中的。
于是,史凌空和张志忠这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他们安静而寂寞的休养生活。
头几天他们各自看他们喜欢的书籍。张志忠在外屋,看的是最新出版的作家杨朔创作的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而史凌空看的是以前看过不止一次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者也许是觉得新鲜;后者分明是为了鼓舞与病魔做斗争的斗志。
但过了不到一周,大小史一岁的小张的情绪就起了明显变化,他有时愣愣地看天花板,一声不吭,本来就比较内向的他变得更加沉闷;有时他则长吁短叹,在地上忙乱地踱着圈子。小史看在眼里,开始也不吭声,后来终于难以保持沉默:“哎,张自忠!”他打趣地称呼小张为那位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在此地,“志”与“自”是音同字不同。小史怕小张没有领会他是出于逗趣,又叫了一声:“荩忱将军!”因为张自忠将军字荩忱。这么一喊,小张不禁开颜而笑了。
“荩忱将军,你得拿出大将军的气派!区区小病,算啥?别东想西想的,养好了病再说。医生不是说叫加强营养吗?咱们的津贴费够了吧,中午饭到食堂吃,什么炒腰花、爆三样、熘肝尖,啥合口吃啥!贵点儿也认了。晚饭要不咱俩到大观楼市场饭馆去吃?不管怎么说,我这副连级的津贴费比你那正排多一点儿,理应我请客。”
“荩忱将军”点头了。
从此,他俩基本上是出双入对,下饭馆,看电影,也符合机要人员必须二人以上通行的规则。史凌空事事征求张志忠的意见:“你最喜欢吃啥?”
“好吃不如饺子。”
“那好,我侦察了一下,大观楼市场西南角有一家父子饺子馆,那里的韭黄饺子太盖了,不信去尝尝?”
张志忠答应了,一品尝,果然其味鲜美。也许为了俭省一点儿,他们每次每人三两水饺,但都要韭黄的。于是,那家跑堂的“公子”白手巾往肩上一搭,向操作间一喊:“韭黄六两啰!”
但二十多天后,小张就吃腻了。小史的食欲却始终不减。后来他俩只好在“二人同行”的前提下,各进了一家饭馆,然后在大观楼影院门口聚齐,再一同回来。这时小史注意到:尽管有言在先,他多花些钱请小张,可到头来一回想,他俩付钱的次数只差一次,这足以看出这位“荩忱将军”打心眼里不爱占人“便宜”。
一个月后,同去犀牛山军区医院复查,史凌空左肺上的病灶已明显缩小:而张志忠同是左肺上的病灶却依然如故,医嘱继续休息。这次回程的路上,小张始终情绪低沉,任凭小史怎样逗他,他也振作不起来,显然是产生了更大的思想压力。而小史在养病中则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对于“压力”,甩掉它!豁出去!六字真言看来行之有效。
这次回来,小张天天躺着,就像是添了新病,有时连中午饭也懒得去食堂。小史为他打饭,终于感动他开了口:
“你当然想得开,年纪轻轻的,东挡西杀,直面烽火战场,不枉人生一世。可我算什么呢?本想也像样地****一场,像《水浒传》里杨志说的:在边关上一枪一刀,虽不说是封妻荫子,总也不辱青春,却想不到又得了这么个讨厌的顽固的病,啥时是个头!”
小张说出了心里话,小史才比较豁然,他建议小张对宋科长诉一诉,看他有什么想法,总是要依靠组织嘛。小张本就白净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凝视着窗外的夕晖说:“宋科长对咱们还是挺好的,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愧对他,自己好没长进,羞于向他讲呀!”
“这没必要。”小史征求他的意见,“要不我向他透一透?”
“别别,过一段再说。”
这一过又是两个月。三个月是一个疗程,再一复查,小史的病灶已“纤维性变”,也就是说,正向钙化的目标挺进,而小张的病灶就像定住了一般,仍没有明显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小张终于向宋科长吐露了自己的心思。宋科长沉吟了一会儿才说:“让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吧。”他那倒抄手的标志性动作中,好像又多了几分沉重。
我的父亲史凌空后来谈到他这一段的心情时说:复查的结果更增加了他战胜病魔的信心,三个月来,没服任何的药物,只靠有规律的休养生活,尽可能地减轻精神压力,提高自身的内在抵抗力,病魔至少已不敢再嚣张。看来不怕死不等于放任自流,真正的无畏是建立在积极面对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不断地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期间,苏联小说中的人物保尔·柯察金,电影中的“无脚飞将军”的事迹都有力地鼓舞了他的斗志,他甚至还萌生了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提笔写作的欲望……
到第四个月头上,宋科长来找小张谈话。从科长的神情上,小史看出有比较重要的话要说,他很自觉地出屋到军区花园散步,一个小时后才回来。这时科长已经走了,而小张的心情好像宽松了些,他对他的病友说:“组织上要我转业了,在地方上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也许有利于我身体的康复。”
“什么地方呢?”
“琴岛。”
“哦,那是个好地方,海边的避暑胜地,我早就向往着呢。”
“那……等以后我混得好一些,在那里与你重逢。”
他俩分手的前夕,彼此交换了纪念品。张给史的,是参军时从老家带来的银钥匙链;史给张的,是他参加省团代会的奖品“解放”牌大号金笔。走的那天早晨,他俩少不了互道临别赠言。史对张说的是:“一定要在新的地方,换一种新的心情,把身体弄好。”张对史说的是:“我专说你不爱听的: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还会有不少困难和挫折,要有精神准备。”
“谢谢你,我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这句话,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
小张走后,小厢房里只剩下小史孤零零一个人,他的生活却安排得更有规律,增加了适度运动的时间。有一天早晨,他突然有了灵感,写下了有生以来第一篇向正式报刊投稿的文章。那是基于《中国青年报》的一次征文,题旨是:“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如何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他就把自己在机要译电工作中两番打破全国新纪录的经历,写了一篇一千五百字的文章。发表出来后被删成八百字,却也使他喜不自禁。过了一周收到六元钱的稿费,又使他一个晚上兴奋得没有睡好觉,第二天起来脑袋好沉,整天精神不好,这又使他谴责自己:看把你烧的,六块钱就这样沉不住气。姓史的,请记住,下不为例!从此他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谨忌过喜过悲。
过了几天,他又将另一篇看“无脚飞将军”的观后感投寄给北京《大众电影》,竟一字未删地刊登出来了。果然,这次他的情绪就平和多了。
所有这一切,他本来对谁都没讲,却没有掩住别人的眼睛,竟“轰动”了整个机要处。
终于,宋科长来“看”他了。他本来准备挨“撸”的,至少要含蓄地批评他“不安心好好养病”之类,然而并没有。科长虽然没赞扬,却说了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看来我们机要处要出作家哩。”
然而,另一桩引起他情绪波动的事却接踵发生了。休养半年后,复查的结果是“基本钙化,上半天班”。这本来是大喜过望的好事,回来本想第一个向宋科长汇报的。谁知宋科长主动上门,在屋内极不寻常地踱了几圈后,试探着说:“凌空同志,有一件事告诉你,你要有个精神准备,要经受得住。”
原来,近期军区司令部直属机关团委改选,上级提名史凌空为团委委员候选人,所有的候选人名单都要拿到各团支部酝酿讨论,由团员发表意见。然而,当史凌空的名字出现在团支部书记赵天登的眼前时,这位“面如重枣”的长条脸登时先入为主地发话了:“养病期间不务正业,工作上未做丝毫贡献不讲,还想方设法大出风头,想当什么作家,这给我们树立的是什么榜样?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极端的名利思想,个人主义的典型!”他一带头,众口相随,史凌空的团委委员候选人自然就被否定了,而后,“大家建议”,赵天登为新的一届团委委员。
史凌空当时向宋科长表示他能理解,也能经受得住。但当科长走后,他却一头倒在床铺上,左思右想,分明是赵天登从中使坏:此人虽看来精明干练,译电业务上却绝非好手,在小史按规定每月领八斤猪肉技术津贴的同时,赵才拿三斤猪肉的津贴,为此他妒忌得心中冒火,七窍生烟,千方百计给使绊子。这次他既然抓住了史向外投稿的“把柄”,岂能放过?
这是史凌空参军以来,明面上受到的最大打击,他整整一天没有起来吃东西,晚上还尽做噩梦。然而当他终于挣扎着起来,昏昏沉沉,立足不稳,对镜看自己满面憔悴时,他猛醒了,不由得在心里骂自己:“史凌空,你既然连死都不怕,还在意这点得失?你再这样小肚鸡肠,小气鬼,我都看不起你!”
“去他娘的吧!”这是他吐出来的最后一句粗话。若干年后,他向儿女承认,他确实说了。
如今父亲史凌空已七十有七,但他不准儿女说“高龄”二字,他的理由是:七十几算啥,比起人家九十几、百十多岁的老同志只能算是“儿童团”。还真是,他的身板出奇的健朗,精神头格外地旺盛,这两年一连出版了两本小书,一本是回忆录《记胶东支前大军中的少儿宣传队》;另一本是散文集《战火中的朝鲜山水》,还挺有看点哩。有人问我和妹妹:“你们家老爷子上过大学吧?”我们只能笑答曰:“他上的是战场大学,学的是密码电报专业。”其实,他参军前只上过高小,参军后蹦蹦跶跶又上了一年速中,就这点墨水。然而他天赋不错,有超常的记忆力,这是我们儿女都不及的,尽管我们中这个“大本”、那个“硕士”的。今年春节,他不知怎么又想起当年养病中的经历和“****”中九死一生的遭遇,百感交集地说:“啥过五关,最大的关是生死观;啥斩六将,最难斩绝的‘将’是心胸狭窄,患得患失。”
他说着,又推开门奔大街报刊亭去了。买报,是他一天里最大的嗜好之一。外面的风挺大,我拿起他的帽子赶了出去,却没想到,四十几岁的我竟然追不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