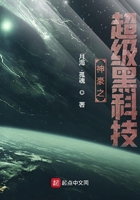我凝神于一片晨曦的明亮中
想那隐蔽之处 许多赤色的精灵
总在移动它们深褐色的趾爪
噢 那阵我心中的大风
是在什么时候
猛地吹破了那些无形的网
摘自《清晨的蛛网》
正午,穿过树林
正午,穿过树林
那个男孩向前跑去
年轻的母亲抬起眼睛
秋天已经成熟
林中汇入八月的风
拂动她宽松的裙子
年轻母亲的眸子里
正午———幽远、透明
书摊开在草地上
心在阳光下行走
坠落的果实也坠入另一个季节
盛夏已经过去
那使你翻开另一页的到底是什么
1984年3月
故乡、菜花地、树丛和我想说的第一句话
是春天,是鹅黄的一片,开在水边和返青的冬麦田旁
村口的树丛仍光裸着
春把希望和一丝过去的忧伤同写在二月
一片鹅黄的菜花地,在南风中,颜色是透明的,轻快的,轻快地摇荡
像我小女儿的心
而父辈们在土地那边留下了走得河道般低洼的路
(多雨的季节可怎么行走)
在阳光和泛起的泥土气息中
候鸟们在筑巢的季节里做它们最后的选择
飞过水面、掠过鹅黄的菜花地
终于栖落在那片褐色的树丛中
绕过那些树干,你在想什么
在久别的故乡
在那片茫茫若失的薄雾的后面
我又听到了犬吠和村子里清晨的喧闹
那片鹅黄的菜花地已开放了许多年
生命之火有时候燃烧得很平静
1984年5月
杜鹃声声,沿乡路走入寂静的山谷
这是暴雨后的黄昏
红色的土路穿过山坡下暗绿色的果园
多么寂静
杜鹃声声
伴我们走过松林下的墓地
当我弯腰抽出那棵谷草
远处
城市的灯光萤火般闪烁
你无意间讲起那些祭祖的乡俗
酒慢慢洒向脚下的泥土
山峦停止了晚风的呼吸
渐渐凝成一座
雄伟的古城
星空高悬
“布谷———布谷———布谷”
杜鹃声声
唤我们走入寂静的山谷
1984年5月
湖边晚归
鸟儿振动着闪光的翅膀,向远方
白日正深远地飞逝
黄昏栖落在浅滩上
晚归的鸟儿在寻找它记忆的踪迹
终止了无数次的思念
在一片沉寂中期待
聆听桨声,等着一条船从那边划来
我也回来了———故乡
黄昏,在一片紫色中多么宁静
一丝幽鸣在水面上缓缓地展开
把寂静凝结在旷野里
如果这时,突然间升一串布谷鸟的叫声
村镇小学的晨钟湿润地振荡
那么,故乡,在你和我记忆的深处
那些无声的对应,悬挂着,沉默着
在泊着许多条船只的村口
一年又一年地吹着黄昏里的风
当守候的钟声骤然间敲响
我知道,故乡
你用以往的眼睛认出了我
1984年7月
灰蜻蜓
你走去的影子突然间唤起了什么
微风轻拂
一只灰蜻蜓
在塘边的草茎上摇曳
水很冷 已是初秋
你走过时的神态不只是宁静
在下午的街角
你轻轻走过
灰色的衣裙有节奏地摆动
时光转瞬成为以往
当你回首 看见的只有
冷似秋水的背影
一只灰蜻蜓
穿过逝去的记忆
在塘边 在秋天的草茎上
而生活 你又怎么知道
未来的一切与记忆中的往事
哪些更长久
1985年6月
晨风
黎明
树木的枝干闪出银辉
春雪的润泽使我想到了你
大河千年涌流
还有亘古的牧歌与梅雨
一头牛正穿过清晨的雾霭
你在一首歌中渐渐呈现
那是一片多么平静的原野
蓝色的炊烟
使初春之晨充满了生机
晨风料峭
吹进敞开的窗子
1985年6月
雨中长笛
这是长笛的声音
黄昏的雨飘个不停
(可以把音量放得小一点)
那些日子已经远得看不见了
秋天在和一个少年的心灵对话
既遥远又陌生
那些逝去的日子
比书中描写得更确切
校园里的树叶黄了
飘了一地
心中的秋天更高远
高得让人发空
落叶在风中滚动
长笛却很纯净
纯净得有如漫步于高原的七月
草场无垠
马群在月光下漫游
而我还听到了那逝去的
深秋里的脚步声
就在这高高的楼窗前
夕阳里闪动的鸽群
现在不知在哪个阳台上躲雨
长笛的声音在飘
飘得很远
1986年1月
月光下的乡村少女
她们径直地走在前面
相互依恋着晚风中的收工行列
说笑着 结实又年轻
在转向灰蓝色的晚霞倦怠又安宁
也许如今她们都已做了母亲
也许一生你都不会再走上那些乡村小径
也许那些怀乡和离别之情已沉淀得透明
也许只有告别了青春才知道什么是痛苦和爱情
也许她们从来没有想过就做了母亲
有时候 人们在一片烟雾中诋毁爱情
谁能如翻动报纸把时光闪闪翻动
失去和惆怅之情常常潜入心中
那么就飘动 飘在沉思与叙述中
回到那些树丛 晚风和垂暮的草垛下
黄昏的寂静渗出幽暗的丛林
渐渐地使行人的脚步变得匆匆
这一切已远得使你无法触摸
在新月的光辉下
那些质朴的影子飘来荡去
我已无法辨别她们的面容
1986年2月
在一本书与另一本书之间
这本书很薄
上个世纪的一颗灵魂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他在不停地召唤我进入那片阴影
桌子上
削下的果皮发出一股股劣质甜酒的气味
玻璃杯中的茶早已经凉了
而灯下的她 正进入一本逃犯写成的名著
不时地停下来思索
有时还看看地图
在南美热带雨林中
乘一艘破船也有可能逃离终生的苦役
人类的自由已被虚幻了多少个世纪
我在想 那颗灵魂
在他死后的一百年中
随时都会把人们引进一片真实的荒漠
这是另一种逃离
在漆黑的窗外
这时 时钟正冷漠地滴穿岁月
1987年1月
面对草滩
心灵的闪光来自对什么的渴求
湖泊在黄昏的余辉中
是有一种欲望来自沉郁的岁月
一封信 一首歌曲 一个无言的请求
当我走过那些河岸和落叶堆积的小径
被一个无法实现的允诺缠绕了许多年
那影子已化为低垂头颈的天鹅
有时我梦见
在一片遥远的草滩上
那只神秘的大鸟正迎风而舞
1987年2月
高庙幽思
列车穿沙荒而来
钻进八月的浓烈阳光
有人为一次孤单的旅行
在这边远的小城
潜入一个漫长而芬芳的下午
那座木制的庙宇已老态龙钟
飞檐交接 透出几丝往日的神圣
楼燕飞鸣 薄暮中有古人穿岁月而来
与我的沉思相遇
迎面揖手 飘三缕长髯转楼窗而去
当这油漆斑驳的古庙
浸入满月的清辉
干燥的八月之风
曾将多少代人的心潮涌动
世界依旧 只是痛苦的思想
更难以找到往日的安宁
不再是高歌
不再是吟诵
不再是朱颜已改的一片失落之情
这亘古至今的寂静
已足够人怀念终生
1987年7月
黄昏,在异乡的寂寞中
异乡的黄昏渐渐来临
寂静中听孩子们的欢笑
那些可爱的声音毕竟属于他人
孤单中眺望远山
蓝色峰峦的那边是一片荒漠草原
我曾看见
一只孤单的骆驼
仿佛在那儿站了许多年
穿黑衣袍的老人
目送我们的汽车消失于一座平缓的土岗
在这边远的地方
谁又知道
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了多少年
而在贫瘠的草坡上有他们温暖的家
牧羊狗狂吠
土墙在阳光下泛出光芒
该离去的都已离去
只有我坐在这把黄昏的椅子上
想到远方的家
灯下与妻子的闲话
缓步而来的夜,正慢慢地
掩去远方的山峦
我突然感到
平凡的日子里
逝去了多少值得珍重的情感
1987年7月
正午,莫高窟
高原上直射的太阳
在这小小的绿色的腹地
蜥蜴在它浓荫的光晕上急行
正午的莫高窟 合上了智慧的眼睛
我徘徊于绿色的栏杆之外
记忆迷失于漫漫长途的沙原之中
三危山在正午的阳光下失去了清晨的神秘
它横卧在那儿
切开大漠流沙的圣灵之光
在它每一块褐色的石头上
停止了千里迢迢的寻游
大地宽广如巨大的海绵
把阳光 声音吸入它沉沉而眠的肌肤
低垂的草叶上没有风尘与沙暴的滋味
只有太阳直视着这小小的绿洲
多年的向往金黄闪烁
于深邃隐秘之中缓缓而升
当我垂首于这正午的宁静
岁月波涛悠悠散去
此刻的洞窟,静息如少女般恬静
1987年8月
被遗忘的高原小站
午后的寂静中
我们走向坡地上的小站
高原的青石峰下
空旷 看不到一个人
道路左边 渐渐侵入的流沙群
在阳光下金黄地闪烁
两只追逐的狗 远远地
从路基上倾斜而下
钻进了一片疲倦不堪的矮树林
那辆疯狂的卡车
扔下我们 拖着尘土的长龙
很快地消失在
山路的拐角上
阳光直射
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穿铁路制服的小伙子迎面走来
突然终止了他缓慢的口哨声
从他疑问的目光里
我们已注定地被抛弃在这儿
远远望去
这高原的七月
那座几乎被列车遗忘的小站
在蒸腾的气流中遥遥而立
比来自远方的客人更孤单
1987年8月
雪一直没有飘下来
不是在水或音乐的节拍里
有时在一阵阵无名的节奏和忧郁的情调中
有一种声音比诱惑更神秘
不一定要知道你是谁
幻想在人丛中不会找到你
也许因此 雪一直没有飘下来
果树对于果树不知是怎么相爱的
围墙上的麻雀飞去又回来
在开花的季节过后
每一个走过园子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人和人是怎么相爱的
有时隔着比树更远的距离
雪一直没有飘下来
尽管在许多瞬间沉入铅灰色的天空
幻想的风使激情发冷
也许那从未降雪的云层很低
它无法知道化成水流的感觉
也许那时你已不再那样说
但 雪一直没有飘下来
1987年11月
黄昏风
黄昏的风
使树木弯向太阳沉落的地方
收音机里
一个声嘶力竭的男人在渴求爱情
挂满各色时装的店门前
少女们突然扬起的黑发
如一丛丛闪动的火焰
这初冬的黄昏风
被那股来自高原的旋律充满
一阵紧似一阵的敲打不是来自那面低音乐鼓
不是海涛 不是幻影
在那声音的背后
我听出了血液的低鸣
这黄昏的风使树木弯向太阳的余焰
在一片凄厉而辉煌的唢呐声中
骤然间
爆发出那发自生命的呼喊
1988年3月
是春天,也不是春天
是春天,也不是春天
她美好,是否也残酷
曾是那样的遥远
田野在一片薄雾中,春天
在它力所能及的地方促根茎风长
我寂静又突然地走近你
爱恋得既具体又神奇
你悄然转身将春天的花束堆满怀抱
是春天,也不是春天
和暖的风吹透整座树林
绿色的火焰闪动金黄的渴望
星星点点,星星点点
织情感的网
而我只想对你说,这季节对于我们
是春天,也不是春天
1988年4月
小镇巴日图
夏日牧场的小镇只有一条街
两边白桦树干的木栏日渐陈旧
风雨剥蚀而远山依旧蔚蓝
最使人怀念的是那座简陋的乡村酒店
斜倚栅栏的是醉酒的男人和长长的套马杆他们的坐骑在阳光下嘶鸣
而主人的灵魂在草场上漫游 久久不愿归还
这洼地上的小镇
四周起伏的草场布满夏日的羊群
黄昏的阵风吹低了云层
雾霭渐渐托起密布的星群
牧人们三五成群,离开小镇酒店
斜跨上坐骑
怀中的老酒带他们走向草场的深处
只剩下几粒灯火 在墨绿色的天体下闪烁
远处 牧羊犬的叫声戛然而止
草场静默 梦中的牧神已悄然降临
1988年7月
周末纪事
鸽子消失在楼群的影子里
黄昏的哨声悠长地颤动
如秋风夕阳下银杏的叶片
颤栗得明亮
颤栗得金黄
秋蝉的鸣叫也渐渐透明
仿佛能感到它蝉翼的光泽与细微的纹路
黄昏使高大的树木垂首
校园寂静
脚迹印满黄土的场院
落叶飒飒
似乎回忆起午间那一阵阵的吵闹声
当我沿着那条回旋的河流走回家去
楼群把长长的影子
抛在陡直的河岸上
那群灰色的鸽子停止了又一日的盘旋
水在平缓地流
(谁又能确切地说出
平凡的生活中逝去了多少相似的日子)
1988年9月
高原遇雨
从湟源到日月山
这朝圣路上
汽车迎八月的高原之雨
道路泥泞
破旧的车厢在颠簸中行进
邻座那件老羊皮袄的气味令人窒息
云雾飘过
峰峦时隐时现
经过一个上午的艰难跋涉
汽车在一个临河的山谷再也无法爬行
雨依旧飘落
在灰色而泛着水光的山谷间
空气潮湿
人有如浸入一洼冷水中
我攀上一座缓坡
农舍前一条长毛的藏狗向我低吼
同车的路人零散在红色车厢的四周
司机在车前无可奈何地环顾
山坡上的青稞开始变黄
这里的夏日已进尾声
那片如海的高原之湖是否也已经变得阴冷
今夜 临湖小镇一张床在空等着它的客人
而高原之雨接连数日
把道路搅翻
滞留了我心中早已向往的里程
1988年9月
雪
在遥遥相望的村落间
冰盘般的太阳
挂在雪后的原野上
一辆马车正穿过岁月的薄雾
(很久没有听到过清脆的鞭声了)
这冬日雪后的“白夜”
一切都沉入了寂静
是谁们隐匿于皑皑白雪中
在岁月之幕的后面
吹起潮润的雪后微风
使枝丫微垂的老树轻轻地颤动
有一种雪
一直落到人生的暮年
往事飘浮 幽鸣而空远
灵魂明静 如一轮高高悬挂的冰盘
1988年12月
剥开橙子
你在那儿剥一只橙子
汁液飞溅
阳光里坠落细微的雨
面对无言
彼此都知道我们的等待
必然是一种相互的摧残
语言之刃比手中的更锋利
冬日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
时光之神 沉醉其中
照在两个新剥开的橙子上
一股苦涩
越来越浓
弥漫了整座房间
1989年1月
凉风乍起
午夜的天空
弥漫开蓝翡翠的光泽
在一片夏日的树木之上
呈现出一双灰绿色的眼睛
一朵云 停滞不动
透过昨日的幻象
往事沉郁
遥远 飘忽不定
无端的愁绪结在那些滴水的蓝色花瓣上
一场暴雨侵入了夏夜的深处
1989年9月
火红的花束
沉沉的如一只陶罐
黄昏的雷电在天边无声地闪动
绿夜
掩住了夕阳火红的碎锦
任一阵冷风在夏季的心头狂吹
倾听夜的声音
无法预测这古老而陈旧的烧结
陶罐流溢的釉色把暗夜如何延伸
而心中那一束橙色的野花
在我采摘了多年后的今天
再次点燃了失落于旷野上的声音
一只陶罐静静地置于窗口
那插满罐口的火红的花束
胜过凡·高的向日葵
1989年9月
再临月夜
当一声尖叫碾过夏夜的寂静
灵魂穿越了积习和黑暗
伴我于窗前
风中明月摇荡如百合花的幻影
透过往事、烟雾和酒
那些渴求生活的灵魂
烛火般脆弱
悄然游荡于摇曳的光芒中
使夜半酒后的泪水辉煌而沉重
在远离生活的时辰
一只手温柔地覆住了情人的眼睛
月色朦胧
泪水一滴滴坠落
溅起了心中无尽的回声
1989年9月
午夜地铁
地铁车站的壁画与生存何关
仕女们舞动的袍袖
掀起了隧道深处幽幽的冷风
鲜花紫色的忧郁在一双颤栗的手上深深浸入的渴望洞穿了多年的梦境
凝神于夏日的激情与疲惫的期待
一辆列车碾过了离别的时间
死亡曾滞留于欢聚的尽头
午夜地铁的壁画下
只有空寂的站台
吹动衣袂的阵风
肃杀深秋般地驱散了心头的幻影
1989年10月
当大风呼呼地刮过
当大风呼呼地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