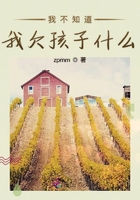打开衣柜,没有一件像样的衣唯一一套西服,裤子都磨得变了颜色。悲伤再一次涌上心头。这么多年,他不追求吃穿,但万兰整天穿衣打扮,有空就逛商店,给自己买那么多衣服,从来不为他想。他的衣,不到换洗不开,不到破旧不能穿,她从不给他更换新衣。这样自私自利的老婆,离了也好,早该离了。
中校长已经把三十万科研经费转到他的名下,由他支配,他签字就可报销。东学潮决定到商店买套衣服,就买那种休闲的,价钱不贵,穿着也自然大方。
进了商店,东学潮才感觉到买衣服的麻烦,要么样式不好,要么价钱不合适。什么样式的衣服穿在身上,感觉都没有中校长和别的老师那样气派。他决定随便买身便宜的,如果和马珍珍谈得顺利,就让她当参谋给他买一套好衣,顺便也给她买点东西。
莲花山其实并不有名,只是郊外普通的一座山,山上树木也不多,许多地方光秀秀的,显得有点荒凉。马珍珍解释说:“我不喜欢那些茂密的森林,密不透风,视野也不开阔,给人的感觉就是压抑。这多好,一望无边,辽阔苍茫,心都扩展得无边无际了。而且人也不多,安静闲适,不像那些风景区,裹挟在人流中,不像游玩,更像被押解着匆匆忙忙赶路。”
感觉像个文学女青年,虽然外表粗糙,内心还是细腻文雅。难道这个女人也喜欢魏晋风度?东学潮感觉更喜欢这个马珍珍了,特别是她的心直快。早上马珍珍打电话说到校园接他,他急忙往校门走,她已经将车停在那里等他,根本不考虑矜持和降低身价。他当时就有点感动,这样不斤斤计较甚至没有心计的女子,当然是最好相处的女子。走到一个安静处,东学潮想更主动一些,揽住她的腰或者牵牵她的手,但她的儿子一直让她拉着。她的手一直在她儿子的手里,她也只能只顾着她的儿子。
很快发现她儿子要比他想象得还要麻烦。儿子太活泼好动了,看到什么都想要,看到哪里都想去,但又不自己去,抓蝴蝶,也要和妈妈一起抓。他只能冷冷地站着观望。东学潮觉得这样别扭下去不行。马珍珍能不能嫁他,很大程度取决于儿子。如果儿子不接受,或者他不接受儿子,马珍珍都不可能不三思。就像一部电视剧里说的,娶老婆,得先娶她的儿子。问题是马珍珍一直不把儿子介绍给他,好像根本没那个意思。儿子要爬一个不太高的岩石时,东学潮主动上前,说要带他爬。马珍珍趁机将儿子交到他手上,但儿子坚决不干,屁股坠地,拉都拉不起来。马珍珍只好拉儿子一起爬山。
一棵高大的果树,上面有半红的果子。儿子一定要摘,但果子高高地挂在最高处,下面的已经被人摘光。东学潮将儿子抱起来,也远远无法够着。儿子却不死心,一定要摘到,摘不到就不走。马珍珍笑着对东学潮说:“爬树怎么样,要不试试。南方有个民族,考验女婿的办法就是让爬树,爬上去才有资格结婚。”
动物大多用类似的办法选择强壮的配偶。小的时候,东学潮爬这么高的树就是闹着玩。如今,东学潮抱住树,身子却沉重得像灌了铅,也好像没有一点力气,力吐皮鞋光滑,努力半天也没爬多高,只好放弃。东学潮红了脸说:“多年不锻炼,不行了。”见马珍珍呵呵笑,又悄声说:“不过你放心,爬树不行,爬人没问题,甚至很棒。”
马珍珍笑出了声,说:“不是我说的,是书上说的,说男人都嘴硬,下面多软,嘴从来不软,也从不说不行。”
这样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东学潮还是有点不能适应,感觉不像知识分子,也不像普通的女子。不过说点粗野的话也没什么,粗野有时也是性格开朗无所顾忌的体现,何况是在她喜欢的男人面前。也许正因为喜欢,才无所顾忌。就像自己的老婆,在丈夫面前脱裤子,也不会有一点遮掩。
儿子却死死抱着树不肯走。马珍珍再仰望一下树,说:“你蹲下给我搭个人梯,我来爬。”
马珍珍踩在东学潮肩上,仍然爬不上去;再踩在东学潮的头上,还够不着要抓的树杈。东学潮只好托住她的屁股,再托住她的脚,总算把她托上。
东学潮浑身鼓胀得有点发晕。马珍珍踩在他肩上时,裙子几乎罩住了他的头,裙底的一切,就展示在他的眼前,而且离眼睛那么近,好像要把他的眼睛遮住。托她的屁股时,他有意托了一下她的****,异样柔软的感觉,让他如同触电。她似乎没有一点反应,连讨厌这样的话都没说。她挣扎着往上爬时,****几次大部分暴露了出来。他决定扶她下树时动作更明显一点,看她有什么反应。如果顺利,今天就彻底将她得到,把事情也彻。
连摇带摘,马珍珍一气弄下来七八个果子。东学潮也不去捡拾,只等着扶她下来。但下来时,却是那么的快捷,还没等他托稳当,她已经滑到了他的怀里。东学潮还是乘机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她小声说小心孩子,他才把她放开。
兴奋就像泉水,流淌得浑身欢快。他感觉,如果他提出今晚住在一起,她也可能不会拒绝,说不定会很高兴很幸福。
儿子要吃苹果,马珍珍急忙用矿泉水冲洗苹果上的泥污。但儿子啃一,酸涩得龇牙例嘴吐掉,再啃一又吐掉。又啃一个,仍然酸涩,然后将所有的一起扔掉。
马珍珍还是捡回几个,装包里,说好不容易得到,拿了回去玩。
儿子仍然闹个不停,和她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坐坐的想法始终无法实现。玩到中午,儿子终于累了,开始吃包里的零食。东学潮紧挨马珍珍坐下,手刚放到她的腰上,儿子立即喊不行,不许耍流氓,然后喊着要到饭吃。
开车来到一处农家乐,要了一个炖土鸡,一盘炒土鸡蛋,两个农家素菜。炖鸡上桌,马珍珍撕了一个鸡腿给儿子,儿子却突然提出要吃肯德基。马珍珍开始哄劝儿子,可越哄,儿子越坚持,而且哭闹得越凶,连打带抓,把马珍珍的一个纽扣都撕掉了。东学潮不能一直坐观,这儿子将来也会是他的儿子,他想试试爸爸的本领。他将儿子抱到怀里,刚说这里没有肯德基,儿子却很响亮地给了他一个嘴巴,一下将东学潮打得呆在了那里。马珍珍急忙将儿子拉过去,与其说是制止儿子,不如说怕东学潮发火打儿子。让东学潮愤怒的是,马珍珍竟然没严厉责备儿子,不痛不痒地教育儿子不能打人,好像儿子刚才是不经意地打了一下小朋友。这样溺爱孩子,长大了怎么了得?婚后怎么生活?长大了,说不定会把他打出去,而马珍珍也肯定向着她的儿子。这个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一团阴云,将东学潮紧紧地罩住。东学潮恼着脸不说话,以此来表示不满和抗议。
马珍珍开始给儿子想办法,说把鸡腿烤一下,再撒点味精调料,肯定比肯德基好吃。儿子同意点头,马珍珍急忙拿了鸡腿去厨房找大师傅,在灶火上给儿子烤鸡腿。
吃完烤鸡腿,再喝一碗汤,儿子终于不再折磨人,跑到院子里逗关在笼子里的黑狗狂叫,又满院子追那些觅食的鸡。马珍珍对东学潮说:“我知道你不高兴,但没办法,每当我生气时,想想他从小就没爹,我就心软了。我也只能责备自己,因为是我的过错,让他一出生就没有爹。我想,他长大懂事了,自然就会理解母亲的苦心,自然就会很懂事。”
东学潮的心也软了,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东学潮急忙说:“也没什么,据说调皮的孩子,将来会有出息。”
马珍珍将话题转到科研上,询问了一些白沙滩的科研情况,说:“你需不需要助手?我想加你们的科研团队,给你们打打下手,抄抄写写。”马珍珍已经是副教授了,加科研团队,当然是为升教授做准备。看来,她也不是个安分守己容易满足的女子。加也好,整天在一起,捂都能捂出爱情的芽苗。结了婚,一起干事业。干一样的事业,不仅方便,也有共同的东西。东学潮说:“你是天才女副教授,要高我一个档次,怎么能让你打下手。让你指导我,咱们一起干,倒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马珍珍认真地说:“不搞点研究工作只教书,感觉太平庸,也太空虚。那咱就说定了,以后有什么工作,比如测定分析一些东西,就交给我。什么时候去白沙滩,也领我去看看。”
白沙滩项目由他来负责,而且中校长明确说过要他再联络一些人组成研究团队,现在正好。东学潮抓住她的手,说:“一言为定,不许反悔。”马珍珍突然问他为什么离婚。东学潮估计中校长已经大概和她说了,他决定详细说给她听。但真说起来也就那么几件事,很快就说完了。
他也想问她为什么离婚。她似乎不愿说,也不愿提起,只说前夫原来在一个科研单位,嫌死工资太少,就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发了点财,就提出了离婚。
东学潮并不满足,离婚的原因,不仅能判断出对婚姻的态度,也能感觉到家庭责任和维持家庭的能力。他想知道更多,但感觉不宜多问什么。气氛显得沉闷起来,两人几乎同时劝对方多吃一点。儿子又跑了回来,说要回家睡觉,说走就得走,一刻也不等,只好匆匆收拾回家。
车停到楼下,还不到下午四点。在路上,东学潮就想好了,今天要到她的家里坐坐,如果她不拒绝,就一直待在她屋里,晚上也不走。虽然理智告诉他这样不好,第一次在一起就这样,一般人都觉得不合适,但理智还是斗不过荷尔蒙。从托她的屁股开始,他浑身的鼓胀就无法消退,一阵阵的性冲动,弄得他如热锅上的蚂蚁。来时买了农家土鸡蛋,也买了几个小南瓜,他有理由送她一起进屋。东学潮急忙下车,把鸡蛋和南瓜都提到手里,一副上楼进屋的架势。东学潮眼睛盯着马珍珍,马珍珍好像并不知道有他这个人,锁好车,便拉着儿子往楼门走。这当然是让他上去,或者是考验他想不想主动上去,也有可能她感觉已经像一家人不用客气。东学潮心花怒放,一声不响急步跟在后面,一声不响一起进了门。
儿子虽然在车上睡了,但还是要睡。马珍珍将儿子抱到卧室,将门关死,和儿子躺在一起,哄儿子睡觉。东学潮只好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等。
环视屋子,感觉应该有一百多平米,比他现在住的房子要大。屋子装修得不豪华,但也能感觉出新屋的气息。只是屋子收拾得不太干净,书报胡乱地丢在沙发上茶几上;桌子上还有几块西瓜皮,好像是昨天吃的;瓜子也吐在茶几上,弄得茶几像个小饭馆的饭桌。可以感觉到,屋里的摆设和她的穿着一样,都表明她是一个不注重细节的人,甚至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但话说回来,一个人过日子,弄那么干净给谁看,他自从一个人过,就从来没认真收拾过屋子,屋子里的尘土比这还多。
马珍珍终于出来了。她轻轻地坐到他的身边,让他感觉挨得很紧。她的身体像巨大的磁铁,东学潮浑身的激情和血液都被吸弓得沸腾起来。他伸手揽住她的腰,试探将她揽到怀里。她立即呵呵地笑了,说:“你干什么呀,不行,不要这样。”但身体却很顺从地倒进他的怀里。东学潮一下想到第一次和万兰亲热,万兰也是这样,说的话也一句不差,表情和神态也一模一样。也许女人都是这样,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接受和矜持。东学潮一下将嘴死死地压到她的嘴上,然后翻身将她压在沙发上。她立即悄声说:“不行,到卧室里。”
他一下将她抱起,将她抱进她指的那个卧室门。
这应该是她的卧室。自从和万兰闹翻,就再没沾过女人,孤寂的夜晚,他多少次靠****来解决问题。今天终于又把女人抱在了怀里,他顾不得许多,很猛烈地将她放到床上,手忙脚乱脱她的衣服,刚进,马珍珍突然惨叫一声,猛地将他翻下来,痛苦地捂住肚子,蜷缩成一团在床上翻滚。东学潮一下愣在那里,感觉不像高潮来袭,更不像玩笑。马珍珍喘息着说:“可能是子宫痉挛,快给我揉揉。”
东学潮不知该揉哪里,而她捂着的地方又死死不放,只能在她肚子周围乱搓。还好,她慢慢安静了下来,然后彻底放松,说:“疼死我了!突然不疼,感觉特别舒服。这下我明白了,不疼痛,才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事情。”
尿憋急了从厕所出来也会说这样的话。但可以看出,刚才她确实是疼坏了,疼出了一头汗,眼睛都疼红了。东学潮将她抱在怀里,却不敢再造次捅娄子。马珍珍说:“我有子宫痉挛的毛病,弄不对就犯。咱们盖上被子躺一会儿。”
也不知痉挛的毛病重不重,如果严重,那也是问题,说不定这也是她离婚的原因。东学潮只能搂着抚摸她的全身,等她舒服了再说。
感觉马珍珍比万兰要柔软一点,也虚松一点。万兰看起来苗条,其实结实丰满,是看起来瘦摸起来肉的那种。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隔着衣服袋,仍然响得像催命的战鼓。是中校长打来的。东学潮急忙坐直身子,中校长说:“你马上来一趟我办公室,有事要和你说。”
休息日都在办公室,不知什么大事。东学潮想问什么事,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好问,问是不礼貌不尊敬的表现。不管什么事,都得立即去,去了自然会知道什么事。放下手机,东学潮想把事情办完毕,马珍珍却摇头表示还不行。看眼表,马上要到六点,他刚才又没说他在外面,去迟了中校长会觉得他怠慢。东学潮只好亲一下她闭着的眼睛,急忙穿好衣服往学校赶。
来到中增长的办公室时,东学潮已经满头大汗。中增长说:“省电视台的打来了电话,明天去白沙滩采访,然后拍摄一个专题片。我决定让你一个人陪他们去,也全权负责一切事情。你先写一个借条,到财务科借五万块钱带上,拍摄期间一切费用,你都支付。如果他们提出买点什么或者支付点报酬,在两三万以内你都可以答应,你都可以伺机处置,不用问我。不知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满意,然后拍一个让咱们满意的片子,最好能推到中央台去。所以你要做些准备,拍什么怎么拍你要先计划一下,最好写一个提纲,然后和他们商量,让他尽量满足咱们,按咱们的意思来拍。”
感觉这个担子很沉重,拍什么不拍什么,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东学潮急忙问大概要拍哪些,中增长说:“当然要拍成果,内容大概就是可行性报告中说的那些。要把成果拍到位,要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拍到位;该美化要美化,该提升要提升,该前瞻要前瞻,该设想就设想。总之你把这些意思告诉他们,他们是专家,他高兴了,自然知道该怎么拍。他们是拍摄高手,也是编辑专家,这一点你不用担心。”